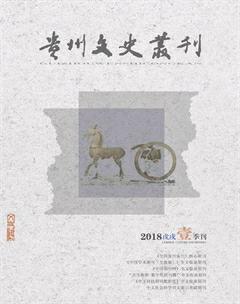試論王陽明軍事思想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與影響
丁濤+鐘少異
摘 要:王陽明創(chuàng)立“心學(xué)”體系的過程,也是推動(dòng)兵學(xué)與儒學(xué)融通的過程,考察王陽明三大軍功,可以看出他以軍政結(jié)合手法,將儒家“治國安邦”與兵家“安國全軍”有機(jī)統(tǒng)一,以期達(dá)到長(zhǎng)治久安的愿景目標(biāo)。在明中期政治昏暗、民風(fēng)不振的大背景下,這種“軍功”“治功”并行并立顯得別具一格,乃至為后世戚繼光、曾國藩等“儒將”或“文臣領(lǐng)兵”者樹立了很好的效仿模板。
關(guān)鍵詞:王陽明 心學(xué) 兵學(xué) 融通
中圖分類號(hào):B248.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8705(2018)01-32-44
王陽明創(chuàng)立“陽明心學(xué)”的過程,既是政治、軍事具體實(shí)踐的過程,也是推動(dòng)兵學(xué)與儒學(xué)融通的過程。兵儒融合是中國軍事思想發(fā)展史的重要內(nèi)容,或者說是主線之一。兵儒融合的歷史過程,可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為標(biāo)志分為前后兩個(gè)大階段:在前武帝階段,體現(xiàn)為在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zhēng)鳴”基礎(chǔ)上不同學(xué)術(shù)流派思想的交互影響;在后武帝階段,體現(xiàn)為歷朝歷代以儒家思想為主導(dǎo)意識(shí)形態(tài)下的兵儒合流。在漢武帝之后兩千年來的中國王朝歷史中,“以儒統(tǒng)兵”逐漸得到強(qiáng)化。王陽明以其大儒領(lǐng)兵的實(shí)踐,將兵學(xué)與“心學(xué)”結(jié)合起來,為兵儒融合帶來了新發(fā)展,對(duì)當(dāng)時(shí)和后世產(chǎn)生了獨(dú)特的影響。
一、大儒領(lǐng)兵的新代表:生平及軍事實(shí)踐
王陽明(1472—1529),明朝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承襲宋明理學(xué),開創(chuàng)“陽明心學(xué)”,自成一派;在事功上聲名卓著,尤其在軍事領(lǐng)域,可謂戰(zhàn)功赫赫,先后平定南贛“叛亂”、生擒寧王、剿撫根除兩廣地區(qū)“民亂”,對(duì)穩(wěn)固明朝中期統(tǒng)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的“文治”與“武功”齊名,在有明一代無出其右者,被后人譽(yù)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完人。其一生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在邊患不斷、“叛亂”四起的背景下,通過心學(xué)的修為、實(shí)踐的磨礪,最終成為“文臣領(lǐng)兵”的典型。從其貢獻(xiàn)來說,創(chuàng)立“陽明心學(xué)”的過程與平叛治亂的親歷實(shí)踐相互交融,對(duì)傳統(tǒng)儒家治世理論的體悟與踐行相得益彰。
王陽明出身官宦家庭,父親于成化十七年考中狀元,在家庭背景熏染下,加上天賦異稟,有機(jī)會(huì)接受儒家傳統(tǒng)治世思想的系統(tǒng)訓(xùn)練,基礎(chǔ)牢固、功底深厚;十五歲時(shí)考察軍事重鎮(zhèn)、了解關(guān)隘及邊防情況,為后來的軍事成就埋下伏筆;弘治十年,邊疆局勢(shì)吃緊,在王陽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自此開始研習(xí)兵法,廣泛涉獵兵家典籍,尤其是評(píng)注《武經(jīng)七書》,打下扎實(shí)的軍事理論基礎(chǔ),成為其兵學(xué)智慧之源1;弘治十二年考中進(jìn)士,觀政工部,受命營(yíng)建威寧伯王越(曾總制大同及延綏甘寧軍務(wù),收復(fù)河套地區(qū))墓,竣工后辭謝金帛而僅受王越所佩劍,足見其志向高遠(yuǎn);同年,應(yīng)朝廷求言北部邊防,上疏陳言整頓邊防“八事”:“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zhǎng);三曰簡(jiǎn)師以省費(fèi);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yán)守以乘弊”1,首次提出邊防戰(zhàn)略對(duì)策總體設(shè)計(jì),體現(xiàn)其以儒家“仁義”為核心、兵家“權(quán)變”為主旨,亦文亦武的治邊理論架構(gòu)特點(diǎn)。
正德元年(1506),武宗初政,寵信宦官劉瑾,大搞特務(wù)統(tǒng)治,王陽明抗?fàn)幹斜毁H貴州龍場(chǎng)驛;期間先后于龍場(chǎng)悟道(1508)、貴陽講學(xué)(1509),憑借對(duì)時(shí)政沉淪的切身感受及對(duì)程朱理學(xué)落寞的集中反思,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學(xué)說,從“圣人處此,更有何道”自念自問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精研頓悟,從“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的哲學(xué)取徑,確立人人自有良知、皆可成圣的“群眾路線”,對(duì)程朱理學(xué)空泛化、程式化、割裂化的背反,激活了傳統(tǒng)儒家“內(nèi)圣外王”由“精英”向底層民眾轉(zhuǎn)化的動(dòng)力,初步建立起向下、向內(nèi)求索砥礪的“心學(xué)”體系,給儒學(xué)的演進(jìn)帶來了新的發(fā)展契機(jī)。此一階段,王陽明逐漸擺脫“五溺”歸正于圣賢之學(xué),其“心學(xué)”思想也基本成熟,在“知行合一”的立意下,通過軍事實(shí)踐促進(jìn)了兵家的“詭”與儒家的“仁”的圓融與和合,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生機(jī)和活力,大大地推動(dòng)了兵儒的深度融合。
正德十一年(1516),南贛“盜賊”蜂起,王陽明擔(dān)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正式開啟平叛治亂的軍事生涯。轄地涉及今江西南部、福建西南、廣東北部及東南、湖南東南等交界地區(qū),地域廣闊、問題交織。王陽明首先以軍事任務(wù)為導(dǎo)向,請(qǐng)發(fā)旗牌、提督軍務(wù)、統(tǒng)一軍令,采取改革兵制、加強(qiáng)協(xié)同、廣收民心等手段措施,歷經(jīng)三次大戰(zhàn),一舉平定為患數(shù)十年的“民亂”。王陽明對(duì)寧王謀反早有覺察,安排得力門生冀元亨赴寧藩講學(xué)的同時(shí)予以戒備。寧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1519)正式起兵,地方各屬應(yīng)對(duì)不力,節(jié)節(jié)敗退,整個(gè)江西幾乎全線崩潰。王陽明臨危受命,準(zhǔn)確研判戰(zhàn)局形勢(shì),指出叛亂有上中下三策,即上策攻京師、中策攻南京、下策據(jù)守南昌。為牽延叛軍出兵南京,王陽明虛造聲勢(shì),離間其將帥,堅(jiān)決直搗南昌,迫使寧王回救,后及時(shí)安撫民心、穩(wěn)定軍心、居中調(diào)度,樵舍之戰(zhàn)生擒首惡朱宸濠,迅速平定叛亂,反映出王陽明出色的政治敏感和兵家的機(jī)敏,奠定了其軍事家的地位。
正德十六年(1522),王陽明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期間在浙江家鄉(xiāng)講學(xué),正式提出“致良知”命題,對(duì)忠信、孝悌、節(jié)義等社會(huì)人心的良知良能進(jìn)行探討,至此“陽明心學(xué)”體系的“三大支柱”基本確立,使其在思考處理軍政問題時(shí)更加成熟穩(wěn)健、自成體系,這一特點(diǎn)在晚年平定廣西思恩田州等地“叛亂”時(shí)得到了集中體現(xiàn),出于“仁心”追求善治的引領(lǐng),針對(duì)性分析“叛亂”根源,提請(qǐng)恢復(fù)改進(jìn)土司制度,在“平叛”時(shí)則極力主張招撫為主、征討為輔,迅速恢復(fù)秩序的同時(shí)妥善解決了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的治理問題。
二、兵儒融合的新發(fā)展:與“心學(xué)”相融通的軍事思想
王陽明“心學(xué)”體系集中展現(xiàn)傳統(tǒng)儒家“三綱八目”由內(nèi)而外的治世理路,突出特點(diǎn)為:以“天下歸仁”為總綱領(lǐng),通過努力尋求良知良能,進(jìn)而教化生民,始終堅(jiān)持以安民養(yǎng)民為目的,在盡可能從政治上解決治世問題的前提下,以軍事手段作為必要舉措,推廣儒家“治平天下”的價(jià)值追求,以達(dá)到長(zhǎng)治久安的遠(yuǎn)景目標(biāo);這種政治追求與軍事實(shí)踐相融通相促進(jìn),也成就了兵儒融合的新發(fā)展。endprint
(一)“陽明心學(xué)”核心價(jià)值追求
1.“致良知”的治世取徑
“陽明心學(xué)”是建立在“心即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三位一體之上的,如黃宗羲所概括“良知為知,見知不囿于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而不滯于方隅”1,是以“致良知”為統(tǒng)領(lǐng),在“心即理”的設(shè)定上,著力于追求“知行合一”的功夫。著力于以“治心”為取徑解決治世問題,即“化治世為治心”2。
明朝中期以降,社會(huì)矛盾日益激化,統(tǒng)治危機(jī)空前,當(dāng)時(shí)程朱理學(xué)已成為追名逐利的“敲門磚”,維系儒家傳統(tǒng)德行修養(yǎng)和教化的社會(huì)功效衰減,迫使當(dāng)時(shí)儒者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陽明心學(xué)”即是在這種背景下孕育誕生的,這一過程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一是“龍場(chǎng)悟道”提出“心即理”。王陽明因?qū)够鹿賱㈣獊y政而被貶貴州,立足儒家傳統(tǒng)治世理論對(duì)程朱理學(xué)活力喪失的反思,基于政治生涯沉淪和生活處境惡化的體悟,提出“心即理”的哲學(xué)命題,成為其“心學(xué)”立場(chǎng)確立的起點(diǎn)和標(biāo)志;結(jié)合早年“七日格竹”的失敗經(jīng)歷,在工夫修養(yǎng)上否定了“窮理于萬物”,轉(zhuǎn)而化理為心,回歸到孟子“盡心知性而知天”的立場(chǎng)上來,開始掙脫程朱理學(xué)格致的桎梏,以個(gè)體的本心探求踐行德性、止于至善的真理。二是“貴陽講學(xué)”論述“知行合一”。正德四年(1509),王陽明應(yīng)邀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xué),開始提出并論述“知行合一”的觀點(diǎn),針對(duì)性地解決程朱理學(xué)“知行有先后,且相分互養(yǎng)”導(dǎo)致實(shí)踐上“兩張皮”相割裂的問題,將“行”作為合于“知”的指向,“知”作為成于“行”的依據(jù),以《大學(xu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為引證,闡釋“好色”“惡臭”乃本心使然不必再向外求“理”,肯定了“知行”在客觀層面的統(tǒng)一性,從形而上解決了實(shí)踐中知行互不統(tǒng)屬的矛盾問題;“知行合一”還體現(xiàn)在學(xué)、問、思、辨、行的具體操作層面,強(qiáng)調(diào)按照能事、解惑、通說、精察、履實(shí)的演進(jìn)邏輯,在做足“知”的工夫后進(jìn)入“行”才能達(dá)到“真知”與“篤行”的高度統(tǒng)一。三是晚年總結(jié)出“致良知”核心意蘊(yùn)。從其江西平叛治亂實(shí)踐可以看出,“致良知”是經(jīng)由“百死千難”的人生閱歷提煉的,即由實(shí)踐體悟自身具備的“良知”,再由“良知”與外部環(huán)境的磨合中獲取“良能”,將對(duì)道德理性的體悟認(rèn)知拉回到倫常日用、集結(jié)于心,使“良知”復(fù)歸于理性與實(shí)踐本身,成為融通體用兩界的統(tǒng)領(lǐng)且不斷精進(jìn),是對(duì)“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升華。
“致良知”這一核心理念的最終提出,植根于人生經(jīng)驗(yàn)的提煉總結(jié),處處體現(xiàn)儒家傳統(tǒng)的治學(xué)與治世的互動(dòng),“心即理”突破了程朱理學(xué)的羈絆,“知行合一”則為“獨(dú)善其身”或“兼濟(jì)天下”的修為踐行觀找到了著力點(diǎn),在其軍政實(shí)踐中逐步得以豐富飽滿,并提供治平家國天下的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這在具體處理軍務(wù)政務(wù)過程中重視安民養(yǎng)民的宗旨多有體現(xiàn)。
2.“宣教化”的漸進(jìn)路線
傳統(tǒng)儒家向來主張“為政以德”,養(yǎng)民教民往往立足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仁心”“仁政”,將面向廣大民眾深耕廣植作為士人道德實(shí)踐的理所擔(dān)當(dāng);歷代王朝統(tǒng)治維系也突出對(du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貫徹。《禮記·儒行》有言“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儀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明確以道義贏取天下歸心、以連接上天與生民,具體落腳則是對(duì)“德治”標(biāo)準(zhǔn)的把控及蓄養(yǎng)。
在王陽明“心學(xué)”體系里,同樣飽含倡導(dǎo)道德、廣施教化的價(jià)值追求,但其重心由程朱理學(xué)精英階層的定位擴(kuò)展至更加需要爭(zhēng)取和拯救的生民,以“化民善俗”為目標(biāo),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治安天下。如其所推崇的“良知”,實(shí)質(zhì)是強(qiáng)調(diào)主體道德的意志、情感對(duì)于世俗倫理事務(wù)支撐的重要性,有明以來“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huì)、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biāo)準(zhǔn)下維持長(zhǎng)治久安”1,此語雖有苛責(zé)之意,但對(duì)明朝治安追求的定義基本屬實(shí),在這種預(yù)定目標(biāo)的感召下,對(duì)教化功能的要求就比較高了,既要說明統(tǒng)治合法合理,更要爭(zhēng)取民心民意,內(nèi)憂外患皆充斥其中的明中葉,扶持人心成為“致良知”的主旨之一,在王陽明看來“修己治人,本無二道”2,“修己”是發(fā)見“仁心”的求索過程,“治人”則是推己及人、宣揚(yáng)正道的踐行過程。
“心學(xué)”向外推送的依據(jù)還是在于《大學(xué)》“三綱”對(duì)“親民”的解釋認(rèn)同,一定意義上“良知良能”代表著具備體認(rèn)踐行良知的、先知先覺先為的“圣人”,而普宣教化的重心則在于如何啟發(fā)愚昧、激起普遍的“仁心”“善行”。如前所述,王陽明在此發(fā)現(xiàn)了更加廣闊的空間,日本學(xué)者溝口雄三總結(jié)為“中國陽明學(xué)在歷史上第一作用就在于‘儒教的大眾化”3。王陽明本人的教學(xué)實(shí)踐就極為豐富,在書院講學(xué)、與弟子友人書信往來到戰(zhàn)后地區(qū)興辦社學(xué)等時(shí)時(shí)處處體現(xiàn)出對(duì)世道人心的關(guān)懷和導(dǎo)化。另外,他還時(shí)常鞭策學(xué)生切忌以高高在上的“圣人”形象示人,而要放低姿態(tài)以“同情”“同心”達(dá)到啟迪民智、發(fā)掘善行的目的。講學(xué)在陽明學(xué)派看來,更是天下治平的大事,為此他們不僅關(guān)注民間教育、參與鄉(xiāng)村建設(shè),更將時(shí)政融入講學(xué)內(nèi)容中,在幫助平常百姓尋找生活意義的同時(shí),賦予成仁成圣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
在其軍政實(shí)踐中,有一項(xiàng)穩(wěn)定秩序的代表性功業(yè)即是興辦社學(xué)、善化風(fēng)俗。這在平定叛亂之后,對(duì)社會(huì)秩序迅速恢復(fù)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如提督南贛軍務(wù)征橫水、桶岡、三浰時(shí),發(fā)布告諭總結(jié)出興亂的根源在于“風(fēng)俗不美”,明確善化風(fēng)俗作為治安首要;巡撫江西征寧王,發(fā)布 “興舉社學(xué)牌”等以安民教化,在規(guī)范地方治理上多有創(chuàng)制,而每每提到興辦學(xué)校、教化鄉(xiāng)里,都將民亂歸責(zé)于“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剿八寨,將興辦思田學(xué)校作為“用夏變夷”的方式,多了一些文化服務(wù)政治的功能意味。另外,強(qiáng)調(diào)要學(xué)有定制以免人去政息,收到參事吳天挺建設(shè)書院的呈報(bào)時(shí),特意要求“置立文簿”,明確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足見其從知學(xué)到興學(xué)的功力之深厚。
宣教化是王陽明將其“心學(xué)”作為改造世道人心的重要實(shí)踐路徑,從底層民眾移風(fēng)易俗到倡導(dǎo)心向光明,從歸化“新民”到戰(zhàn)后秩序恢復(fù),是以柔化的手法對(duì)踐行儒家“人性可塑”主張的具體落實(shí),盡管賦予了較為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從文化土壤的培植角度上,對(duì)妥善平穩(wěn)解決社會(huì)矛盾沖突提供了有力支持。endprint
3.“圖善治”的總體設(shè)計(jì)
從學(xué)理上看,“致良知”的提出為其實(shí)踐追求“仁心”提供了形而上的支撐,宣教化是“正人心”的必然取徑,最終落腳則在“圖善治”。可見王陽明開創(chuàng)的“心學(xué)”并不失于玄談,而是以實(shí)現(xiàn)“王道”政治為根本立足的。
“陽明心學(xué)”在“知行合一”上與程朱理學(xué)相較,不僅旨在破除“繼絕學(xué)”上說與做的剝離,更是將“知”與“行”在實(shí)學(xué)道路上做了開辟性的努力。浙東學(xué)派之所以在王學(xué)之后,明確提出經(jīng)世致用之學(xué),也是由此澆灌而來,“明清之際的經(jīng)世實(shí)學(xué)思潮具體表現(xiàn)為兩個(gè)方面:對(duì)理學(xué)的空談心性而言,主張經(jīng)世致用;對(duì)理學(xué)的束書不觀而言,主張回歸儒家原點(diǎn)”4。正如王陽明勸導(dǎo)一名主持訟獄的官吏所說“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shí)學(xué);若離了事物為學(xué),卻是著空”5,他極力主張做學(xué)問要落地在事上,砥礪磨練下工夫才會(huì)有所增益。因此,王陽明在體驗(yàn)中琢磨、在琢磨中踐行,推行善治上下了很多工夫。
大力改進(jìn)并推行“鄉(xiāng)約”。正德十二年、十五年,先后頒布施行“十家牌法”及“南贛鄉(xiāng)約”,其中“南贛鄉(xiāng)約”目標(biāo)直指戰(zhàn)亂后民眾的教化治理,采取建立鄉(xiāng)約的辦法穩(wěn)定鄉(xiāng)村社會(huì)秩序,進(jìn)而完善治理模式,以懲惡揚(yáng)善的旗幟為號(hào)召,鼓勵(lì)鄉(xiāng)民在教訓(xùn)子孫、和順鄰里、互助協(xié)作、勸善誡惡等方面建立廣泛深厚的聯(lián)系,共同培養(yǎng)“良善之民”、化育“仁厚之俗”。整個(gè)鄉(xiāng)約共十六條,包括鄉(xiāng)官設(shè)置、責(zé)任義務(wù)、召集組織、彰善糾過、習(xí)俗禮儀等,基本囊括日常生活秩序的所有內(nèi)容,思路清晰、緊貼實(shí)際,最大限度地滿足治理需求,他“把鄉(xiāng)里體制、保甲制度同鄉(xiāng)約結(jié)合起來,構(gòu)建了一個(gè)集政治、軍事、教育功能于一體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共同體,形成了一套完備的農(nóng)村基層控制體系”1,在戰(zhàn)后建設(shè)方面探索出整套做法,對(duì)后世也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根據(jù)實(shí)際設(shè)置縣治及土官流官。針對(duì)“叛亂”區(qū)域涉及地域廣泛或是多府縣交織導(dǎo)致“權(quán)力真空”的情況,王陽明提請(qǐng)?jiān)O(shè)置新的縣治填補(bǔ)治理空缺,不僅實(shí)現(xiàn)了較短時(shí)間內(nèi)戰(zhàn)區(qū)亂象的恢復(fù),更是著眼于從根上解決治理困境。對(du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土官流官設(shè)置問題的處理上,表現(xiàn)出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tǒng)一的鮮明特點(diǎn),他認(rèn)為應(yīng)把握“順應(yīng)民俗、不違其宜”的原則,使人各得其所,將“特設(shè)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shì)”與“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相配合,不僅明確管理關(guān)系層級(jí),同時(shí)在朝會(huì)貢獻(xiàn)、襲授調(diào)發(fā)、稅賦征納、訟案處置等具體事務(wù)方面理順了相互之間依存共生、共建共管的關(guān)系,另外最大程度發(fā)揮監(jiān)管職能,根據(jù)需要特分設(shè)“土官巡檢”調(diào)諧其中,在運(yùn)轉(zhuǎn)體制上進(jìn)一步鞏固確保了治安的落地。
解民困體現(xiàn)“仁心”“仁政”。無論是戰(zhàn)前、戰(zhàn)中、戰(zhàn)后,在籌措用兵糧餉、彌補(bǔ)鹽政漏洞、改進(jìn)商稅征收以及對(duì)補(bǔ)救天災(zāi)人禍等方面,都體現(xiàn)了其體恤民情、施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巡撫江西征寧藩時(shí)曾發(fā)布“寬恤禁約”,充分體恤興兵革對(duì)民眾生產(chǎn)生活帶來的勞費(fèi),嚴(yán)令所屬各州縣官員“痛恤民隱”不得叨擾加重百姓負(fù)擔(dān),違者以軍法論處;在鹽政及商稅征收上,始終強(qiáng)調(diào)保障民生與預(yù)留軍費(fèi)的協(xié)調(diào)平衡,堅(jiān)決反對(duì)涸澤而漁,遵循“不加賦而財(cái)足,不擾民而事辦”2公私兩全原則。
(二)軍事思想基本特點(diǎn)
前文已述,王陽明正式開啟其軍事生涯,是在南贛平“盜匪”,其治軍練兵用兵思想多有創(chuàng)設(shè),內(nèi)容涉及選將用兵、整訓(xùn)精武、軍政協(xié)同、后勤保障等要素;在傳統(tǒng)儒家“治平觀”指導(dǎo)下,王陽明平叛治亂始終堅(jiān)持以養(yǎng)兵弭寇、長(zhǎng)治久安為根本,力求將軍事進(jìn)剿對(duì)民生的破壞降到最小。
1.注重“就地選練”的精兵思想
對(duì)于如何平定區(qū)域內(nèi)“民亂”問題,王陽明總結(jié)以往大范圍調(diào)兵得不償失的教訓(xùn),從節(jié)省兵力民力考慮,明確提出加強(qiáng)對(duì)當(dāng)?shù)匕傩盏木幘毼溲b,作為治安依憑;同時(shí),在培養(yǎng)選任將才方面指出要以“忠信”作為第一要義,甚至也可以有條件地任用稍有瑕疵的能征善戰(zhàn)之人。
在“足兵”方面,王陽明清醒認(rèn)識(shí)到征調(diào)客兵不僅靡費(fèi)甚重,更嚴(yán)重的是不能起到穩(wěn)定局勢(shì)的作用。他分析南贛形勢(shì)時(shí)認(rèn)為,之前每逢變亂都不加區(qū)別地花費(fèi)大量時(shí)間精力調(diào)動(dòng)土軍狼達(dá)的習(xí)慣做法是不可取的,一方面不僅勞民傷財(cái)、貽誤戰(zhàn)機(jī),平匪的過程也靡費(fèi)巨大;另一方面,一旦客兵撤離“盜匪”又會(huì)興風(fēng)作浪,容易陷入來回調(diào)兵而沒有效果的“怪圈”。對(duì)此,他認(rèn)為應(yīng)該從亂源上著手,破除習(xí)慣上對(duì)土軍狼達(dá)的依賴,立足當(dāng)?shù)匕傩战M織鄉(xiāng)勇、有所備御,才能不失機(jī)宜地解決好治亂反復(fù)的問題。為滿足戰(zhàn)訓(xùn)實(shí)際需求,本著“治眾如治寡”的兵法原則改革兵制,按照“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duì),隊(duì)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zhǎng)、協(xié)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yíng),營(yíng)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1的結(jié)構(gòu)編練鄉(xiāng)勇,形成號(hào)令統(tǒng)一、層層節(jié)制、上下相維的指揮協(xié)同機(jī)制,為后續(xù)作戰(zhàn)訓(xùn)練的運(yùn)轉(zhuǎn)展開提供了制度支撐。將才的揀選也是其精兵思想的應(yīng)有之義,早在“陳言邊務(wù)疏”中,王陽明對(duì)人才的儲(chǔ)備揀選就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看法,“八事”中首條便是“蓄才以備急”,認(rèn)為選用良將是制勝的首要,是決定國家治安命運(yùn)的大事,他大膽地提出“舍短以用長(zhǎng)”原則,從歷史上選任將領(lǐng)的實(shí)際來看,能打勝仗的將領(lǐng)大都有些瑕疵,他肯定備戰(zhàn)迎戰(zhàn)時(shí)可以“用過”,但也應(yīng)有必要的原則遵循“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2,而最重要的品質(zhì)還是要講求忠信,對(duì)有才能但僅為一己之私的還不如棄之不用。
揀選兵將、改革兵制僅僅是預(yù)備動(dòng)作,真正要形成戰(zhàn)斗力還是離不開實(shí)戰(zhàn)操演,王陽明對(duì)此深有體悟,將練兵的主要內(nèi)容概括為知節(jié)制、洽情意、建信義、齊心志,著力于集中操演戰(zhàn)陣、共同生活,練就紀(jì)律嚴(yán)明、高度協(xié)同、官兵友愛的軍隊(duì),以達(dá)到“居則有禮,動(dòng)則有威”的目的。
2.堅(jiān)持“賞罰維信”的練兵用兵原則
行伍之間獎(jiǎng)懲公正嚴(yán)明、軍令政令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是順利圓滿達(dá)到戰(zhàn)斗目標(biāo)的有力保障,王陽明深知日常養(yǎng)成的重要,在操演時(shí)就申明法紀(jì)、獎(jiǎng)勤罰懶,樹立了很好的導(dǎo)向,其治下軍隊(duì)紀(jì)律嚴(yán)明、號(hào)令統(tǒng)一,得益于有功及時(shí)褒獎(jiǎng)、有過嚴(yán)懲不貸、以整個(gè)戰(zhàn)局為重評(píng)判功過等做法。endprint
戰(zhàn)時(shí)執(zhí)行軍法的標(biāo)準(zhǔn)更為嚴(yán)厲,如征剿橫水、桶岡時(shí)專門強(qiáng)調(diào)軍令共用了20個(gè)“斬”字,針對(duì)不同的情況規(guī)定非常細(xì)致,大到失誤軍機(jī)小到取人一草一木都在可斬范圍,考慮極其周詳甚至有些嚴(yán)苛;同時(shí),嚴(yán)令凡是臨陣對(duì)敵作戰(zhàn)單元之間必須相互策應(yīng)、協(xié)同行動(dòng),將官兵卒伍牢牢捆扎在一起,激勵(lì)官兵在作戰(zhàn)時(shí)建立信任和互為依靠,大大助益于增強(qiáng)部隊(duì)凝聚力。對(duì)違背既定行動(dòng)計(jì)劃的堅(jiān)決予以懲戒,但在戰(zhàn)局緊迫的時(shí)候,也會(huì)靈活處置,如漳南道守巡官有關(guān)軍事行動(dòng)不協(xié)同的問題,王陽明在評(píng)定時(shí)以整個(gè)情勢(shì)作為依據(jù)對(duì)涉案的指揮高偉等人予以懲戒,將各自功過情況條條分析,嚴(yán)格按照軍法論處,并嚴(yán)肅追究上級(jí)“督提欠嚴(yán)”的連帶指揮責(zé)任,但考慮到正值緊急用人之時(shí),便以“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來處理,以“大捷不計(jì)其小挫”作為激勵(lì),展現(xiàn)出準(zhǔn)確把握尺度的大將風(fēng)度。
平抑將士爭(zhēng)功同樣也能看出其維護(hù)軍令威信的決心。征剿南贛曾發(fā)生兵備僉事王大用與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圍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爭(zhēng)功打筆墨官司的事情。查明事實(shí)真相后,王陽明從整個(gè)戰(zhàn)局考慮,引導(dǎo)相關(guān)人等正確對(duì)待功勞,強(qiáng)調(diào)以協(xié)同配合作戰(zhàn)的成效作為考量軍功的首要,點(diǎn)出“獲級(jí)者匹夫之所能,爭(zhēng)功者君子之大恥”,激勵(lì)將士“同心易氣”,而不能因小功而失大體。王陽明深知“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quán)”3的道理,賞罰有信且公允及時(shí)才能發(fā)揮激勵(lì)人心、提振士氣、統(tǒng)一號(hào)令的作用;同樣,對(duì)于個(gè)人的功勛榮耀始終定位在自己的職分上,在成功平定寧王叛亂后他曾以兩次辭封“新建伯”的實(shí)際行動(dòng)做出了表率。
3.把握“剿撫并用”的治平準(zhǔn)則
王陽明平叛治亂雜于王霸之道,“仁政”“德治”無法施展時(shí),側(cè)重于武力征剿,條件滿足時(shí)則盡可能采用招撫教化舉措,始終秉持“樹德務(wù)滋,除惡務(wù)盡”的訓(xùn)誡。
平南贛時(shí),認(rèn)為“民亂”的根源在于百姓生計(jì)困難、官府腐敗不作為或處置不當(dāng)導(dǎo)致真盜真賊鉆了空子,認(rèn)識(shí)到有司濫用招撫是致使民眾無所適從、于盜賊不能起到震懾平抑作用的主要原因,因此王陽明每次平亂都是深入一線掌握實(shí)情,并多采用分化瓦解、化整為零的策略調(diào)控正面壓力,如推行“十家牌法”,整肅后方和穩(wěn)定內(nèi)部的同時(shí),起到了孤立盜賊的作用;平定寧藩時(shí),王陽明不濫施殺戮而大量投放“投首牌”,發(fā)布“安民榜”,承諾“惟首惡是問”,對(duì)心懷奸佞欲圖不軌的嚴(yán)懲不貸,對(duì)脅從人員則只要自首即可免罪,這種區(qū)別對(duì)待有效地瓦解叛軍、防止民變,更為極力減少平叛和戰(zhàn)后建設(shè)阻力打牢了基礎(chǔ)。
征討廣西思恩、田州以及斷藤峽、八寨,王陽明認(rèn)為兩廣變亂起于土官的相互仇殺,事關(guān)土官流官改制施行、治理矛盾日久不解的問題,而不能以寇賊興亂荼毒生靈來定性,更不能以單純軍事行動(dòng)征討解決,清醒地看到都御史提督軍務(wù)姚鏌雖通過武力征討擒獲反叛土官岑猛父子,但隨后又激起其部下盧蘇、王受再次擁兵造反以致兵敗束手無策的結(jié)果,認(rèn)為“自責(zé)自勵(lì),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nèi)治外攘而我有余力”才是根本,對(duì)之前單純軍事路線進(jìn)行了批判,明確整頓軍政、重樹威信、安撫百姓才是正道;隨后做出息兵罷餉、休養(yǎng)生息的柔化處理,除保留湖廣永順、保靖官兵防守城池,以待沿途糧草馬匹齊備后發(fā)回外,營(yíng)造了內(nèi)緊不忘軍備、外松安撫民心的氛圍,很快盧蘇、王受便請(qǐng)降了,這種不以殺伐建功的做法受到當(dāng)時(shí)及后人的褒獎(jiǎng)肯定。
4.著力“穩(wěn)固后方”的建設(shè)思想
王陽明三次受命征伐均展現(xiàn)出崇尚“伐謀”“伐交”的兵家智慧,在戰(zhàn)前部署、戰(zhàn)中運(yùn)籌及戰(zhàn)后建設(shè)方面,又表現(xiàn)出以體恤民情的善治為根本、實(shí)現(xiàn)“弭盜安民”最終目標(biāo)的儒者風(fēng)范。
平南贛過程中,出臺(tái)并大力推行“十家牌法”,以“家牌”為載體,登記每戶人數(shù)、房屋數(shù)、戶籍、姓名、年齡、職業(yè)、身體情況等信息,及時(shí)穩(wěn)定人丁,摸清底數(shù),采取類似“連坐”的方式促進(jìn)相互監(jiān)督,在戰(zhàn)時(shí)從制度上增強(qiáng)各家各戶聯(lián)絡(luò)、方便統(tǒng)一管理進(jìn)而“清理門戶”穩(wěn)定后方的同時(shí),也為戰(zhàn)后治理打牢了基礎(chǔ),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十家牌法”根本著眼還是在于營(yíng)造培養(yǎng)勸善懲惡、禮讓敦厚的民風(fēng),與隨后推出的“南贛鄉(xiāng)約”相協(xié)調(diào),使管理與教化相配合,很快就實(shí)現(xiàn)了安定生活、端正風(fēng)氣的目的。另外,注重及時(shí)應(yīng)對(duì)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如寧王叛亂前夕吉安十三個(gè)縣即已遭受旱災(zāi),寧王曾發(fā)布“偽命”減免稅負(fù)、收攬人心,軍事平叛初步完成后,百姓對(duì)減免稅賦的舉措無所適從、普生疑慮,王陽明憑借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及對(duì)戰(zhàn)后百姓疲弱情勢(shì)的體恤,認(rèn)為如果還要征收稅賦將很可能再次激發(fā)民變,為盡快穩(wěn)定民心、推動(dòng)戰(zhàn)后各項(xiàng)秩序恢復(fù)重建,立刻呈上“旱災(zāi)疏”提請(qǐng)“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yōu)免”,在面對(duì)第二年旱情有所加重而軍民未獲賑濟(jì)反追征賦稅的現(xiàn)實(shí),再次提請(qǐng)寬免兩年的錢糧稅負(fù)。
思恩、田州等地“叛亂”平定之后,基于不具體區(qū)分情況普設(shè)流官激起民變的現(xiàn)實(shí)認(rèn)識(shí),及時(shí)提出“益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shè)流官以制其勢(shì)”1的對(duì)策,即設(shè)流官知府與土官知州相結(jié)合、輔之以土官巡檢的方式,解決順?biāo)炫c管理的矛盾;同時(shí),王陽明也清醒地看到“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無法確保“流官”之制能有效施行的實(shí)際,采取“以其所以處之之道”發(fā)揮目長(zhǎng)、父老子弟等良善之民的示范帶動(dòng)作用管控“頑鈍無恥之徒”,確保社會(huì)生活秩序的總體平穩(wěn)。
(三)心學(xué)與兵學(xué)的融通
傳統(tǒng)儒家在構(gòu)建理論時(shí)即是文修武備的設(shè)定,而起支撐作用的便是“仁愛之心”。所謂“文修”即是要以民為本,其方法路徑即為廣泛施行愛民、養(yǎng)民、教民、治民和保民的各種政治;所謂武備,在儒家看來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對(duì)象僅僅是討伐叛逆的“有限戰(zhàn)爭(zhēng)”,即“只是在國內(nèi)或在各民族內(nèi)有叛亂不靖時(shí)始行軍事的討伐”2。王陽明謹(jǐn)遵先賢教誨,用務(wù)實(shí)的軍事政治相結(jié)合的手法來追求長(zhǎng)治久安,較為妥善地解決了治民、保民的現(xiàn)實(shí)問題。
1.基于“仁道”的用兵之道
王陽明戎馬生涯多用“奇正”“虛實(shí)”取勝,深諳兵家“先勝”之道,在摸清敵情、站穩(wěn)腳跟之后再謀兵制勝,靈活運(yùn)用“詭道”平亂的同時(shí),依然遵循“仁道”“仁心”以治亂,以最小的代價(jià)爭(zhēng)取最大的勝利、穩(wěn)定治理秩序,以致后人評(píng)價(jià)“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1。endprint
從其軍事實(shí)踐過程及效果來看,用兵之道與“仁道”得到了很好的融通,始終以“仁道”為最高原則,運(yùn)用“詭道”指導(dǎo)戰(zhàn)事也是適可而止。平定南贛,感念體恤兵荒馬亂給尋常百姓帶來的生計(jì)之困苦,多次發(fā)布“告諭”以安民心;對(duì)待“賊匪”同樣做到“仁至義盡”,大都是將武力鎮(zhèn)壓放在收拾人心之后;選練民兵提出“資裝素具,遇警即發(fā),聲東擊西,舉動(dòng)由己;運(yùn)機(jī)設(shè)伏,呼吸從心”2的設(shè)計(jì),以備戰(zhàn)事展開隨機(jī)應(yīng)時(shí)、運(yùn)用純熟,表現(xiàn)出對(duì)“虛實(shí)”技巧的駕馭;領(lǐng)兵直擊橫水,注意把握地勢(shì)、示形久屯,而又趁其不備、奇襲取勝,表現(xiàn)出對(duì)“奇正”的靈活運(yùn)用;清理橫水“匪寇”,分設(shè)奇正二哨,在大霧掩護(hù)下分進(jìn)合擊悉數(shù)剿滅匪巢;進(jìn)攻桶岡謹(jǐn)遵“善戰(zhàn)者,其勢(shì)險(xiǎn),其節(jié)短”訓(xùn)誡,避敵鋒芒、休兵養(yǎng)銳,發(fā)布告諭招降納叛分化敵軍、集中力量進(jìn)襲頑抗之?dāng)常宰钚〉膫鰮Q取了最大的勝利。平寧藩攻打南昌部署十三支部隊(duì)于七座城門,其中六支作為夾擊的機(jī)動(dòng)部隊(duì),總兵力共計(jì)3.4萬余人,據(jù)統(tǒng)計(jì)“除了屯守部隊(duì)之外,于陣前殺敵的僅有一萬四千人”3,體現(xiàn)出其善用“寡兵”的藝術(shù)和技巧,也是其以“仁道”統(tǒng)兵打仗在確保戰(zhàn)勝基礎(chǔ)上盡可能愛惜兵力民力的直接體現(xiàn)。
2.“破心中賊”與“破山中賊”的難易
王陽明認(rèn)為:一方面在軍事行動(dòng)上誅滅反叛很容易,較之安撫人們心中不安分的心才是最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基于善治的“寬政”要與具備威懾力的軍事行動(dòng)的“猛糾”相配合才能達(dá)到安民養(yǎng)民的主旨。為此,他秉承孔子“寬猛相濟(jì)”的訓(xùn)誡,軍政實(shí)踐中也往往在“收拾人心”上著力最多。
“破山中賊易”是對(duì)其軍事實(shí)踐成效顯著而論的。王陽明提督南贛、征討寧藩、平定思田八寨等總能化險(xiǎn)為夷,其中對(duì)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運(yùn)用純熟固然是因其平時(shí)在兵學(xué)上所下的工夫,更是將修煉心性與從軍從政實(shí)際相統(tǒng)一的結(jié)果。王陽明提出“四句宗旨”,是在久經(jīng)沙場(chǎng)戰(zhàn)陣、官場(chǎng)政治考驗(yàn)而成就功業(yè)的基礎(chǔ)上“修成正果”的,是其“心學(xué)”體系構(gòu)建完成的重要概括,正如日本陽明學(xué)者岡田武彥所說“王陽明在中年時(shí)并沒有從曲學(xué)阿世的觀念中擺脫出來。但晚年當(dāng)他以‘致良知為學(xué)之宗旨以后,便把一切雜念統(tǒng)統(tǒng)拋在腦后,并在此基礎(chǔ)上建立起獨(dú)自的心學(xué),最終奠定了明學(xué)”4。在他看來,“破心中賊”難就難在“收拾人心”,必須在“四句宗旨”上長(zhǎng)久下工夫,才能真正“知善知惡”以致實(shí)踐“為善去惡”,達(dá)到良知良能,而重難點(diǎn)在于對(duì)“仁心”“仁道”“仁治”的覺知篤行;“破山中賊”王陽明始終堅(jiān)持以上三者合一,從修為心性起步,在軍政實(shí)踐中體會(huì)如何“破心中賊”,如平定思田,認(rèn)為“民亂”興起是沒有遵從“民惟邦本”的根本原則,無論是設(shè)置流官還是土官均已失掉“善治”的本心,功利化、程式化、簡(jiǎn)單粗暴的治理方式使得“仁治”本意打磨殆盡,因此他認(rèn)為要行善治必先擇善治之人才,結(jié)合邊夷實(shí)際,緊抓順應(yīng)民心,明確提出選人用才要用“忠實(shí)勇果通達(dá)坦易”、“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耐其水土”三者兼?zhèn)涞姆€(wěn)健練達(dá)之人;隨后的興建學(xué)校、教化百姓等舉措,則是基于為后任者打下“收拾民心”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的長(zhǎng)遠(yuǎn)考慮。
3.以安民養(yǎng)民為目標(biāo)的“吊民伐罪”思想
遙承孟子“仁心”之道的王陽明,非常清楚興師討伐對(duì)“治平天下”的功能作用,更明白要以“仁道”來約束征討行為,始終秉承“敬天保民”的傳統(tǒng)治世理路,以“吊民伐罪”“解民倒懸”作為宗旨,將軍事行動(dòng)落腳在安民養(yǎng)民這一根本目標(biāo)上。
王陽明兩次奉命出征平定“民亂”分析社情民情,在歸責(zé)上都在于有司的不作為、慢作為、胡亂作為上,認(rèn)為安民養(yǎng)民做的不足不到才是關(guān)鍵所在,因此興師問罪的主要對(duì)象僅僅是加重社會(huì)動(dòng)蕩和矛盾的首惡分子,并不為難百姓,相反總是能夠體恤民情,盡可能安撫之;在軍事征討結(jié)束后,緊接著便在追求善治上下工夫,如根據(jù)需要添設(shè)郡縣、疏通鹽法解決民生問題、發(fā)布告諭勸勉從善安撫“新民”等,從用人才、革制度、興教化著手,竭力改善百姓民生和解決治理方面的頑癥痼疾。平定寧王之亂更是高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道義大旗,常以“竊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作為感召激勵(lì),盡最大努力調(diào)動(dòng)所有能夠調(diào)動(dòng)的力量;即便是在上疏處置從逆官員時(shí),從“仁心”“仁政”出發(fā),提請(qǐng)“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跡之堪憫者,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1,有效避免處置從逆、脅從的擴(kuò)大化,展現(xiàn)出過人的智慧和圣人的情懷;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擒獲寧王首惡的當(dāng)天,王陽明還上了一道“旱災(zāi)疏”,隨后其治下又發(fā)生水災(zāi),以沒有盡到人臣之職分而自劾罪己,切實(shí)在戰(zhàn)后建設(shè)恢復(fù)秩序上傾注大量心力,足見其安民養(yǎng)民的決心意志。
三、軍事實(shí)踐及思想對(duì)當(dāng)時(shí)及后世的影響
兵學(xué)與儒學(xué)的交融互動(dòng),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就已發(fā)端,儒家在梳理其學(xué)說時(shí)從根上并不排斥否定戰(zhàn)爭(zhēng),而是將征伐列為宣揚(yáng)“王道”“仁政”的工具來解讀,兵學(xué)在自身的演進(jìn)路徑中,也有綜合吸收諸子學(xué)說的印記,其中在政略上對(duì)尋找形而上的意義更多源于儒家。歷代治亂興替中,政治與軍事相輔相成的融合過程從未間斷,從西漢武帝確立儒家思想統(tǒng)治地位以來,至王陽明對(duì)傳統(tǒng)儒家“慎戰(zhàn)”“備戰(zhàn)”思想進(jìn)行了傳承和發(fā)揚(yáng),始終不離“天下歸仁”的命題,對(duì)兵家“安國全軍”“令文齊武”思想運(yùn)用純熟,賦予更多“弭盜安民”的政治倫理意味,在戰(zhàn)爭(zhēng)觀念、戰(zhàn)略思維、治軍安民等方面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yuǎn)的影響,建構(gòu)“心學(xué)”體系時(shí)將兵學(xué)與儒學(xué)的融合在實(shí)踐上大大推進(jìn)一步。
(一)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影響
1.平叛與治亂結(jié)合實(shí)現(xiàn)長(zhǎng)治久安
王陽明一生的軍事實(shí)踐主要有“三征”,基本路徑是武以戡亂、文以安民,在此過程中,盡可能做到“文武兼修”,力求長(zhǎng)治久安,對(duì)南方政局穩(wěn)定起到重要作用。
從實(shí)際效果來看,著力解決明廷長(zhǎng)久以來治民不善的問題,如平南贛時(shí)針對(duì)性提出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添設(shè)縣治以順民心民意、圖永安永保,先后提請(qǐng)?zhí)碓O(shè)建立平和縣、崇義縣、和平縣,他認(rèn)為這是“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的“長(zhǎng)策”,分析“民亂”反復(fù)的根源在于縣治不力導(dǎo)致民不聊生,生動(dòng)地將征剿比喻為“針?biāo)幑ブ沃健保鴮峋嘲裁褚暈椤帮嬍痴{(diào)養(yǎng)之道”,兩者應(yīng)該并行并立才能確保不生禍患。不僅如此,他始終將設(shè)立學(xué)校作為善化風(fēng)俗的必要舉措,認(rèn)為“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后,尤益存恤”2,否則將前功盡棄、悔之晚矣。在設(shè)縣治的態(tài)度上,他是非常謹(jǐn)慎的,經(jīng)常深入一線實(shí)地考察選址,選任官員堅(jiān)持“諳曉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為”的用人標(biāo)準(zhǔn)。endprint
從方式方法上看,緊抓民生問題以安民心。如平定寧王,因?qū)幫踟澅苫囊愿鞣N方式搶占、賤買、抄收百姓田地、山塘、房屋等,以致民無棲身之所、無用鋤之地,嚴(yán)令將侵占的房屋、田地等歸還本主;同時(shí),嚴(yán)禁各屬豪強(qiáng)借機(jī)強(qiáng)買強(qiáng)賣強(qiáng)占,援引《尚書》“守邦在眾”、《周易》“聚人者財(cái)”,認(rèn)為安邦首先要安民、安民必須要散財(cái),只有百姓生計(jì)得以維持,國祚才能保全;痛感“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對(duì)發(fā)生叛亂地區(qū)的賑災(zāi)、減免稅賦放在了“弭災(zāi)變”“立民信”的高度。
從管理重心上看,圍繞打牢治理根基著手,采取大力推行“十家牌法”“南贛鄉(xiāng)約”“興辦社學(xué)”等系列舉措,不僅在戰(zhàn)時(shí)極大地凝聚調(diào)動(dòng)了人力、物力、財(cái)力,更在實(shí)際運(yùn)轉(zhuǎn)中改善基層治理問題,如其“心學(xué)”取徑向內(nèi)、向下一樣,他將主要精力投放在最基層的管理單位上,極大地解決了當(dāng)時(shí)鄉(xiāng)村面臨的“自組織”形態(tài)松散、事實(shí)上管理缺失的問題。
2.以正心、攻心為上的制勝機(jī)理
王陽明始終關(guān)注“世道人心”,即是落腳在以良知為內(nèi)核,導(dǎo)引出“仁心”“仁政”拯救天下蒼生,其善于明理以正人心、攻心以瓦解敵軍,著眼于從根上破解“禍亂相尋于無窮”的惡性循環(huán)。
正因?yàn)椤昂笫懒贾畬W(xué)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為陰邪之術(shù)……;外假仁義之名,而內(nèi)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shí),詭辭阿俗,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zhǎng)”1的現(xiàn)實(shí),他認(rèn)為有必要從力行工夫致良知的根本上做起,而平叛治亂的過程也始終以正心、攻心為上。如前所述,征討南贛無論戰(zhàn)前準(zhǔn)備、戰(zhàn)中運(yùn)籌還是戰(zhàn)后重建,王陽明均善于穩(wěn)定人心、分化敵軍,充分證明了他不僅深諳兵法,更是對(duì)心戰(zhàn)運(yùn)用純熟,在“告諭浰頭巢賊”中,從常理常情說明被安上“盜賊”的名分是人所不欲的,對(duì)因官府所迫、大戶所侵導(dǎo)致錯(cuò)起反叛之心表示遺憾和同情,深知這種為情勢(shì)所迫的“民亂”絕不是出于本心,以父母對(duì)待子女總有不忍之心來說明“不得已而興兵”的事實(shí),最后發(fā)出“痛哉痛哉”的感慨,總的來看,這篇告諭流露出其仁厚赤誠之心,除卻分化“盜賊”考慮外,更多的是明理以正人心。
寧王叛亂,王陽明奉命興“仁義之師”征討在道義上爭(zhēng)取最大支持,收復(fù)寧王老巢南昌城時(shí)便使用了“攻心”戰(zhàn)術(shù),發(fā)布告示點(diǎn)明懲辦首惡主旨,不累及城中百姓,勸勉安撫民心,盡管因?yàn)槭爻钦呶唇邮艽烁媸径鴽]有發(fā)揮實(shí)際作用,但其抓準(zhǔn)時(shí)機(jī)的敏銳不得不令人稱道,以“伐謀”“伐交”的“安國全軍”最大限度減少損失的手法,同樣出自“仁心”的引導(dǎo),具備這種戰(zhàn)略思維很大程度上減省了征伐過程及安定戰(zhàn)后秩序的成本,達(dá)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3.政治與軍事的相維協(xié)同
王陽明從軍生涯鮮明特點(diǎn)之一便是用政治思維解決軍事問題,每當(dāng)臨危受命征討叛逆時(shí),總是從政治的角度闡釋“民亂”起因、分析敵我情勢(shì)、發(fā)布告諭告示安撫軍心民心、熟練運(yùn)用傳統(tǒng)儒家“治平天下”大戰(zhàn)略思維指導(dǎo)戰(zhàn)爭(zhēng)、倡導(dǎo)順應(yīng)民情普興教化,統(tǒng)一官軍民思想的同時(shí),最大限度贏得人心、減少平叛治亂的阻力。
提督南贛軍務(wù)時(shí),以奉公守法、去患安民、協(xié)力濟(jì)難、竭誠報(bào)國為感召勸勉各屬,將“弭盜安民”作為臣子的職分激勵(lì)同僚勇?lián)厝危辉诮忉屚菩小笆遗品ā睍r(shí),發(fā)布告諭稱推行此牌的根本目的在“剪除盜賊,安養(yǎng)小民”,采取的是防間革弊、保安良善的不得已之法,并以移風(fēng)易俗的教化作為切入收拾民心,達(dá)到了清除間諜、穩(wěn)固后方的軍事目的。巡撫江西征寧藩時(shí),發(fā)布“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yīng)”,開篇便擺出高舉義旗姿態(tài),直接點(diǎn)明“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雖然當(dāng)時(shí)還不是專責(zé)軍務(wù),依然從道義上號(hào)召各屬;鄱陽湖大戰(zhàn)在即時(shí),仍堅(jiān)持打“政治牌”發(fā)放“投首牌”最大限度分化瓦解敵軍;戰(zhàn)后告諭“頑民”時(shí),充分曉之以理、動(dòng)之以情,同時(shí)也檢討官府在落實(shí)“十家牌法”不得要領(lǐng)而引起了混亂的“三失”,但出于“不忍人之心”,不情愿用進(jìn)剿的手段行“不教而殺”之事,依然要為“頑民”留下改過的余地。平定思田時(shí),曾多次強(qiáng)調(diào)要將政治招撫與軍事剿滅相結(jié)合,在“湖兵進(jìn)止事宜”中,明確要求一線官兵區(qū)別對(duì)待“亂民”,嚴(yán)禁濫殺無辜,覓得可以不使用武力平復(fù)的時(shí)機(jī)后,本著“不違農(nóng)時(shí)”、愛惜民力、節(jié)省兵力的原則,除安排必要的守備力量,將兵屯悉數(shù)放回,在攘亂一經(jīng)結(jié)束緊接著便是“一記組合拳”,興辦學(xué)校、推行鄉(xiāng)約、賑濟(jì)軍民,迅速安撫軍心民心、恢復(fù)戰(zhàn)后秩序。
在王陽明看來,面對(duì)“頑匪”當(dāng)剿則剿,毫不手軟,但更重要的是要爭(zhēng)取戰(zhàn)后安定民心,從政治上維持整體平穩(wěn)才是“王道”,總歸于軍事手段的有限控制與政治治理的無限延展相維相用,著力解決治亂反復(fù)的根源問題。
(二)對(duì)后世的影響
總的看,王陽明在德、功、言上均有創(chuàng)設(shè),而他從軍從政所形成的一整套做法,可以說與明朝惡劣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有莫大關(guān)系,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士大夫群體,在明中期以后與“暴政”“荒政”做斗爭(zhēng)時(shí),逐漸養(yǎng)成不能“得君行道”退而求“覺民行道”的轉(zhuǎn)變1,或者是爭(zhēng)取“得君”重推“覺民”的融合;同樣也為“心學(xu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提供了土壤,王陽明“心學(xué)”與其事功在當(dāng)時(shí)程朱理學(xué)遍天下的環(huán)境下,多被世人詬病,然而儒學(xué)本身具備的“實(shí)學(xué)”精神在反思檢討與重構(gòu)的過程中也被激發(fā)出來,這種精神及實(shí)踐的路徑為明朝后期以戚繼光為代表的“儒將”、乃至晚清曾國藩等“中興”名臣所吸納借鑒,對(duì)明清兩朝的統(tǒng)治維護(hù)和修補(bǔ)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
1.對(duì)明后期以戚繼光為代表的“儒將”的影響
至明朝后期,儒學(xué)在“陽明心學(xué)”的澆灌下對(duì)兵學(xué)的反哺改造,已從戰(zhàn)爭(zhēng)觀、戰(zhàn)略指導(dǎo)滲透到治軍作戰(zhàn)等軍事實(shí)踐中,一方面,治軍領(lǐng)兵的將領(lǐng)大都有比較扎實(shí)的儒學(xué)理論功底且受到陽明后學(xué)的影響較深,具體作戰(zhàn)甚至效仿王陽明平叛治亂的整套做法;另一方面,涉及練兵、選將、作戰(zhàn)等具體內(nèi)容時(shí),將儒家忠信、仁義、安民等貫穿始終,培育發(fā)展出練膽、齊心、愛兵、保民等檢驗(yàn)軍事實(shí)踐成效的重要指標(biāo)。
與戚繼光齊名的俞大猷(1503—1579),是當(dāng)時(shí)杰出的將領(lǐng),他早年入私塾讀書,十五歲考中秀才,師從《易》學(xué)大家蔡清的弟子王宣、林福、趙本學(xué),養(yǎng)成豪邁正大、機(jī)敏好學(xué)的品格學(xué)風(fēng),在趙本學(xué)引領(lǐng)下由《易》入兵、融會(huì)貫通,打磨出較高的文人風(fēng)骨及武人韜略;世襲百戶之職,后武舉會(huì)試中進(jìn)士,以署千戶守御金門,注意運(yùn)用儒家詩書禮儀興教化,與當(dāng)?shù)匕傩战V泛聯(lián)系,深得民心,身為武官治理成效卻勝于文官;征討安南莫登庸父子時(shí),俞大猷上疏主張大兵壓境造勢(shì)下應(yīng)以伐謀攻心為上,果然莫氏父子不戰(zhàn)而降,印證了俞大猷是富有政治頭腦的將領(lǐng);前后抗擊倭寇十余年,其軍事思想散見于《正氣堂集》《洗海近事》等著作,總結(jié)提出練兵首在練膽氣、重在練技藝,兩者相得益彰;思想訓(xùn)練方面注重“申明忠孝大節(jié)以化導(dǎo)之,使心知乎親上死長(zhǎng)之義”2,這些做法幾乎都被戚繼光借鑒和發(fā)展。endprint
戚繼光(1528—1588)是明中后期較為典型的“儒將”,盡管是將門出身,但早年師從治學(xué)嚴(yán)謹(jǐn)、崇尚德行的儒生梁玠,受到“陽明心學(xué)”的浸淫,主要事功是南抗倭寇和北備邊防,根據(jù)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撰寫實(shí)用性和操作性很強(qiáng)的《紀(jì)效新書》《練兵實(shí)紀(jì)》,在后世廣為推崇和流傳。其在軍事實(shí)踐中倡導(dǎo)“正心術(shù)”、“身體力行”與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遙相呼應(yīng),是“心學(xué)”在軍事實(shí)踐領(lǐng)域貫徹落地的開創(chuàng)者。主要特點(diǎn):一是主張就地揀練兵士。負(fù)責(zé)寧波、紹興、臺(tái)州三地軍務(wù)時(shí),上書“練兵議”分析當(dāng)時(shí)大范圍調(diào)動(dòng)舟師兵勇但“兵無節(jié)制,卒鮮經(jīng)練,士心不附,軍令不知”對(duì)平定倭寇治亂起不到實(shí)際作用的現(xiàn)實(shí),提請(qǐng)就地揀選浙士三千。二是以“正心術(shù)”為“練將”的首要。援引往古時(shí)練兵用兵根本之法,認(rèn)為練就“仁義之師”的基本功在于“練心”,將“仁義出自吾心”作為“練將”的首要條件和基本要素,明確提出“光明正大,以實(shí)心行實(shí)事”,“忠君、衛(wèi)國、敬人、強(qiáng)兵、愛軍、惡敵”等重要指標(biāo),對(duì)將領(lǐng)“良知”考察與訓(xùn)練進(jìn)行了量化,高度重視練就剛勁穩(wěn)固的內(nèi)心。三是借鑒王陽明推行的“連坐法”。以嚴(yán)刑峻法作為增強(qiáng)官兵相互信任、相互支撐的保障,強(qiáng)化卒伍之間的協(xié)同與配合,在“申連坐”中強(qiáng)調(diào)“把總—哨官—旗總—隊(duì)長(zhǎng)—隊(duì)兵”層層節(jié)制,每級(jí)以上一級(jí)作戰(zhàn)效果為判斷獎(jiǎng)懲依據(jù),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陣型遠(yuǎn)比匹夫之勇重要,嚴(yán)令“殺賊只是萬人一心,強(qiáng)者不得先進(jìn),弱者不得遲后。如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jìn),即斬賊首、得賊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1。四是講求“氣和心齊”。負(fù)責(zé)北部邊防期間,結(jié)合在南方抗擊倭寇的練兵經(jīng)驗(yàn),糅合兵儒兩家理念整理《練兵實(shí)紀(jì)》,對(duì)“治眾如治寡”的理解貫徹,始終強(qiáng)調(diào)“氣和則心齊”,本著知兵愛兵的初衷,要求主將要像父母那樣“常察士卒饑飽、勞逸、強(qiáng)弱、勇怯、材技、動(dòng)靜之情”2,才能真正練就心齊氣和、作戰(zhàn)有力的卒伍。
以俞大猷、戚繼光為代表的“儒將”在練兵備防作戰(zhàn)實(shí)踐中,直接或間接受到“陽明心學(xué)”啟發(fā)影響,講求兵家謀略制勝的同時(shí),都富有儒家政治頭腦和治平精神。客觀講,在面臨比王陽明更加復(fù)雜多變、內(nèi)外交困的局勢(shì)時(shí),他們不僅在軍功上有所突破,對(duì)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系統(tǒng)總結(jié)提煉并以條令實(shí)操的形式固定下來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事實(shí)上對(duì)兵儒交融提升到一個(gè)新的高度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
2.對(duì)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晚清“中興”名臣的影響
經(jīng)過明朝中晚期“陽明心學(xué)”的洗禮,至明末清初經(jīng)世致用之學(xué)已初現(xiàn)端倪,以顧炎武、黃宗羲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對(duì)萬歷中期以后“心學(xué)”崇尚空談、純修心性的總體趨勢(shì)進(jìn)行反思,轉(zhuǎn)向傳統(tǒng)儒學(xué)“修齊治平”由內(nèi)而外取徑的回歸,至清晚期,逐漸打造出以曾國藩為代表的“衛(wèi)道士”士大夫群體像。這種實(shí)學(xué)回歸對(duì)晚清從軍從政辦理實(shí)務(wù)上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以曾國藩為代表在面對(duì)晚清內(nèi)憂外患危局時(shí),以更加務(wù)實(shí)的姿態(tài)編練新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yùn)動(dòng)、呼吁振興程朱理學(xué)對(duì)抗“異端邪說”,以軍事與政治相配合“雙管齊下”,實(shí)現(xiàn)了晚清統(tǒng)治“借尸還魂”、迎來所謂“同治中興”。
曾國藩(1811—1872)作為公認(rèn)晚清“文臣領(lǐng)兵”的代表,承接戚繼光治軍練兵作戰(zhàn)的“衣缽”,將“治心”推廣到“治軍”的各項(xiàng)實(shí)務(wù)當(dāng)中,在用儒學(xué)“包裝”兵學(xué)、以儒統(tǒng)兵上走得更遠(yuǎn),系統(tǒng)用儒家“仁”“義”“禮”“法”等命題賦予兵家“制勝之道”形而上的意義。在論述“將材”時(shí),將忠義血性作為“帶兵之人”所必須具備的政治軍事條件,主張要從忠義誠樸的儒生士子中挑選骨干;在選兵問題上,延續(xù)了戚繼光專揀樸實(shí)之人的傳統(tǒng),為便于純凈風(fēng)氣,提出要多用“樸實(shí)而少心竅之人”,將觀人觀心之道用于揀選兵士,從根上斷除威脅士心不一、難于運(yùn)籌的可能;在“治心”方面,提出“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于錢財(cái)之外者。后世將弁,專恃糧餉重優(yōu),為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為已淺矣”3,不應(yīng)該單純?cè)阱X糧上收買兵心,而要以仁愛之心善待士卒,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齊心”,將“練心”“提氣”作為選任治軍帶兵之人兩個(gè)缺一不可的支點(diǎn);事功方面主要是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yùn)動(dòng),以深諳“陽明心學(xué)”治心治軍之法的“理學(xué)”出身兼濟(jì)經(jīng)世致用的實(shí)學(xué)相協(xié)調(diào),最大限度的發(fā)揮出“理學(xué)”的執(zhí)著精神和隱忍特質(zhì),謹(jǐn)遵“先勝后求戰(zhàn)”訓(xùn)誡,強(qiáng)調(diào)穩(wěn)扎穩(wěn)打、步步為營(yíng),如1859年,在面臨石達(dá)開率軍進(jìn)入浙江、福建,后又轉(zhuǎn)戰(zhàn)贛南而使江西處于三面受敵的不利情勢(shì)時(shí),他提請(qǐng)收攏兵力集中攻打景德鎮(zhèn)以穩(wěn)固南岸,為進(jìn)軍安慶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攻下重鎮(zhèn)安慶后,采取“積小勝為大勝”的策略扎扎實(shí)實(shí)在“天京”外圍做清理工作,最后集全力一舉合圍,產(chǎn)生摧枯拉朽的效果。
與曾國藩并稱的胡林翼(1812—1861)也是當(dāng)時(shí)“文臣領(lǐng)兵”的典型,出身書香門第,幼承家學(xué),道光二十七年入職貴州,早期多任知府以鎮(zhèn)壓為主,他主張“用兵不如用民”,推行保甲以團(tuán)練親兵抵御“匪寇”和維護(hù)治安,強(qiáng)調(diào)嚴(yán)懲“首惡”的同時(shí),恩威并施、普興教化,為后期加入湘軍奠定了實(shí)踐和理論基礎(chǔ);鎮(zhèn)壓太平軍時(shí),努力經(jīng)營(yíng)湖北成為曾國藩堅(jiān)強(qiáng)的后援,選才強(qiáng)調(diào)“謀野則獲,謀邑則否”1,認(rèn)為鄉(xiāng)野士民多樸實(shí),能實(shí)心做事,堅(jiān)決不用油滑、畏縮之人,同時(shí)推崇以氣節(jié)為重,用“公心”來“齊心”,認(rèn)為“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2才能堪當(dāng)大任;治軍練兵方面貫徹嚴(yán)明軍法與仁愛治軍相結(jié)合的路子,明確指出“經(jīng)制嚴(yán)明,方有條理”3,借鑒湘軍營(yíng)制頒布詳盡章程規(guī)范軍旅之事,除了嚴(yán)格軍令,他還善于依托湘軍特殊的招募方式用情將將,以對(duì)將領(lǐng)日常的關(guān)心照顧籠絡(luò)人心。
應(yīng)該說,在王陽明、戚繼光的主要影響下,曾、胡開創(chuàng)發(fā)展了湘軍模式,也通過軍政實(shí)踐培養(yǎng)出了湘軍群體,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對(duì)清廷有再造之功,同時(shí)本著傳統(tǒng)儒家本身具備的“實(shí)學(xué)”精神,在實(shí)務(wù)上開啟近代化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逐步將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來“師夷長(zhǎng)技以制夷”自強(qiáng)御辱的設(shè)想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shí),盡管有限但在事實(shí)上開了風(fēng)氣。
On the Academic Value and Influence of Wang Yangmings Military Thought
Ding Tao Zhong Shaoyiendprint
Abstract: Wang Yangming founded the "Mind Philosophy" system,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Discussion on his military practice in Jiangxi and Guangdong and Guangxi,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nity of Confucian "administer state affairs well and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and "keep a country at peace and an army intact" of military strategists,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arkness and sluggish folk custom, the "military exploit" and "governance merits" of parallel appears to have a unique style. Moreover, these practice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later generals and scholars, such as Qi Jiguang and Zeng Guofan.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Mind Philosophy; Military Science; Syncretic
作者簡(jiǎn)介:丁 濤,1982年生,湖北襄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橹袊鴼v代軍事思想。
鐘少異,1963年生,浙江平陽人,研究員、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yàn)橹袊娛率泛蜌v代戰(zhàn)略。
1 王玨:《王守仁<武經(jīng)七書評(píng)·孫子>略論》,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huì),《孫子兵法與和平合作發(fā)展——第九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huì)論文集》,軍事科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627頁。
1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九,別錄一,奏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286頁。
1 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上冊(c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頁。
2 朱承:《治心與治世——王陽明哲學(xué)的政治向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頁。
1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60頁。
2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四,文錄一,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頁。
3 溝口雄三:《兩種陽明學(xué)》,李曉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第251頁。
4 王杰:《論明清之際的經(jīng)世實(shí)學(xué)思潮》,《文史哲》,2001年第3期,第110頁。
5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三,語錄三,傳習(xí)錄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頁。
1 王金洪、郭正林:《王陽明的鄉(xiāng)村治理思想及其實(shí)踐體系探析》,《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9年第4期,第15頁。
2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九,別錄一,奏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頁。
1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十六,別錄八,公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頁。
2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九,別錄一,奏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頁。
3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十三,別錄五,公移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頁。
1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十四,別錄六,奏疏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頁。
2 徐培根:《中國國防思想史》,中央文物供應(yīng)社1983年版,第136頁。
1 張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五,列傳第八十三,王守仁(冀元亨),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170頁。
2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十六,別錄八,公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7頁。
3 岡田武彥:《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xué)智慧》中卷,錢明審校,楊田、馮瑩瑩、袁斌譯,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頁。
4 岡田武彥:《王陽明與明末儒學(xué)》,吳光、錢明、屠承先譯,錢明校譯,重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
1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十二,別錄四,奏疏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頁。
2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十,別錄二,奏疏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頁。
1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二,語錄二,傳習(xí)錄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頁。
1 余英時(shí):《宋明理學(xué)與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8年版,第179、181頁。
2 楊健、謝鋼編:《中國兵書集成》第四十冊(cè),大同鎮(zhèn)兵車操法,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頁。
1 戚繼光撰:《紀(jì)效新書》(十四卷本)卷之十,實(shí)戰(zhàn)篇第十,范中義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03頁。
2 戚繼光撰:《練兵實(shí)紀(jì)》卷之二,練膽氣第二,邱心田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3頁。
3 蔡鍔輯錄:《曾胡治兵語錄》,胡賢林、譚動(dòng)良譯注,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7-8頁。
1 胡林翼:《胡林翼全集》中冊(cè),卷一,大東書局1936年版,第1頁。
2 蔡鍔輯錄:《曾胡治兵語錄》,胡賢林、譚動(dòng)良譯注,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3頁。
3 汪士鐸編篡:《胡文忠公撫鄂記》,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60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