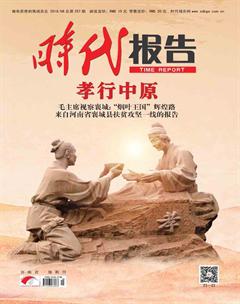政策調整不宜大水漫灌
顏色 郭凱明

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公布以來,宏觀政策層面出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微妙調整。7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穩健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同日,中國人民銀行開展5020億元一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規模相當于降準0.5%,為有記錄以來單日最大;加之月初央行再次降準,貨幣政策似乎趨于寬松。
此前,7月20日,金融機構資管新規細則落地,較4月資管新規和市場預期也有所調整和緩和;近期央行還通過調整MPA考核和窗口指導等方式鼓勵銀行信貸投放和投資信用債,監管方面也顯現寬松跡象。
在此背景下,圍繞著宏觀經濟政策是否將發生重大轉向,市場各方觀點不一,爭論熱烈。
國內外環境出現新變化
在國內環境方面,上半年經濟穩增長壓力加大,去杠桿政策背景已經不同于去年。去年一方面國內杠桿率整體偏高且上升較快,影響了金融系統穩定性;另一方面消費和出口需求回暖,全年GDP增長6.9%,實現了2009年以來全年經濟增速首次回升。因此,在去年持續推進去杠桿不但非常必要,而且國內環境也比較有利。
但是,今年上半年經濟表現并不盡如人意,去杠桿環境有了轉變。盡管上半年GDP實際增長6.8%,總體增長較為平穩,但GDP名義增速持續回落到9.8%,為最近6個季度以來首次降至10%以下。消費增長9.4%,增速回落到個位數,其中5月單月增速下降至8.5%,為15年來最低;投資累計增速持續下行,上半年增長6.0%,低于去年同期2.6個百分點。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宏觀經濟政策偏緊有關。上半年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速大幅回落至7.3%,其中5月和6月當月分別僅增2.3%和2.1%。這既說明財政政策遇到了明顯阻滯,也反映了PPP和棚改投資積累的隱性債務造成了地方政府謹慎支出。另一方面,金融監管趨嚴導致金融機構表外資金持續回歸表內,實體經濟流動性也趨緊。6月M2同比增長8.0%,增速降至歷史最低。6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1.18萬億,盡管較5月腰斬的新增社融規模有所回升,但仍顯著低于預期。其中表外融資持續下降,6月單月下降6916億,降幅環比擴大2701億。
國際環境方面,3月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引發金融市場波動劇烈。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對實體經濟影響仍然可控。
首先,美國對我國34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征25%關稅,接下來預計加征關稅的160億美元和2000億美元產品也沒有超過此稅率。關稅提高影響的是邊際價格,而中國出口產品替代率低、需求價格彈性小,受價格因素影響相對有限。加之中國出口企業經營靈活性高和人民幣快速貶值,這些都意味著中美貿易摩擦對出口的影響將遠低于實際加征關稅的出口額。
其次,去年我國對美國出口近5000億美元,拉動我國GDP增長0.64個百分點左右,2500億美元占比在50%左右,因此即使潛在加征關稅的這2500億美元產品全都不出口,也僅拉低GDP增速0.3~0.4個百分點。當然,如果未來貿易摩擦繼續升級,后續影響可能會擴大。

中美貿易摩擦對金融市場沖擊明顯。當前企業和金融機構杠桿率偏高,而金融市場在去杠桿政策下信用收縮,使得金融系統整體相對脆弱。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下投資者信心受損,投資和貿易不確定性增加,導致金融市場承受很大壓力。上半年上證股票總市值下降超過3萬億,A股股指下跌14.4%。貿易摩擦升級疊加美國經濟向好和美元走強,也造成了人民幣快速貶值。6月當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出現歷史最大跌幅,進入7月后也已貶至一年來最低。此外,今年以來違約債券數量和余額均較去年有明顯上升,債市違約風險也有所提高。
相機抉擇的合理性
財政政策方面,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財政將迅速發力。繼4月政治局會議提出“把加快結構調整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后,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提“擴內需”,并且首次將兩個“積極”放在一起表述,體現了財政擴張的堅定決心。
一方面提出要減稅降費,擴大稅收抵扣企業范圍,加快稅收返還進度;另一方面提出要加快地方專項債券發行和使用進度,督促地方盤活財政存量資金,推動在建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這將對下半年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起到提振作用。
此外,中央財政在民生方面也有望加快支出,推進建設和儲備一批對接發展和民生需要的重大項目,并通過調整養老、教育和醫療健康政策拉動內需。
貨幣政策方面,今年以來央行貨幣政策整體穩健,對金融去杠桿做了適度應急響應。央行今年三次降準和近期創紀錄MLF操作,關于流動性的表述已經由“維護流動性合理穩定”變為“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些均體現了央行對市場流動性的呵護。6月M0和M1分別增長3.9%和6.6%,分別較5月回升0.3個和0.6個百分點。SHIBOR和DR007利率維持了下行態勢,反映出銀行間貨幣市場流動性較為寬松。6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84萬億,比去年同期和上月增加3000億和6900億,居民和企業貸款也顯著回升,實體經濟貸款需求得到了一定支持。
金融監管方面,資管新規細則等監管政策有所緩和,有助于緩解信用緊張。與4月資管新規相比,新出臺的資管新規細則進行了調整,在產品凈值計算、新老產品對接、銀行整改過渡等方面,均提供了一定的緩沖期和靈活性。細則較之市場預期更為寬松,對消除市場不確定性、穩定市場情緒有著積極影響,也有助于前期處于觀望狀態的金融機構開展新業務。預計社融下降趨勢將得到緩解,非標融資的萎縮速度也會放緩。此外,央行近期還通過調整MPA考核和窗口指導等方式鼓勵銀行信貸投放和投資信用債,監管方面也顯現寬松跡象。
因此,無論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是金融監管方面,當前政策已經對經濟下行和信用收縮的潛在風險做了應對和調整,體現了應對變化宏觀局勢的一種政策相機抉擇的合理性。
大水漫灌已無法達到穩增長目標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高投資帶不來高增長。中國資本邊際產出持續走低,再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投資等大規模刺激政策,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非常有限。當前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增強,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上半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8.5%,比去年同期上升14.2個百分點。并且,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轉化,重新回歸大規模投資刺激模式,只會加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帶來諸多問題。
其次,中國經濟仍有諸多亮點,新的經濟增長動能逐步形成。一是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加快,上半年分別增長8.4%和6.8%,比去年同期分別高1.2個和1.3個百分點,其中6月增速均環比提高。二是工業企業生產平穩,企業利潤改善。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6.7%,利潤總額增長17.2%,均高于去年全年增速;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6.7%,比去年同期提高0.3個百分點。三是經濟結構持續優化,新動能增長較快。上半年服務業比重增至54.3%,比去年同期提高0.3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業的投資和增加值增速均高于整體工業增速,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光纖、智能電視等高技術產品產量保持了較快增長。因此,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依然穩健,實體經濟的問題更多是結構性問題,在總量上搞大水漫灌是無法解決的。
再次,中國宏觀杠桿率依然較高,繼續加杠桿將加劇金融風險。盡管去年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勢頭明顯放緩,增幅比之前5年年均增幅低10.9個百分點,但是杠桿率只是在高位上趨于了穩定,當前仍然高于250%,因此繼續加杠桿的空間并不大。并且,一些結構性債務問題依然存在,企業杠桿率、居民債務收入比等仍處于國際高位,PPP和棚改投資又導致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隱性債務。考慮到當前金融體系依然較脆弱,如果繼續快速加杠桿,短期可能會引發金融風險。
因此,重回加杠桿和大規模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舊模式不具備現實基礎,當前政策調整也并非以往的大水漫灌。財政政策上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務依然較高,財政支出空間有限,當前更多的仍是確保建設計劃更加有效執行,并未大幅加碼。貨幣政策上也只是邊際微調,央行松緊適度的政策取向沒有發生明顯轉變。此外,資管新規細則盡管有所緩和,但整體上并不改變嚴監管的大方向。
深化改革開放、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近期的政策調整體現了宏觀調控的連續性,只要保持定力、堅定信心,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適度的增長,今年全年GDP增長6.5%和金融市場穩定的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展望未來,由于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還存在著各種低效率的資源和要素錯配,深化改革開放、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仍是應對中國宏觀經濟困局的最優選擇。
一是繼續大力深化改革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和土地市場等,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加快中國增長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轉化。二是加強私有產權保護,加快個人所得稅改革,降稅不僅針對低收入群體,也應有效針對合法的中高收入群體的稅負過重問題,以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激發創新創業的企業家精神和活力。三是進一步落實開放,繼續提高能源領域和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程度,審慎推動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同時在知識產權和高科技領域擴大雙向交流,引領更深更廣的全球化進程。只要這些改革紅利能夠持續釋放,中國不僅能夠完成穩增長目標,而且實現三步走中的中長期戰略目標也是無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