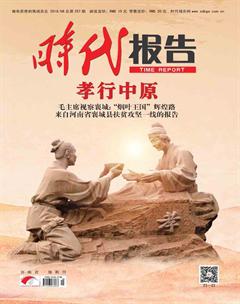劉慶邦:小說的細節之美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細節之美》。首先我個人認為小說是一種美學現象,或者說小說是一種以詞表意的美術。這就是說,我們寫小說是一種發現美、表現美的過程。我們讀小說也是一種欣賞美、享受美的過程。不論是讀,還是寫,它整個的過程都是審美的過程。
細節從哪里來
我自己總結細節是從這四個方面來的,我要一個一個來講:第一細節是從回憶中來。我認為一個人有三種基本力量,第一是體力,第二是智力,第三是意志力。這三種基本力量相輔相成,哪一種力量都不可缺少,你哪一種力量不強大,就成就不了什么事業。在這三種基本力量中,智力里我又把它分成三種力量,第一是記憶力,第二是理解力,第三是想象力。
我說細節首先是從記憶中來的。因為我自己認為寫小說是一種回憶的狀態,要調動我們的記憶。我們有了一定的經歷,一定的閱歷,有了很多的記憶,然后我們才會有可回憶的。應該說,記憶力對一個作家來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們沒有記憶力,沒有什么可回憶的,小說就不能進行。我們作家很大的責任,或者說很大的一個功能,就是為我們的民族保留記憶,通過作品為我們的民族保留記憶。一個人如果喪失了記憶力,這個人就是一個無用的人,或者說就是一個傻爪。我們的民族如果也喪失了記憶力的話,那是非常可怕的,可能重蹈災難的覆轍。
1960年我九歲,應該說那幾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得很不錯的,就是沒有收回來而已。我記得紅薯都長得這么大個,大紅薯頭,我們那兒一說紅薯長得個大就是長得像碓頭一樣。因為“大躍進”,頭天晚上,上面布置下來任務,說明天要檢查,明天這塊地要種上麥子。第二天上午公社就要來檢查了,收紅薯的時間只能在夜里進行。怎么進行呢?婦女把紅薯秧子薅薅,扔到炕邊,然后套上犁子,套上牛,犁一遍,根本顧不上出。一般我們出紅薯是用釘鈀出,出得很細致的。可是在那種大躍進的情況下,根本不顧這個了,用犁子一犁,大的紅薯骨轤轤的,婦女在后面撿幾塊,象征性地撿幾塊出來,收得很少很少。然后就開始耩麥子,第二天地上就插上紅旗了,說我們一夜就種上小麥了,然后檢查團來了。檢查團倒是滿意了,可到冬天就沒吃的了。餓得最慘痛的時候,想起來說:喲,那時候咱們的紅薯沒收,都在地里埋著呢,去看看有沒有。已經種上麥子了,紅薯早就爛在地里了,看著老鴰在地里飛來飛去,它在那淘壞紅薯。人看著老鴰在那淘,就追著老鴰去,一挖,就挖出壞紅薯來。壞紅薯也吃啊,不吃,人活不下去。那年我剛上小學二年級。我要翻過一個干坑去上學,那是1958年的時候,跑上跑下,如履平地。1960年,我餓得,不知道我是什么形象,反正肯定是頭很大,脖子很細,肚子很大,非常畸形的狀態。我們現在老在電視上看到非洲的那些孩子,都是細脖子,肋骨露著,我想我可能就那種形象。坑都爬不上去了,爬到半截又滾下來了。可以說就差點餓死,是這么一種狀態。
我父親就是1960年去世的,當然他不是完全餓死的,他得了一個病,腸胃炎。拉兩天肚子,很快就不行了。這些都給我留下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整天不斷有要飯的,要飯也要不到。食堂蒸的饃很小,說:食堂的饃,洋火盒,大人倆,小孩一個,再小的攤不著。都編成順口溜。這樣我調動我的記憶,寫了一個長篇——《平原上的歌謠》,是2004年的時候,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今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還要再版重印,他們要給我出一個長篇系列,包括《紅煤》《遍地月光》。通過我的長篇,把好多好多的事都調動起來了。如果我們不寫這個小說,很多記憶也許都埋葬了,都沒用,但我們一旦寫起小說,好像找到了一個抓手,記憶源源而來,細節也源源而來,都調動起來了,都成了活的東西。
所以我主張作家要多走多看,豐富自己的經歷和閱歷,這樣我們的記憶力才能有庫存,才有可挖掘的東西。我不主張還沒有什么經歷呢,甚至說還沒有什么可回憶的東西呢,就開始寫作。你沒有可回憶的東西,寫作至少是不豐富的、不厚重的。
第二,細節是從觀察中來。其實我們在以前的觀察,好多是無意識的觀察,或者說是不自覺的觀察,一旦我們想寫作就變成了有意識的觀察,自覺的觀察。觀察要求我們始終要保持一個好奇心,或者說要保持一個童心。你對什么事情都要有興趣,別人不感興趣的,你要感興趣,別人不愿意看的,你要把你的好奇心、童心調動起來看一看。我有好多的素材、好多的故事都是看來的。有的時候并不用問,不用采訪,是用心來觀察。我常說我們看東西不是用眼睛來看,是用心來看,要有心目,要有內視的能力,不但看自己,還要用心目來看世界,來看周圍的東西。
好多周圍的東西都是通過我們的看來觀察出來的。我舉個例子,有一次我走到學校門口,看到吹糖人的,一塊糖稀捏吧捏吧,一吹就成了孫猴子,吹成一個母雞。后來我再寫小說,寫到吹糖人的時候,我就用得著了。再比如有一年,我到一個煤礦住了一個星期,回來寫了四五個短篇,還寫了一個中篇,就看了那么幾天,看了以后,它主要是激發我的想象力,激活我的生活庫存,然后把很多過去的生活都調動起來,然后來進行寫作。
我到一個礦工住的地方去看,剛坐了一會,開門就進了一個女的,不打招呼,好像進自己的家一樣。我問:這是你老婆嗎?他說:不是。我說:她進你屋很方便啊。他說:都熟了嘛。通過這一個細節,我展開我的想象,然后又增加了很多的細節和情節,把它寫成了一個小說。我把她想象成的情節是:這個女的是另外一個礦工的老婆。那個礦工下井了,這個礦工就跟他老婆好上了,有情感上互相安慰,彌補一些性的饑渴。很溫馨的一種小說。我設計了一個情節,他的騾子受傷了。他對他的騾子感情非常深,給騾子起了一個名叫:火箭。“火箭”腿受傷了,他非常著急,他和那個女的倆人一塊帶騾子去找大夫看,這個女的丈夫說:沒用了,趕快把它賣掉,早賣還能賣個幾百塊錢,你越治越瘦,到最后也賣不到什么錢了。他舍不得,怎么也不忍心,把自己心愛的騾子賣到肉坊里去。這個女的就相當于他的相好,不說情人。他說:你去給我賣去。女的答應了,想想那不行,說我也不敢去。最后就讓她的丈夫去,因為他一直主張把這個騾子賣掉嘛。她丈夫牽著騾子去賣了。老板當時沒在,老板在后面一個小樹林里,正在那準備殺一頭騾子呢。殺騾子的過程是我到那個小鎮親眼目睹的。這個過程對我來說非常震撼,我知道這個素材用得著,以后會寫小說用它,但一直還沒有用上。在寫《騾子》的時候我把它用上了。殺騾子怎么殺呢?用一個破衣服把騾子的眼蒙上,因為騾子的力氣非常大,十幾個人還沒一個騾子的力氣大。拴到樹上以后,把騾子的眼蒙上,先用12磅的大錘打騾子的面門,把騾子打暈以后,趁騾子倒地的時候,用刀把騾子的脖子抹掉。整個過程非常殘忍。這個丈夫說:這太殘忍了,不是人干的事,怎么這么干呢!結果騾子沒賣,又把騾子牽回去了,他倆一看:喲,你怎么把騾子又牽回來了。他說:不行,不行,我受不了,不能這么干。通過這個事,他倆知道她丈夫也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從此以后這個小伙子不跟人家老婆偷情了。通過這件事情喚起了妻子對她丈夫的尊重,也喚起了自己人性的尊嚴。這么一個小說,結尾是升華的。
專業作家長期寫作,對素材的消耗量很大,很多細節我們都會用得著,在這用不著,在別的地方就會用得著。這就要求我們保持看的意識和看的狀態,要不然的話很多好的細節都會錯過去。
第三,我認為細節是聽來的。有時候你偶爾聽一耳朵,聽到一個細節,這個細節激發了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小說。我聽來的小說可以舉出很多很多。這個聽要求你首先要是一個有心的人,你的心是有準備的心,你的耳朵是有準備的耳朵。這樣,你聽了以后,腦袋才會記住,才會把它變成小說。如果你的心不是有準備的心,你聽了,只能是這個耳朵聽,那個耳朵冒,聽了跟不聽是一樣的。所以聽之前一定要有小說意識、細節意識,聽來的話才是有用的,有效的。如果不是這樣,你聽得再多,是無效的。
有一次我到山東煤礦采訪,那時我還在《中國煤炭報》當副刊部主任,去給一個煤礦做系列報道。從一個老礦區到一個新礦區去,他們送我,要走好遠。在車上司機隨便聊天說:咳,這小煤礦還給挖煤的發幸福票呢。我問:幸福票咋回事。咋回事?說給他發一張幸福票,讓他去找小姐。說白了就是讓他去當嫖客。一個月你能干夠25個班以上,就給你發一張幸福票。窯主說幸福票值300塊錢呢。其實所謂歌廳、發廊、洗腳屋也是窯主辦的,他給礦工發一張幸福票。通過這個回收礦工掙的錢。
我一聽這個能寫成小說。光聽這一耳朵,要把它變成小說還要設計很多情節、細節。我先把小說的名字叫成《幸福票》。它非常有反諷意味。然后我就設想,回憶。回憶和觀察是綜合的,不是說這個素材是回憶來的,那個素材是觀察來的,這個素材聽來的,很多都是綜合到一塊。我想如果我們村的一個人到小煤窯去挖煤,要給他一張幸福票,說這張幸福票值300塊錢。他怎么也舍不得去花掉這“幸福票”啊!這就有故事了。我想起老家有一個嬸子,叔叔死了好長時間,嬸子到兒子家輪著吃飯,都對嬸子不太好。嬸子的閨女來看嬸子,給嬸子提了雞蛋,都不給嬸子煮著吃。那時候雞蛋還是非常寶貴的東西。閨女拎的雞蛋,嬸子想數一數。在桌子上一打開手巾包,她忘了雞蛋是圓的。雞蛋一亂滾,她趕快往一塊收拾,還是有一個雞蛋掉到地上摔碎了。摔碎了以后,她心里很害怕,趕快把地上都弄得很干凈。她兒媳婦一回來,問:雞蛋怎么少了一個,誰吃了。嬸子說:反正我沒吃。沒吃?雞蛋怎么少了,就開始罵人。嬸子也開始賭咒,誰要是吃了,讓他不得好死。為了一個雞蛋鬧翻了天,這是我嬸子家發生的事。我就想:如果是她的兒子到礦上去打工,兒子會想到:我這300塊錢能買多少個雞蛋啊,怎么也舍不得去花這個幸福票啊。我設想他想把這幸福票兌換成現金,人不給他300塊錢,給他200塊錢,他也干啊。會計說:不行,這是讓你幸福的,你換成現金就幸福不了了。什么是票啊,票旁邊還有一個女呢!這不是票,是嫖。你知道吧。然后做了他很多工作,他還是舍不得,好多周圍的窯工有愿意花這個錢的,說不行你借給我,再發了幸福票我還給你。這里面好多的細節,細節上來就給它現場感,就以細節的形式出現。最后寫了八九千字吧,將近一萬字。
窯主發現有人偷印他們窯上的幸福票。過去的幸福票統統作廢,再發新幸福票。這個小伙子受打擊真大啊,整天掖著藏著,幸福票一個舍不得花。結果幸福票作廢了,又發了新的幸福票。原來印的是黑字,這回幸福票印的是紅字。這怎么辦?領了新幸福票以后,有了非常緊迫的感覺。這個幸福票怎么處理呢?這時小說就結尾了,留了一個懸念給讀者。我不能讓他一定去當嫖客,我要給他出一個難題,就給它來一個提問,看看他這個幸福票怎么處理。然后就留給讀者來思索。
《幸福票》給了一家刊物,這家刊物不敢發,說有點尖銳,有點沉重。給另一家刊物,另一家刊物說這沒問題,就發出來了。發出來以后,在國際上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德國很快翻譯成德語。年前去加拿大,他們也談到了《幸福票》,他們非常喜歡,認為是對現實的質疑。
第四,我認為細節是從想象中來的。我前面說到人的智力,我又把它分成三種能力,記憶力、理解力、想象力。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說想象力是一個作家的基本能力;想象力是小說創作的生產力。從我國的四大名著來看,《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每一部名著都離不開想象,都有想象在起作用。但是它們的想象又各有不同,我認為《紅樓夢》是個人的經歷加想象,也就是曹雪芹,他有貴族的體驗,有皇家的體驗,然后加上他的想象,成就了《紅樓夢》。《三國演義》是歷史資料加想象。《水滸傳》是民間傳說加想象。《西游記》的想象更豐富,它本身就有非常大的想象力,我認為它是幻想加自己的想象,成就了《西游記》。

不光是四大名著,我們每一個作品都有想象的成分在里面。剛才休息的時候,我給一個朋友題的字:信言不美。這是老子說過的話。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說藝術是需要想象的,藝術是需要虛構的。你把現實中的生活搬過來,它是不美的。這個意思梅蘭芳也說過,梅蘭芳說:不像不是戲,太像不是藝。這是強調虛構,強調想象力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說口技,它摹仿狗叫是很美的,但是你真正拉來一條狗,讓它在臺上叫,那就不美了。需要有個轉換,需要有個虛構和想象來把它變成藝術品。
好的小說包含想象多,包含想象越是多的東西,越是好的小說。它不是照搬生活,特別是寫短篇的時候,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結束的地方正是小說開始的地方。舉個例子來說,我有一個小說,叫《走窯漢》,是1985年在《北京文學》發的。北京的一個老前輩、老作家林斤瀾老師,特別喜歡這個小說。他認為這個小說是我的成名作,說我通過這個小說就走上了知名的站臺。這個小說是寫煤礦的支部書記把人家礦工的老婆誘奸了。這個礦工非常生氣,扎了書記一刀,沒把書記扎死,把礦工判刑了。判了多少年刑之后,把他放了出來,那時候放出來以后,還可以回到礦上繼續當工人。這個故事我就是從故事結束的地方開始的,從他出來繼續上班寫起,寫他向支部書記復仇。寫這么一個過程。設計的一些情節、細節非常緊張。他復仇,把刀子拿出來在那比劃,他又不扎他。他在澡堂老盯著支部書記的傷疤看,他采取一種精神拷問的辦法,要把支部書記的精神打垮。他帶著他的老婆老去找那個支部書記。因為支部書記被撤職了,他也是當一個普通的工人。有一次支部書記冒頂被煤埋住了,他把他扒出來,繼續折磨他,最后一直把支部書記折磨得精神垮了,精神弄得恍恍惚惚的,買一碗飯還沒吃呢,就扣到池里去了。終于有一天自己跳到窯里去,摔得粉身碎骨。他老婆聽說支部書記跳窯死了,她也從樓上跳下去了。當這個礦工聽說支部書記跳窯的時候,他沒有震驚,當聽說他老婆也自殺了以后,喲!他有點感到震驚了。本來是坐著的,一下站起來了,站起來,他很快又坐下了。八千多字的短篇,容量非常大的,就是他在向支部書記復仇的時候,等于把他的妻子也給傷害了。他傷害他的妻子也許是不自覺的,但是他老提起那件事情,老讓他妻子講支部書記誘奸她的細節,等于在不知不覺中把妻子的精神也摧跨了。這個小說從人性的復雜性、豐富性這個角度來寫。細節、情節是我虛構出來的。
情節可以想象,我自己認為細節也是可以想象的。好多作家的創作談里,認為情節可以想象,細節很難想象。如果你沒有見過,經歷過,細節是想象不出來的。但我的體會是細節也可以想象。有的時候我們寫東西會有寫不下去的時候,比如一個情節,我覺得寫一千字才能充分,才能表達我的思想,它的味道才能出來,可是寫著寫著覺得又沒什么可寫的,在這種情況下,有的作者往往會采取繞過去的辦法,把這個情節說過去就完了,能自圓其說就行了。我的體會是絕不能繞過去,絕不能偷懶。在覺得沒寫充分的時候,一定要堅持,調動自己的全部想象,全部的感官來參與自己的想象。這時候你的靈感會爆發,靈感的火花會閃現,你的腦子像打開了一扇窗戶。有時候自己為自己叫好,這就是勞動的成果,艱苦勞動后的靈感閃現的一種成果。
我遇到好多這樣的情況,后來我看自己的小說,凡是覺得閃光的地方,美好的地方都是堅持想象的結果。比如我的短篇小說《鞋》,因為這個得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讀者面稍稍寬一些。這個小說里面有一個細節就包含了我的想象在里面,得到那個細節以后,自己非常得意。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寫的時候陽光從窗子照進來,寫著寫著覺得需要有一個細節,才能使這個小說完整、飽滿和充實,但一時又想不起怎樣的細節。我暫時不寫,想啊想啊,突然覺得有一個細節爆發出來。我寫有一個未婚妻給她的未婚夫做鞋這么一個過程,在她想象中這個鞋已經做好了,她送給未婚夫,讓他穿一下試試,穿上以后,未婚妻問他:怎么樣?他說挺好,就是有點緊,有點夾腳。走了一圈以后,她又問:怎么樣?他說腳有點痛。這個女孩子說:你疼,我還疼呢!未婚夫問:你哪痛啊?她說:我心疼啊!有了這么一個細節以后,小說味道完全就不一樣了。女孩子說:新鞋子都緊,都夾腳,你穿了一段以后,時間長了以后就合適了。
這種細節除了它的情緒在里面,背后還有好多沒有說出來的文化內涵在里面,甚至包括鞋文化、性心理學,包括了很多語言背后的內容,這一下子就顯得美了,豐厚了,這樣的細節在小說中是非常重要的。自己寫了這個細節以后,就覺得非常得意。還有好多小說有類似這樣的細節,我都是奮力想象出來的。我聽到好多作家說小說寫完了,發表了就算完了,就不再看了,我不是這樣。一個短篇寫完以后,我不知要看多少遍。小說寫完了,我看;發表出來,我還要看;然后收到集子里出了書以后,我還愿意看。有時候看著看著自己淚濕眼眶。通過這樣的看,我對自己的小說會有一個判斷。如果小說放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還愿意看,還看得下去,我就覺得這個小說已經經過了時間的檢驗。說明這個小說藝術上是有價值的,是可以留存下來的。這是一個時間上的判斷。還有另外一個判斷,如果這個小說過去時間已經很長了,還看得我動情,看得我流淚,我覺得這個小說里面的感情的含量是存在的,或者說情感是飽滿的;是真實的,它能打動我的心,至少在表達感情上是成功的。其實我們寫小說就是表達感情的,通過語言也好,通過情節也好,通過細節也好,來表達我們的感情。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人是感情的動物。
怎么樣來使用細節
我們寫小說時寫不長,本來可以寫成萬字的短篇,或者寫成三萬字的中篇,寫著寫著覺得沒什么可寫的,也有情節,也有細節,就是寫不長。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會把細節寫細,沒有把過程拉長,沒有像日本的香道、茶道一樣把過程拉長,沒有把它細化。
怎么樣才能把細節寫細呢?重要的一點就是把細節心靈化,賦予細節心靈化的過程。世界上什么最細?先是海明威說:什么最廣闊,他拿天、地、海洋這幾個來相比,最后說人心最廣闊。我現在來說什么最細,我認為不是毫米,不是微米,也不是納米,人心最細,比納米還要細。所以,我們要把細節寫充分,就必須把它心靈化。你看我們好多好的小說都是心靈化的。我比較喜歡王安憶的小說,她把一個細節能寫好幾頁,她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心靈化的過程,在心靈化的過程當中找到我們自己的內心,找到我們自己的真心,也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心結合起來。找到自己的真心了,你才可能把細節心靈化。
寫小說的過程就是尋找自己的過程,尋找自己心靈的過程。也可以說你抓住了自己的心,就抓住了這個世界。我在別的地方講過,一個人到了這個世界上,當我們有了生命意識的時候,急于抓到什么?所謂生命意識其實就是死亡的意識。好多年輕人沒有生命意識,也就是沒有死亡意識,他覺得他們的生命還很長很長,路還很長很長,沒有考慮過生命的盡頭在哪里。人上了一定的歲數,有了一定的閱歷、經歷以后,他們的生命意識就增強了,死亡意識就增強了。人總是要死的,人的長度是非常有限的,人生不足百嘛,就這么幾十年。有了生命意識的時候,我們會心生恐懼,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當我們想到:我們將有一天在這個世界不存在了,什么都沒有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煙消云散了,這時候真挺可怕的,人生真是沒有意思,非常虛無的。當人心生恐懼的時候,就想抓住什么東西,像人掉進水里要抓住生命稻草一樣。
我們急于抓住的都是些什么呢?多是些物質性的東西,房子、汽車、金錢、美女,等等。這些物質性的東西我們抓來抓去到頭來我們什么都抓不到,是一場空,抓來抓去是一場空的。這個思想,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已經通過《好了歌》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說到金錢、妻子、權力、兒女,把世上所有重要的物質性的東西都提到了,最后他的觀點就是:好就是了。
那么,我們來到世上真的什么都抓不到嗎?我認為我們所能抓到只有我們自己的心。通過抓住我們自己的心來和這個世界建立聯系,再造一個世界,等于我們抓住了整個世界。曹雪芹就是通過《紅樓夢》的建造,抓住了整個世界。可以說,我們古往今來多少帝王將相都像過眼煙云一樣消散,曹雪芹因為有了《紅樓夢》,不管歷史的長河怎么來沖刷,《紅樓夢》會越來越散發出它璀璨的光輝,不會因為時間的過去,磨滅它的藝術光輝,隨著時間的推移,《紅樓夢》會越來越顯現出它的藝術光輝。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作家一種寫作的動力。我們想對自己的一生有所安慰,覺得自己的一生沒有虛度,只有通過這種辦法來抓住我們的內心,抓住我們的真心。通過抓住我們的心,抓住和世界的聯系,再造一個世界。
當然,我們作家不能都像曹雪芹一樣,有宏偉的構造,有這么大的建筑。但我們可以有小的建造,比如我們可以寫一篇散文,可以寫一封信,可以寫一首詩,可以寫短篇小說。如果有我們的真情流露,有我們的真心在里面,我們也等于抓住了這個世界。可以說能不能抓住自己的心,能不能把這個東西心靈化,是衡量一個作品是不是成功的很重要的標準。好多人寫了一輩子東西,沒有一樣東西是屬于他的。給領導寫了好多報告,起草了好多文件,這些東西不屬于他。有人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他是用自己的心寫的,里面有自己感情的容量在里面,那這些文字,就是屬于他的。因為這些文字已經打上了他的心靈的烙印,已經包含了他豐富的感情在里面。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字還是這么多字,就看我們怎么來使用它,怎么樣來心靈化,怎么樣來賦予它真情和真心在里面,然后就變成我們自己的。我們現在看一個東西,衡量一個人的作品,寫到什么樣的程度了,有時候我們看前面幾行,就知道他達到什么程度了。我們怎么判斷的?就看有沒有他自己的東西,有沒有個性化的東西在里面,有沒有他的真心、真情在里面。這個我們大家可以試一試。你寫他人,要進行反觀,找到自己,然后把這個細節寫長。這個長的過程就是一個心靈化的過程。
細節除了心靈化,還要有現場感。我們在寫細節的時候,容易回顧、容易交待,這些你不容易寫細,你給它一種現場感,就是現在進行時,容易寫細。我最初寫小說的時候,有編輯跟我說,寫小說其實沒有什么,就是簡單交待情節,大量豐富細節,重點刻劃人物,就這么三句話嘛。
這么久了,這三句話我也記住了,說得非常有道理。情節很簡單,細節很豐富,重點刻劃人物,要把人物立起來,人物很重要。在大量豐富細節時候,你要給細節一種現場感,現場的感覺容易把很多東西都調動起來,比如空間利用起來,時間利用起來,感官利用起來。我們在寫小說的時候,不僅是腦子在起作用,其實是我們所有的感官全部參與創作,要高度集中,包括視覺、味覺、觸覺,我們身上的感覺都要發揮作用。比如我們寫到下雨的時候,會聞到濕潤的氣氛,耳邊像聽到雨沙沙的聲音,皮膚會感到一種涼意,然后你全部的感官調動起來,才能寫細,才能把你的感覺傳達給讀者,才能感染讀者。
寫小說對體力都有要求。我說趁現在體力還不錯,能吃、能睡、還能喝點酒,敏感還保持著,不妨抓緊時間寫。每個人的生命有限,寫作的精力也有限。比如一個婦女她在生育的年齡,可以生出白白胖胖的孩子,過了生育期,再讓她生,那非常難了。果樹有掛果期,在掛果期它可以結很多果子,碩果累累,能壓彎枝頭。過了掛果期以后,它結的果子又小,也不圓潤,也不美。所以我現在寫東西抓得還是比較緊的。文壇把我叫成勞動模范,每年的大年初一我都起來寫東西,除夕大家看春節聯歡晚會看得很晚,有時候我也看,但是不影響我第二天早起。我的習慣是早上起來寫東西,第二天早上五點我準時起來,每年的大年初一我都是這樣。有人說:劉慶邦,你是不是要做一種姿態啊?我說我不是做姿態,我就是通過這件事情來考驗一下自己的意志力,看我能不能管住自己。
我為什么要強調意志力啊?一開始我說人有三種力量:體力、智力、意志力。意志力也很重要的,沒有意志力也很難成就一個東西的。人的智力差不多,如果沒有意志力做保證,一個東西堅持不下來,很難有所成就。我自己的體會是,一個人一生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錯,比如寫小說,我一生能把小說寫好就不錯了。這個就需要我的意志力做保證。意志力說白了就是志氣,就是人的毅力,人的韌性。好多人的才華是不錯的,也寫過不錯的小說,但由于他的意志力不行,寫著寫著很快就放棄了。這跟跑馬拉松差不多,跑馬拉松有時候需要意志力來起作用。作家的競賽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志力的競賽。沈從文說:一個人走上文學這條路并不難,難的是走一輩子,難的是走到底。走到底靠的是意志力。有人說你太不像話,太苦自己了。我說:其實不是,我寫的時候很痛快,你如果讓我不寫了,我就覺得不舒服,不痛快。我的寫作就是這樣一種狀態,不僅是一種精神的需要,也是身體的需要,甚至變成了生理上的需要。如果我幾天不寫東西,會覺得焦慮,好像吃得不舒服,睡得也不舒服,有時候還有無名火。但我一進入寫作狀態,馬上就很適應,吃得也好,睡得很好。小說開頭,我會在日記本上記一筆,我的小說已經開始了,進入了寫作狀態,真痛快!
大致的意思已經基本講完了,還有一點就是把細節詩意化。這一點跟儀式感是一個意思。我們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我們寫小說最高的境界是達到一種詩意的境界,詩意的境界我認為是最美的境界。把小說詩意化了,我覺得非常非常好。其實我的小說有兩個路子,一種是詩意化的寫作,一種是現實的、酷烈的小說,對現實介入比較深,像《神木》。《神木》拍成《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這種小說也要寫,但我自己最愛寫的還是那種審美的、詩意化的小說,我覺得這種小說最符合我自己審美的要求,也是我最愿意寫的東西,也更符合我自己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