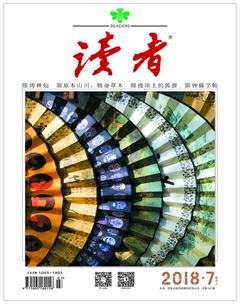戰(zhàn)爭中的日本人
魯思·本尼迪克特
每個(gè)國家的文化傳統(tǒng)中都有一套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正統(tǒng)理論。日本和西方戰(zhàn)爭傳統(tǒng)的差異全部體現(xiàn)在他們?nèi)绾慰创褪姑稀?/p>
日本為其戰(zhàn)爭合理性辯護(hù)的前提和美國截然相反,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與美國人不同。美國把戰(zhàn)爭歸因于軸心國的侵略性——日本、意大利和德國以一系列罪惡的侵略行徑打破了國際和平。但日本人對戰(zhàn)爭的起因持有不同看法。他們認(rèn)為,只要國家擁有絕對的主權(quán),世界就會(huì)動(dòng)亂不斷。因而日本需要通過戰(zhàn)爭來建立一個(gè)等級(jí)體系——當(dāng)然,是在日本的領(lǐng)導(dǎo)之下。日本在自己的領(lǐng)土上實(shí)現(xiàn)了統(tǒng)一與和平,他應(yīng)該去幫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國,把美國驅(qū)逐出去,其次是使英國和俄國“各就其位”。所有的國家將組成一個(gè)大世界,在國際等級(jí)體系中找到各自的位置。以上是日本創(chuàng)造出來的很符合其文化的幻想,可惜那些被它侵占的國家并不這么認(rèn)為。事實(shí)上,即便打了一些敗仗,日本也不愿意從道德上否定其大東亞理念。甚至連那些最沒有沙文主義傾向的日本戰(zhàn)俘,也很少去指責(zé)日本對東亞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qū)的野心。
日本人對勝利的信心也寄托在一個(gè)與美國主流觀點(diǎn)完全相反的基礎(chǔ)之上。“會(huì)贏的!”他們叫道,“這是精神對物質(zhì)的征服。”美國的確是個(gè)大國,軍事力量的確很先進(jìn),但這有什么關(guān)系?日本人表示,所有這些他們都預(yù)見到了,并沒放在心上。日本國民報(bào)紙《每日新聞》上說:“如果我們害怕這些數(shù)據(jù),這場戰(zhàn)爭根本就不會(huì)開始。”
當(dāng)日本連戰(zhàn)連捷的時(shí)候,其國內(nèi)的政客、指揮官和士兵們無不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這場戰(zhàn)爭并非軍備競爭,而是“信仰物質(zhì)”和“信仰精神”之間的較量。當(dāng)美國人打勝仗的時(shí)候,日本人又再三宣揚(yáng):在這場較量中,物質(zhì)注定會(huì)失敗。
當(dāng)然,和其他參戰(zhàn)的國家一樣,日本其實(shí)也是有顧慮的。在整個(gè)20世紀(jì)30年代,他們的軍事開支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等到偷襲珍珠港時(shí),日本將近一半的國家支出花在了軍事領(lǐng)域。日本并非像它說的那樣不在乎軍事裝備。它和其他各國的不同之處在于,其軍艦和槍炮只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現(xiàn)和象征符號(hào),如同武士佩帶的刀,其最終象征的是道德品行。
和美國一樣,日本為了這場戰(zhàn)爭不得不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生產(chǎn)制造,但同時(shí)有自己的一套指導(dǎo)思想。日本人認(rèn)為精神就是一切,精神永世長存;物質(zhì)當(dāng)然必不可少,卻處于次要位置,并會(huì)逐漸消亡。對精神的依賴成了戰(zhàn)爭中的行為準(zhǔn)則。日本戰(zhàn)爭手冊的第一頁上印著一行加粗的字:讀之必勝。冊子里有一句口號(hào):“以我們的訓(xùn)練成果對抗敵人的數(shù)量優(yōu)勢,以我們的血肉對抗敵人的鋼鐵。”
日本政府甚至在民間也推行“精神克服物質(zhì)條件”這一信條。在工廠連續(xù)工作12個(gè)小時(shí)并經(jīng)歷了通宵達(dá)旦的轟炸恐懼后,人們定會(huì)感到疲憊不堪吧?可政府卻對民眾說:“我們的身體越沉重,我們的意志、精神就越能超越它們。”人們在冬天的防空洞里會(huì)感到寒冷吧?大日本體育文化社在廣播中建議大家做暖身體操。他們認(rèn)為這種體操不僅可以代替取暖設(shè)備和被褥,甚至可以在食物匱乏、無法滿足人們?nèi)粘K璧臅r(shí)候代替食物。政府說:“當(dāng)然,有人可能會(huì)說眼下食物短缺,我們沒力氣做體操。不對!食物越短缺,我們就越應(yīng)該通過其他途徑來增強(qiáng)體力。”
戰(zhàn)爭時(shí)期的日本廣播電臺(tái)在這種問題的處理上更加激進(jìn)。他們甚至聲稱,在戰(zhàn)斗中,精神可以戰(zhàn)勝生理死亡。某個(gè)廣播電臺(tái)講述了一則英雄飛行員戰(zhàn)勝死亡的奇聞:
在空戰(zhàn)結(jié)束后,日本戰(zhàn)機(jī)以三架或四架的小編隊(duì)飛回基地。一個(gè)空軍大尉乘坐第一編隊(duì)的飛機(jī)返航。下飛機(jī)后,他站在地面上,用雙筒望遠(yuǎn)鏡注視著天空,一一清點(diǎn)歸來的部下。他看上去面色相當(dāng)蒼白,但又非常鎮(zhèn)定。等最后一架飛機(jī)歸來后,他填寫了報(bào)告單,走進(jìn)指揮部向指揮官做匯報(bào)。一匯報(bào)完,他就轟然倒地。在場的軍官急忙沖過去救他,但是……唉!他已經(jīng)死了。人們檢查后,發(fā)現(xiàn)大尉的身體已經(jīng)冰涼,胸口有一顆致命的子彈。剛死之人的軀體不可能冰涼,而大尉的身體卻如冰一般寒冷。大尉必定已經(jīng)死去好久了,是他的精神在做報(bào)告,是他強(qiáng)烈的責(zé)任心創(chuàng)造了這個(gè)奇跡!
對美國人來說,這個(gè)故事荒誕離奇、不合常理。但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日本聽眾不會(huì)嘲笑這則廣播,也不會(huì)把這個(gè)故事當(dāng)作天方夜譚。
日本人在戰(zhàn)時(shí)不斷表示:所有事情都在他們的預(yù)料之中,并且他們已做好一切應(yīng)對準(zhǔn)備。不管什么樣的災(zāi)難(對平民的轟炸也罷,在塞班島的失敗也罷,或者菲律賓失守也罷),日本政府總是對國民說這些都在預(yù)料之中,沒什么可擔(dān)心的。他們說:“美國對基斯卡島的占領(lǐng),使日本本土處于其轟炸圈內(nèi),但我們早已預(yù)見到這情形,并做了必要的準(zhǔn)備。”“毫無疑問,敵人會(huì)從海、陸、空全方位攻打我們,但我們的作戰(zhàn)計(jì)劃早已把這些情況考慮在內(nèi)了。”只有承認(rèn)一切都在預(yù)料之中并且做了充分準(zhǔn)備,日本人才能不斷強(qiáng)調(diào),所有這些都是他們主動(dòng)期待發(fā)生的,沒有人可以強(qiáng)加任何事在他們頭上。這樣的信念對日本人來說必不可少。
“我們不能覺得自己是在被動(dòng)地挨打,而要相信是我們主動(dòng)把敵人吸引過來的。”他們不說“最終該來的,還是來了”,而是說“我們在等的終于來了,我們歡迎它的到來”。海軍大臣在國會(huì)中引用了19世紀(jì)70年代偉大武士西鄉(xiāng)隆盛的教誨:“世界上有兩種機(jī)遇:一種是我們趕上的,另一種是我們創(chuàng)造的。哪怕在極大的困境中,一個(gè)人也必須給自己創(chuàng)造機(jī)遇。”當(dāng)美軍攻入馬尼拉市時(shí),電臺(tái)里說:“山下奉文將軍咧著嘴笑稱:‘?dāng)橙爽F(xiàn)在已落入我們懷中了。在敵軍登陸仁牙因?yàn)巢痪茫R尼拉市迅速陷落,這正是山下奉文將軍的策略,一切按照他的計(jì)劃發(fā)展。”換言之,輸?shù)迷綉K,反而越成功。
讓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是萬事已提前規(guī)劃好。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威脅莫過于不可預(yù)知的意外。
(摘自浙江文藝出版社《菊與刀》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