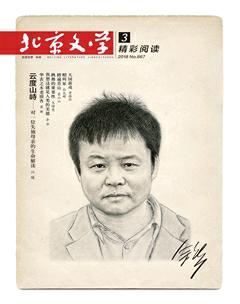書·記
海笑
風吹哪頁翻哪頁。
北漂的我,有點隨遇而安。漂泊十年,北漂七年。癢。抓癢的方式,看書。前些天,還和多年不見的老同學爭吵來著。他說:人的命運是上天注定的。我不信命。然而我相信人的孤獨是與生俱來的。北漂,風起云涌,物是人非。許多人來了,又走了。一個廚師去法國做刀削面。一個網管回家去創業。一個編曲音樂人被家人洗腦搞直銷。一個無名詩人自殺。一個大姐瘋了。一個做兼職時認識的搬家的工友腰傷了沒錢住院。一個玩玉的兄弟得了絕癥,很久沒有消息了……
“天下,暫時相聚,忽然云散水空流。”
北京似乎留不住我的兄弟朋友。唯有書,常相伴。可是我來北京的時候,只有一本《凡高自傳》。還是借大學同學的。
淘書記憶
小時候淘氣。長大了淘書。淘書,我上中學就開始了。周末趕大集,別的孩子買吃的,我淘書。例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大厚小字本,黃土顏色封面。“人啊,忍,韌,仁”。五個字,寫一生。
大學受紅柯老師影響,更喜歡淘書。很多舊書店,是沒有店名的。關門后,外面看,就像是工地房。有時偶遇紅柯老師。紅柯老師一看就是書店常客,操著方言向店主說,學生沒啥錢,算便宜哈。紅柯老師經常會引薦一些冷門的圖書,《君王論》《熱什哈爾》……“當古老的大海朝我涌動迸濺,我采擷了愛慕的露珠”,紅柯老師后來寫到了他的小說里。
和一些愛淘書的老同學,為了新的發現,經常走得很遠很偏僻。一走就是一天。我是如此的喜歡走長路。老同學問我:路是沒有盡頭,以后你會去哪里?當時真沒想過。畢業十多年,老同學們工作、成家。我一個人,自從淘了一本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竟然真的走遠了。老同學問我何時“收心”,我竟無言以對。就像我《流浪貓》唱的:下一秒,我在哪兒?某街道?某荒郊?
曾經有一個笑話。一個人生病瞧大夫,說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不進夜店,問還能活多久?醫生說你那么無聊,何必活那么久?我心說這個大夫,一定不懂得有書的快樂。愛書的人,淘到好書,怎么會無聊呢?
前兩年,北京有舊貨市場,還有舊書的攤位。特價書店自不必說。每年更有一年好幾次的地壇書市、朝陽公園書市,很是熱鬧。
說來我也是傻。第一次轉地壇書市,因為要收門票,我自作聰明,把地壇公園繞行一圈,以為有圍墻就有缺口,能逃票。就像顧城當年去老動物園,為了給蠶寶寶求桑葉,滿處找翻墻地兒。地壇,是什么地方?結果,自然是沒有。
一年年的書市,貴了。舊貨市場,慢慢拆了,沒了。舊書成了收藏書。盜版、翻印、電子版,加速了圖書的消失。便宜還想有的看的,推薦潘家園舊貨市場。市場邊角處。不貼邊兒走,不問熟人,不會發現。書市只有周六日兩天開放。有多便宜?一兩塊錢。比如,卡內蒂《迷惘》就是我兩塊錢淘來的。
淘書,吃飯,錢從何來?
剛來北京時,不想找工作的我,只想兼職鐘點工,自由。例如,我發過一個月送餐的傳單,十元一小時。老板精明,幾百張傳單厚厚一沓,發完為止。于是兩個多小時,領到十塊錢。當時北京公交卡四毛錢起步,往返八毛錢。早餐一碗粥、一塊餅,兩塊錢。有時老板心情好了,管一碗熱湯掛面,不要錢。中午地攤,豆芽燜面三塊錢。晚飯,一個戧面饅頭、一包榨菜,一塊錢。
每周六日,淘書錢,就是這么來的。
我平時不戴眼鏡。日常,誰也不知道,不相信,我近視五六百度。公交潘家園橋西站下車后,淘書前,我會鄭重其事地打開像是盛放金銀首飾的、包裹著大紅色絲綢的長盒子,取出我的金絲近視眼鏡,斯文戴上。卻不顧斯文掃地,蹲在每一個書攤前,眼睛逐行掃描每一排整整齊齊碼著的書,手里扒拉著攤主故意放亂的,干脆從蛇皮袋子呼啦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堆書。挑所需,選所愛。有的書臟,只好如馬克西姆《出埃及記》那樣,拍落、吹落塵土。青蛙一樣蹲著,爬啊爬啊,從頭爬到尾,西排到東排。不知不覺,閉店音樂響起,那是薩克斯的《回家》。
地下人間
書越來越多。和許多北漂一樣,為了省錢,我住地下室。半地下室有巴掌小窗通風透氣。地下二層的純地下室不見天光,白天懂得夜的黑,最適合看書。我這地下室,幾年下來,不知不覺,書就堆了單人床那么長寬,兒童票那么高。沒書柜,全在地上,辛苦了地下室的除濕機。夏秋季節,地下室除濕機大多在我屋里。轟鳴聲里,盛放排水管的臉盆,魔術一樣,無中生有。看不見的水蒸氣,成水滴,成水流,滴滴答答,童子尿一樣細細長長。學生時代,說某同學,麥當勞里就可以看書學習。我不行,嗅覺靈敏,餐館看書會饞。不過地下室看書,機器響動,不影響我。我可以像《浮生六記》那樣隨時想象。我有聚斯金德的《香水》、有夏目漱石的《貓》、有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有米什萊的《山》《海》《鳥》《蟲》……天下萬事,盡在書中。
北漂書攤
不想當上班族,何不擺個書攤?
北京歡樂谷附近,我成了第一批擺地攤的人。
書攤簡單,一個大媽買菜用的那種行李車,一二十本書,一張床單。賣幾本,第二天加幾本就是了。擺了書攤,知道了擺攤的辛苦。春有沙塵秋雨風,夏有蚊子冬有雪。
書攤沒什么生意。一個文身哥們兒,代步車飛馳而過時,旁邊手機貼膜大哥說話一針見血:有錢的不看書,看書的人沒錢。
擺書攤,和其他地攤一樣遭遇城管游擊戰。隨時敵進我退敵退我進。自從有了我的書攤、幾個襪子攤點后,歡樂谷附近的傍晚比集市還熱鬧:烤地瓜的爆米花的、假箱包的、假名包的、賣保健品從頭發絲到腳后跟包治的、打底褲男女老少高矮胖瘦都能穿的……
垃圾遍地,吆喝大喇叭擾民。幾經舉報,城管幾次突擊圍追堵截下,“歡樂谷集市”終于消失,只留想念。
圍城姑娘
圍城姑娘,是光顧我書攤最多的書客。
姑娘清瘦,短發整齊。簡單黑色或素色調衣褲。不戴耳環項鏈。皮膚很好,剝了皮的荔枝一樣。
姑娘面容姣好,舉止卻有幾分男人的大大咧咧。我書攤沒有坐的地方,姑娘絲毫不介意地上干不干凈,街頭雅不雅觀,鋪書攤的床單一角,姑娘盤腿就坐。翻了這本看那本,看了品相看譯本。經常聊天得知,姑娘是電力公司的。地攤鄰居那里得知,姑娘有自己的黑色小轎車。除了我的書攤,其他地攤她從不光顧。
姑娘對我出手也大方,品相不是太差的,每次幾乎打包全買,勸我可以早點回家。
我知道姑娘是在照顧我的生意。文學名著是普通家庭常備的,何況這樣一位愛書勝過打扮的姑娘。我的反射弧一定太長。面對這么好的姑娘,我當時沒有動心。每每想來,覺得沒有進一步交流實在遺憾。姑娘一定是單身,因為現在回憶起來,我推薦的書,她從沒有反對意見。唯有錢鐘書《圍城》,她堅持拒絕。她說她不想還沒走進圍城,就去念及圍城外的好。我可能一再傷害了姑娘。我說這本書寫得很好,我這本品相版本也好。另外我過分直接地說,我的藏書沒有二十五史那樣的成套系列古典。即使有,也不會賤賣。
圍城姑娘,后來,再也沒有相遇。
圍城姑娘,如今你是否走進圍城?如今你是否幸福安好?
白胡子大爺
白胡子大爺,胡子和洪七公同款。
白胡子大爺不是買書的。白胡子大爺說,他觀察我好幾天了。大冷天,實在是看不下去了。一邊命令的口吻對旁邊的兒媳說,把家里那個羽絨服拿來,我能穿他就能穿。
白胡子大爺轉身進了京客隆超市,很快出來,提了一大袋饅頭,和六連包大分量的方便面。
白胡子大爺兒媳住得不遠,羽絨服很快拿來。接過饅頭方便面,穿上羽絨服,我心里熱乎乎的。我問大爺住哪里?以后好報答。大爺手一擺,說希望以后我能有出息,說以后記得垡頭,有個愛管閑事的白胡子老頭就是了。
慚愧我的倔強和不務實,一直也沒出息。這些年,北漂人情冷暖自嘗。雖然一面之緣,老大爺的白胡子一直在我腦海浮現。地下室搬離一次又一次,我曾去過垡頭老地方念舊,旁邊擺頭花手套地攤的一個大媽認出我,聊天時說,也就送我羽絨服那兩年見過,大爺兒媳有時還買她的小物件。可是大爺這些年沒見出來了。我聽到后心頭一沉,不敢多問,不敢多想……
北漂,年年歲歲,朝朝暮暮。此時,又是一個冬天。我在讀李奧帕德的《沙郡年記》。這是我多次向認識的友人推薦的一本書。書里有一句話,我很喜歡:大雁隨風而去,但愿我是那風。
阿沫曾經是個空姐,因為喜歡看言情小說,后來索性就辭職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到如今也出版了七八本書了。在影視改編日漸繁榮的時候順勢轉型做起了編劇,因為這年頭靠紙質書稿費養活自己也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