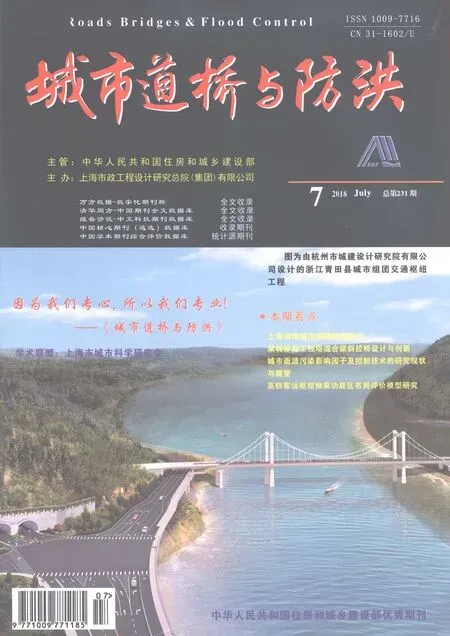城市面源污染影響因子及控制技術的研究現狀與展望
陸松柳,章 燁
(1.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市 200092;2.啟迪水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 200072)
1 研究背景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也給城市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其中水體富營養化、黑臭等城市水污染問題尤為突出,已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我國在城市點源污染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即使點源污染達到“零排放”水平,地表水水質達標率也僅42%~65%。其中,面源污染是城市水環境質量無法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即城市硬質下墊面上大量面源污染物可通過雨水和徑流進入受納水體,造成水體較高污染負荷,初期徑流的直接排入則可導致水體嚴重的突發性污染[1]。
在已實現污水二級處理的美國城市中,水體BOD年負荷源自降雨徑流的40%~80%,城市降雨徑流被美國國家環保署列為導致全美河流、湖泊污染的第三大污染源[2],并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會立法保障雨水的調蓄及利用,逐步構建污染防治與總量削減相結合的多目標控制和管理體系[3]。歐盟國家則通過雨水費政策、城市排水體制、末端處理方法和最佳管理實踐初步實現了雨水的有效管理,其中德國已成為雨水管理政策最完善、技術最先進的國家之一[4]。
我國城市雨水徑流引起的面源污染問題也十分嚴重,如滇池富營養化問題中,雨水面源污染負荷率占67%[5];據估算統計,北京、上海城區雨水徑流污染占水體總污染負荷均為10%[6]。屋面雨水徑流、街道雨水徑流、分流制出水口水質以及合流制雨天溢流為我國城市面源污染負荷的主要來源。早在1980年,北京就開展了城市面源污染調研工作,此后蘇州、上海、廣州等城市的徑流污染特征、規律及控制技術也被逐漸研究[6]。然而,我國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歷史遺留問題,使得城市面源污染的深度和廣度,以及所面臨的壓力遠超發達國家。因此,探索城市面源污染的關鍵影響因素,開展其控制技術等方面的相關研究十分必要。
2 城市面源污染特征分析
2.1 面源污染負荷性質
城市面源污染物以各種形式積蓄在街道、陰溝和其他不透水地面上,通常將其分為物理性污染物、化學性污染物和生物性污染物[7]。物理性污染物為徑流中夾帶的懸浮物,來自工地建筑垃圾、砂子塵土、汽車尾氣顆粒物、大氣干濕沉降物、輪胎和剎車摩擦產物等。化學性污染物主要有汽車尾氣中的重金屬、垃圾堆放產生的耗氧有機物、動植物有機廢棄物、有機有毒污染物等。生物性污染物主要指病源性微生物,來源于下水道溢流、寵物以及野生生物等,城市徑流中細菌含量往往超過公眾對水要求的健康標準[8]。
2.2 面源污染現狀特征
城市面源污染由降雨徑流的淋浴和沖刷作用產生,尤其在暴雨初期,地表或沉積在管網的污染物被徑流沖刷匯入水體,短時間內污染物濃度高于平時污水濃度,因此面源污染具有污染突發性、水流量大、污染成分及濃度復雜多變、污染源時空分布離散、監控困難等特征。污染負荷高、排水標準低、雨污混接嚴重、法律法規欠完善等是我國城市面源污染的主要現狀。
我國各城市道路雨水徑流和排污口雨水徑流污染情況嚴重,SS、CODCr、BOD5、TN、TP 等水質指標平均值均超地表水環境質量Ⅴ類標準[9]。城市不透水面積大,地下入滲量小,徑流量與徑流峰值明顯增加,積水導致部分城市垃圾被浸泡,溶出重金屬、N、P等的其他污染成分,進而加劇雨水污染負荷。等級越高的城市,其降雨徑流污染物負荷越高[10];南方城市路面徑流污染負荷均值高于北方城市,而北方城市屋面徑流污染更為嚴重;城區交通區降雨徑流污染高于商業區、工業區、居民區[11]。
我國的排水標準較低,如上海城區的排水系統僅達1 a一遇的設計標準,且很多系統只有泵站與總管達到1 a一遇標準,支管并未完成相應的配套改造;部分城區采用分流制系統,但也存在放江頻率與排江水量均高于合流制系統的問題[9]。由于市政排水系統缺少統一規劃建設,群眾意識缺乏,部門監督不力,導致雨污水混流現象嚴重,以上海市芙蓉江系統服務范圍為例,小區合流管、小區污水、路邊小店污水等接入市政雨水管道的混接點共482處,新建分流區內約20%混接率,部分污水未經收集與處理直排江河[12]。
3 城市面源污染的影響因子
城市雨水面源污染影響因素十分復雜,涉及自然地理、人類活動、社會經濟等諸多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影響因子。
3.1 水文氣候
降雨量、降雨強度、雨型和降水歷時是影響雨水徑流水質的重要因素。不同的雨情對地面、屋頂等的沖刷強度和時間不同,對污染物稀釋溶解作用和傳輸能力也有所不同,最終導致雨水徑流中污染物濃度存在差異[10]。車伍等[13]在對不同降雨強度條件下屋面徑流水質變化規律的研究中發現,15 min降雨量為4 mm的短時暴雨具較大沖刷力,初期徑流SS達1 985 mg/L,而1h降雨僅1.4 mm的徑流中SS僅166 mg/L。氣候因素對雨水徑流水質也有影響。李立青等[14]研究發現,武漢市十里鋪集水區2003~2005年內,2次降雨間隔時間與初期降雨徑流污染負荷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晴天天數越多,地表污染物累積越多,降雨徑流的污染程度更為嚴重[15]。
3.2 地形地貌
不同的城市地形地貌,直接影響雨水徑流的蒸發、下滲、傳輸等,也影響著城市布局、功能區組織和道路管網、水處理設施設置、景觀組織等,最終導致不同程度的城市面源污染。我國山地城鎮約占全國城鎮總數的一半,因其地表高差大,暴雨產流和排放較平原城市更為迅猛。王書敏[16]研究典型山城重慶的面源污染時空分布特征得出,山地城市暴雨徑流較平原城市,交通干道污染負荷產率較大,污染物濃度降低速率較快。
3.3 土地利用方式
城市的快速發展使得城市土地利用面積和類型增多,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影響著下墊面的類型和分布,進而影響雨水徑流量的儲蓄與削減,雨水水質的過濾與凈化。Ballo等[17]研究發現,上海中心城區內4類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徑流中,TP變化顯著且濃度各異。任玉芬等人[18]對中科院生態環境所內不同下墊面徑流進行水質檢測,發現屋面TN最高,草坪TP最高,路面COD和BOD5污染最嚴重。
3.4 地表衛生管理
道路和停車場表面有塵土、枯枝落葉、生活垃圾等,其初期徑流中還含有大量有機物、細菌、烴類、重金屬等污染因子[8]。雨水口是城市道路排水系統中重要的構筑物,也是城市面源污染物進入水環境的重要通道,其前堆積的生活垃圾、污水以及腐爛變質的沉積物,也可使城市徑流污染程度加重。因此,城市地表衛生管理水平(清掃范圍、內容、頻率、效率等)可直接影響污染物的積累狀況。
3.5 排水系統管理
城市排水系統包含排水管道、泵站和污水處理廠,是處理和排除雨污水的工程設施系統。排水系統的管理對于城市面源污染控制十分重要。由于管理者監管不嚴,杭州很多已通過驗收的新建污水管道在后期頻繁出現問題。排水是否通暢,污水是否外溢、水泵和管道等設施設備是否會受二次損傷,均與排水系統的建設規劃、運行、維修和養護等管理有關[19]。
3.6 社會經濟因素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社會經濟活動愈加頻繁,隨之自然下墊面減少,排水系統、管理水平、環境意識、法律體系等跟不上發展的需求,致使城市水環境面臨壓力。孫金華等[20]分析了1920~2000年太湖流域大量資料,發現太湖水質每經10 a下降一個級別的演變規律,其水環境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人類活動有著緊密聯系。
4 城市面源污染的控制技術
目前我國城市面源污染控制多采用“源-遷移-匯”逐級控制措施。源控制將雨水污染物盡量控制在源頭,以攔截、消納、滲透、削減方式來減輕后續徑流污染處理負荷和負荷波動,它是面源污染控制中最有效和最經濟的控制措施[21],其中下墊面改造最為常見。遷移控制是經雨水徑流污染物輸送和擴散機理的探究,采取適當措施以減少污染物排入地下水或地表水,匯控制則是通過自然生態技術或人工技術來降解徑流污染物[22]。遷移控制和匯控制的主要工程性措施包括植被淺溝、生物滯留系統、人工濕地和調蓄設施等,但此類技術往往會受城市建筑、占地條件、工程造價等因素限制,具有一定的改造難度。
4.1 下墊面改造
以改善地表透水性和增大透水面積為目的的下墊面改造是控制城市面源污染的關鍵因素之一,設置透水鋪裝、綠地建設以及屋頂綠化技術是防治面源雨水污染的重要手段。
4.1.1 透水鋪裝
利用大空隙結構層使雨水就地下滲和過濾的透水性鋪裝,可消納表面或周邊徑流,補充地下水,減輕城市雨水排瀝系統的負擔。常見的透水鋪裝有透水混凝土、透水瀝青、透水磚等,多應用于非機動車道、小區道路、園林道路等建設。透水鋪裝的徑流削減效果一般與材料結構、降雨情況、徑流水質相關[23]。此外,半透水型鋪裝的內部孔隙還可存蓄雨水供后續回收利用,有研究表明,其徑流削減能力高于無收集措施時約10%[24]。滲溝、滲坑、滲渠等的排水滲透設施是透水鋪裝的另一種形式。其中,地下排水滲溝以滲流的方式匯集水流并就近排出路基以外,可有效降低路面徑流和路基范圍內的地下水位,已廣泛應用于我國公路路基排水系統,如S309線臨夏至大河家二級公路段[25]。排水滲溝具填石和管式兩種類型,前者多為碎石和卵石,后者常選陶土、水泥混凝土、帶孔塑料等。滲透管溝占地少,雨水下滲速度快,但易堵塞滲水孔,基本無污染物去除及凈化作用,且其建設需一定挖深和土方量。
4.1.2 綠地建設
作為天然透水性材料,綠地可對雨水徑流進行滲透、凈化、儲蓄與利用,其入滲速率為1.53×10-6~4.9×10-5m/s,能有效削減 COD、NH4-N、TN、TP等[26]。合理種植植被、布設綠地高程、改善土壤性質、改造下層土壤等均有利于城市雨水利用和面源污染控制[27,28]。草地和下凹式綠地是城市綠地的代表。其中,草地產流比明顯低于相同條件的裸地,土壤含水率明顯高于裸土。下凹式綠地則為高程低于周圍路面的公共綠地建設,利用開放空間承接和貯存雨水,一般通過水文模型和概率分析方法來進行設計[29],若草坪低于周圍路面高程10~20 cm,則其入滲量可為路面的3~4倍。重現期為5 a的降雨試驗表明,下凹式綠地徑流削減率達46.58%,且對顆粒態磷具有明顯的去除效果[30]。下凹式綠地后期維護管理規范或標準,以及其長期運行對土壤理化狀況、微生物種群等影響仍有待深入研究。
4.1.3 屋頂綠化
美國是首個將屋頂綠化應用于現代建筑的國家,此后在屋頂上作防水滲透處理、上敷薄層土壤和種植綠色植物等技術被逐漸應用,可顯著控制城市面源污染,突出表現在降低屋面徑流系數、削減污染物和蓄存部分雨水等方面。屋頂綠化所用植物需具備耐熱性、抗逆性、耐旱性等基本條件,佛甲草為典型代表。劉葆華[31]對佛甲草綠化屋頂進行降雨吸收量測試中發現,當降雨量較小時,此類屋頂吸水率可達50%~100%。蓄水層介質特征,如厚度、坡度、孔隙率與保水率等也會影響雨量截流和污染物濃度削減。VanWoert[32]試驗得出,將介質層厚度增加、坡度減小,可增加雨水滯蓄量。鄭美芳等人[33]的一項研究表明,以田園土為基質層的綠色屋頂徑流中TN、TP和CODCr總負荷較普通混凝土屋頂徑流低19%~84%,但以人工基質為基質層的綠色屋頂TP負荷較對照屋頂偏高。此外,屋面植物需施用化肥和農藥,直接導致屋頂雨水徑流中TP含量較高,這也成為潛在新污染源[34]。因此,我國各地陸續頒布了《屋頂綠化技術規范》,對建筑物要求、綠化設計、綠化施工、后期養護等作了相關規定,有助于綠色屋頂技術的安全應用。
4.2 植被淺溝
植被淺溝,亦被稱為植草溝,是一類由植被覆蓋的水流輸送渠道,即景觀型地表溝渠排水系統,已廣泛運用于部分發達國家。它可持留、過濾、滲透雨水徑流,減少至少10%~20%徑流峰值,也可降低徑流中懸浮顆粒物、金屬、有機物等含量[35]。Reeves[36]研究指出,干植草溝對TSS、TN、的去除率均可達90%以上,標準傳輸植草溝和濕植草溝的處理效果不及干植草溝,且較長的植草溝有利于污染物的消除。我國在近幾年才開始應用植草溝,例如石家莊濱水生態園植草溝、西安浐河景觀節點中的植草溝設計、深圳茜坑水庫生態草溝等[37-39]。植草溝的設計直接影響其對城市面源污染控制的效果,目前國內學者對設計相關的水力計算和水質凈化功能進行了充分論述和總結,如水力停留時間、縱向坡度、最大徑流流速、有效水深等的取值,具有較強的指導性[35]。植草溝技術需進一步解決細菌輸出、占地面積較大、溝內堵塞、設計規范與評判標準缺乏等問題。
4.3 生物滯留系統
生物滯留系統一般由預處理草溝(可選)、淺層存水區、植物種植區、種植土壤層、沙濾層、砂礫墊層、排水系統和溢流裝置等組成,具有污染物沉淀、過濾、植物吸收、土壤吸附、微生物修復等作用,實現徑流雨水的蓄滲和凈化[40]。弗吉尼亞大學學者[41]監測發現,新建的生物滯留設施可消除86%TSS,90%TP,97%COD 以及 67% 油脂。Davis[42]對生物滯留池進行場地試驗,得出磷去除率可達77%~79%。國內深圳光明新區36號和38號兩條道路自建成生物滯留設施以來,傳統道路排水弊端得到改善,道路綜合徑流系數小于0.60,污染物去除率達40%~50%[43]。土壤結構、植物選型、氣候條件、服務面積等都可能影響生物滯留系統性能以及成本大小。目前,該系統仍是一個較新的領域,需收集、共享、開發基礎數據,進一步研究與實踐,如優化土壤介質以提高處理性能;完善生物滯留的數值建模以增加模型輸出值的可信性;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開展生命周期跟蹤研究等方面。
4.4 人工濕地
人工濕地由基質層、濕生植物、微生物等構成,是一種經過人為設計、構建、管理的特殊生態系統和近自然型水處理技術,多用于處理污染徑流、富營養化河湖水、生活污水等[40]。人工濕地因其具有蓄洪、削減洪峰流量和流速、減少沖蝕等作用,同時對進水流量和水質變化有較強的耐受和緩沖能力,近十幾年來,被逐漸應用于城市面源污染控制。嚴立等[44]應用三段式潛流濕地系統凈化湖濱帶初期雨水,TN、TP去除率分別達 51.2%、64.8%。尹煒等[45]考察結果顯示,塘和復合潛流人工濕地組合系統對武漢桃花島地表徑流中COD、TP、TN、SS的削減率達64.7%~90.4%。人工濕地設計需注重植物選型、布局、生長狀況等,也可與其他技術搭配使用,如入濕地前修建過濾帶以截留水中顆粒物,出濕地后增加滲透措施以強化處理出水。人工濕地技術積累,濕地系統被不斷完善與開發,相關技術規范制定與頒發,均可保障該技術的健康發展和合理應用。
4.5 調蓄設施
在雨水污染控制中,除利用天然池塘或洼地暫時調蓄雨水外,調蓄池的應用也于近幾年內備受國內學者關注。利用管道本身的空隙容量調節洪峰流量是有限的,建設人工雨水調蓄池(管)則可提高系統排水能力,削減洪峰流量,如齊齊哈爾市內30余座調蓄池明顯改善了原市內嚴重的內澇局面[46]。雨水調蓄池還可控制初期雨水和合流污水溢流對受納水體的污染,石家莊正定新區調蓄池和雨水泵站聯用有效收集了初期雨水并減少了面源污染[47],蘇州河環境整治二期中,沿河建設的合流調蓄池削減COD年入河量[48]。目前,由于調蓄池的功能、溢流方式等不同,各地容積計算方法不一,如上海雨水調蓄池旨在收集初期雨水,其容積計算參考德國,而北京的調蓄池以削減洪峰為主,通過脫過流量法和軟件模擬進行容積計算[49]。在調蓄池布設過程中,設置位置(末端和中間)、選擇類型(地下封閉、地上封閉和地上開敞)是重點,也是影響城市面源污染控制效果的關鍵因素[50]。此外,滿足截流調蓄效果且系統工程費用最小化、系統管理及運行優化等問題也正在被深入研究。
5 展望
城市雨水徑流污染具有隨機性、廣泛性、模糊性特征,其控制處理難度較大,目前已成為國際環境問題研究的熱點。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城市面源污染的基本特征、主要影響因子、控制技術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與運用。為進一步改善城市水環境質量,促使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以下幾個方面可作為城市面源污染的研究重點:
(1)我國城市類型多樣,地區自然條件、基礎設施、社會環境等各異,今后應根據不同區域特點,建立相應的城市面源污染控制理論,必要時可定位、布點進行監測研究。
(2)大氣干濕沉降是城市面源污染氮負荷的來源之一,應充分考量其對水環境的影響。
(3)加強城市面源污染對地下水污染的研究,以及對人體生命健康的影響研究。
(4)今后應更注重人工措施結合自然措施,技術工程對策與非工程對策并舉的研究。
(5)我國城市面源污染控制尚處于初始階段,因缺乏強有力的法規依托,而使得一些控制措施無法落實到位,今后應加強相關行業政策、法律法規、行業標準等內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