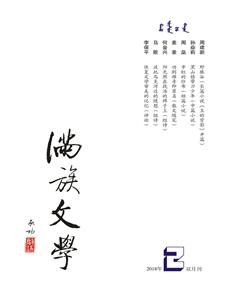碗
李金紅
小時候去小伙伴云珍家玩兒,看到她家櫥柜里擺滿琳瑯滿目的大碗、小碗和各種好看的盤子。那些碗潔白如雪,質地細膩,散發著柔和的亮光,碗的外面還有花草圖案,非常漂亮。更讓我驚奇的是,有一次云珍趁她媽不在家,偷偷端出一對锃亮的碗給我看,她說是銀碗。我看那碗上凸起的花紋雕刻的真好看,像優美卷曲的葡萄藤。她們家的碗深深地打動了我,回家告訴了母親。母親說,有錢人家用的碗大多都是這樣,用細瓷碗,也有用銅碗、銀碗。聽說用銀碗吃飯還能解毒呢!
我們家用的全是黑乎乎的粗瓷碗盤,沒有亮光,只散發著沉默的亞光,或者閃出直率的光斑,拿捏在手里沙楞楞的,且薄,端著碗,里面的熱飯就燙手。然而,我的內心仍然很安靜,從日出后端起一只粗瓷碗,到日落后放下一只粗瓷碗,我們一家人生活得很快樂。
結婚后進了婆家門,還是端著粗瓷碗吃飯。那日中午,婆婆小心翼翼雙手捧著一只敞口藍花粗瓷大碗,碗里的土豆湯冒著熱氣,放到桌子中央,我們各自舀一小碗湯就著發面玉米餅子吃,香香的真好吃。我好奇地端詳這么大且好看的碗,公公笑著告訴我,“九一八”事變后,他被日本人抓到本溪湖煤礦當勞工。一天中午,領了兩個橡子面窩窩頭,剛咬了一口,一個灰頭垢面的人走到跟前,拿著這只黑乎乎的大碗要換飯吃。公公看那人有氣無力、站立都不穩的樣子心軟了,就把窩窩頭送給他,不要他的碗。那人二話沒說,把碗生生塞到公公前懷,轉身便走。公公追上去退返,那人惱火了。公公敬佩他的骨氣,只好將這只大碗帶回家,也帶回了這段故事。
每年春節前夕,婆婆都要去離家一公里多的供銷社買幾只碗。我問婆婆,家里的碗夠用了,為什么還要買新碗?婆婆說這是鄉下人的規矩,每年添新碗筷意味著家里日子過得好,糧食一年比一年打的多,年年有余糧,天天有飯吃。多少年來,婆婆大多都買二號碗和花盤子,從不買細瓷碗。二號碗不大不小,一般人吃一碗飯就夠了,不像那些粗瓷小碗老是盛了這碗又盛那碗忙活人。買來的二號碗,藍藍的碗邊,暗白色的瓷,雖然比亮閃閃的白細瓷碗差多了,可是比粗瓷小碗光滑多了。婆婆說這樣的碗厚實,不容易碎,價錢還便宜,很適合我們家用。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們家的生活貧苦,一年到頭吃粗糧, 碗里頓頓是玉米粥,盤里餐餐是咸菜,偶爾見到一頓大粗瓷碗盛的青菜端上飯桌,大人孩子樂得夠嗆。我們習慣了這種清苦的日子,每天晚上,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坐在炕上,踏踏實實端起飯碗吃飯,有說有笑,也很快樂。偶爾公公還會糾正一下孫子們端碗的姿勢,孩子們含笑按爺爺指教去做。
后來,孩子們長大,陸續考上大學,走進大都市,踏上了工作崗位。我們家也搬進了城里。房子大了,寬敞的櫥柜里,擺滿了兒子們買回來成套的細瓷花碗,有來自瓷都的釉下彩名碗,香港細瓷釉下彩繪著清新如洗的薔薇和蘭草的大瓷湯碗,還有木碗、塑料碗、不銹鋼碗、微波爐碗,大大小小,應有盡有。每年春節,全家人一個不少圍坐下來,熱熱鬧鬧吃年飯。碗盤里的飯菜也跟著時代變化著,前些年,碗里裝的是細糧,盤子里盛的是魚肉蛋。近幾年,提倡健康飲食,碗里盛的是玉米、小米、薏米、雜糧粥;湯碗里裝的是蘿卜絲蝦仁湯、海帶豆腐湯,盤子里是青菜、大醤等。雖然每年春節,我還像往年一樣大鍋烀肉,小鍋煎炒的準備年飯,可孩子們最喜歡吃的還是那些清淡的菜,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情形不見了。飯桌上不變的是:困難時期的碗盤還會照樣登上大雅之堂。端上裝滿魚丸湯的藍花大湯碗,我們會想起公公被抓勞工, 國人受欺壓的年代;端上婆婆拖著裹腳從供銷社買回的二號碗和花盤子,就想起了生活困難時期,盼著過上富裕生活的不易;端上兩只小木碗,眼前會呈現孫女小手端不住二號碗,掉在地上摔碎嚇得哇哇大哭,而后我跑遍市場買回來木碗的場景……
如今,每當兒孫回家團聚,端起飯碗,熱熱鬧鬧吃飯時,老伴總會諄諄告誡家人:我們的日子過得好了,不需要像過去那樣用金碗、銀碗來增添光彩,而人的一生不管用什么碗,只有把飯碗端牢,路走正,才最光彩最有價值!否則,什么碗都會丟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