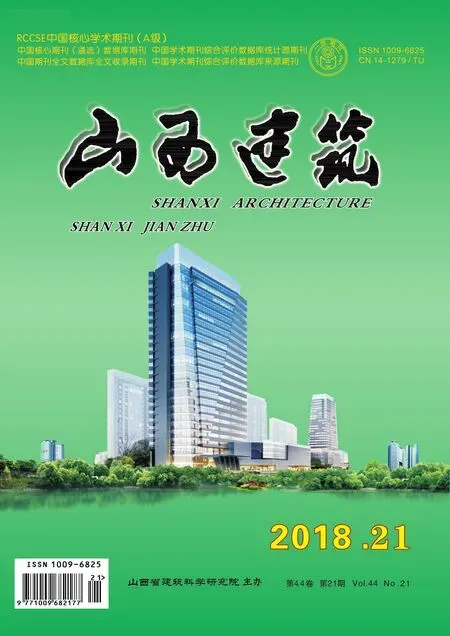車輛跟馳行為研究綜述
郭力瑋 郭彬杰 鄭海兵
(重慶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學院,重慶 400074)
0 引言
車輛跟馳行為是描述同一車道上前后兩車在行駛車隊中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微觀交通流的基礎交通行為[1]。跟馳模型是基于傳統的動力學和運動學,研究車隊中前車的運動狀態對跟馳車的運動狀態的影響,通過研究車隊中車輛逐一跟馳的特性對微觀交通流進行描述,為車輛跟馳行為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在微觀交通流仿真、交通安全評價、交通事故分析、通行能力分析以及交通系統評價等領域,車輛跟馳模型都展現出重要的應用價值[2,3]。跟馳模型從起初的模型演變成交通流中具有重要研究意義的車輛跟馳理論,經過了60多年的發展歷程,通過結合交通工程學、系統工程、物理學、心理學等眾多學科的知識,不斷對其進行改進,為交通流的研究以及交通工程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4]。
從最初車輛跟馳行為概念的提出,各國學者采用不同的理論方法對車輛跟馳行為進行研究,同時結合交通工程以及統計物理對車輛跟馳行為進行系統的建模分析,從而形成了現有較為完善的車輛跟馳理論,最后結合我國較為復雜的交通特性,將跟馳行為和交通流中的宏觀現象進行統一分析,給出未來車輛跟馳理論面臨的挑戰和發展趨勢。理論形成過程中,有大量的國內外學者投身于車輛跟馳模型的研究,尋求不同情況下的車輛跟馳行為分析的方法,對交通行業的發展以及交通領域的研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 車輛跟馳行為的發展歷程
20世紀50年代初期,車輛跟馳行為的概念被提出,Reuschel[5]對行駛車隊中的車流從運動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為跟馳行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Pipes[6]結合前一學者的思考,基于加州規則(California Vehicle Code),給出了行駛車隊中前后兩車安全跟馳距離的假設,即車輛速度每增加4.47 m/s,安全跟馳距離需增加一個車輛的長度。
20世紀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車輛跟馳模型開始運用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GM)實驗室進行研究,從而為后續各種跟馳模型的提出奠定了基礎[7,8]。后來Chandler,Herman和Gazis等學者分別從刺激—反應的模式、車隊中交通流的穩定性問題和交通流微觀模型和宏觀理論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入手,對GM模型進行了改進研究,從此GM模型在跟馳模型中顯現出較為突出的地位,同時也為微觀交通流理論的研究開辟了先河[9-11]。
20世紀60年代開始,心理學和視覺知覺理論被運用到跟馳行為的研究當中,大量的學者認識到車輛行駛時駕駛員的心理特征與感知決策對車輛跟馳行為影響的重要性,單純從車輛動力學和運動學的角度考慮不能更全面的反映車輛的跟馳行為。此后部分學者結合了統計物理學,以及通過微觀跟馳行為反映宏觀交通流的現象,接著廣義力模型、智能駕駛模型和全速度模型等多種跟馳模型被提出[1]。
21世紀以來,隨著微觀交通仿真軟件的廣泛運用以及智能交通系統的發展,大量學者開始研究基于ITS模擬論證與實際運營的理論基礎下的跟馳行為。研究過程中,不斷結合新理論和新方法,將統計物理學、心理學、計算機仿真技術等知識與交通工程學廣泛結合,發展至今已有超過70多種的車輛跟馳模型被提出,車輛跟馳理論也越來越細致化,專門化,逐漸成為微觀交通流理論中的核心理論之一[12,13]。
2 車輛跟馳行為研究分析
伴隨著非自由狀態的提出,即在一隊高密度行駛的車流中,車輛間距不大,前車車速對后車車速進行制約,車輛的跟馳行為也被廣泛研究。由于車隊具有制約性、延遲性和傳遞性3個特性,因此為了保證車隊的正常有序的運行,進行車輛跟馳行為的研究變得至關重要[14,15]。縱觀跟馳理論發展的歷程,學者們采用各自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對車輛跟馳行為進行研究分析。
2.1 不同控制方式交叉口的車輛跟馳行為研究
部分學者根據道路交叉口的類型不同,分別對信號交叉口、環形交叉口以及無信號交叉口下的車輛跟馳行為進行了研究。
在信號燈控制的交叉口中,胡家興等[16]車輛通常不只是受到前車運行狀態的影響,信號燈當前狀態將更大程度地對其車輛運行狀態進行影響,駕駛員需要判斷與前車車輛間距以及信號燈的顏色采取跟馳行為。于少偉等[17]首先分析了在現有的優化速度模型和廣義力模型的基礎上,沒有充分考慮信號交叉口處的車輛跟馳行為,于是構建了一種考慮信號燈作用下的跟馳模型。
在環形交叉口中,金勇等[18]對環形交叉口入口道車輛行為進行分析,認為車輛在進入環島時,需要對環形內部的車輛間距進行合理判斷,等待足夠的間隙出現才能插入車隊中,同時表明線性跟馳模型可用于環形交叉口入口道的車輛跟馳行為研究。
較少學者針對無信號控制交叉口的車輛跟馳行為進行研究,認為該種情況下的車輛跟馳行為可用傳統的車輛跟馳模型進行研究解決,跟馳車輛的行駛狀態總取決于前車的運行速度,忽略了相交道路的車輛對該方向的車隊造成的影響,因此無信號交叉口的車輛跟馳行為有待研究[19]。
2.2 基于車輛安全間距的跟馳行為研究
一隊行駛的車流中,前后兩車之間需要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因此在進行車輛跟馳行為的研究分析時,許多學者會將兩車之間的安全間距作為基準,建立相應的跟馳模型[20]。
王波等[21]認為,駕駛員的駕齡、性別、個體特征等是影響前后兩車的期望安全距離的主要因素,因此根據不同的影響因素對車輛的安全間距進行了仿真分析。胡紅等[22]從突發事件情況下駕駛員心理和行為特性方面考慮,給出了在最小安全跟車距離下的應急疏散跟馳模型。楊達等[23]根據車輛跟馳中的“2 s規則”對車輛間的安全距離進行說明,即在路旁選擇一個標記,前車駛過標記后2 s,后車剛好過標記,此時兩車間距為最優間距。當然,根據行駛速度的不同,也可定義成3 s或4 s規則。
2.3 非機動車跟馳行為研究
針對我國復雜的交通特性,大多數城市存在較為嚴重的機非混行現象,部分城市通過設置了非機動車道解決機非混行的問題,因此對于非機動車道上行駛的非機動車,其跟馳行為也成為重點研究對象。非機動車主要包括電動車和自行車,研究時需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但兩者的速度差異較為明顯,研究的難度也相對較大。
早期國外對于非機動車跟馳行為的研究均是建立在虛擬車道的基礎上,他們將非機動車道按照不同的寬度進行劃分,使其接近機動車道跟馳行為的特性。Sutomo和Hoque[24,25]分別以1.0 m和0.5 m的單位寬度對非機動車進行劃分,分別建立了TRASMIC模型和MIXSIM模型對非機動車跟馳行為進行了研究,其中Sutomo在此基礎上還針對機非混行做了研究。后來Hossain[26]對上述方法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的MIXNETSI模型考慮了自行車的縱向跟馳行為和橫向換道行為產生的影響。
國內的一些學者借鑒了國外的經驗,在基于建立虛擬車道的方法上做出了一些改進。由于非機動車靈活性較強,且不存在機動車的車道劃分形式,因此其車輛跟馳行為的研究較為復雜,李星星等[27]通過建立非機動車虛擬行車道,使非機動車在虛擬車道中無法實施變道行為,采用研究機動車跟馳行為的方法對其進行分析。
對于非機動車跟馳行為研究,國內外學者大多采用的是建立虛擬車道的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方式無法反映出真實的非機動車跟馳特性,并且未充分考慮非機動車的靈活性,因此非機動車的跟馳行為還有待深入研究[28]。
2.4 考慮側向車影響的車輛跟馳行為研究
通常情況下,學者們對于跟馳行為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合理的假設前提下進行的,認為跟馳車輛都是沿車道中線行駛,忽略了車道之間的相互影響。
陶鵬飛[29]認為行駛過程中相鄰車道的車輛會對車輛跟馳行為產生影響,于是分別從相鄰車道同向和反向行駛的車輛出發,建立了受側向車影響的車輛跟馳模型。曲大義等[30]發現在跟馳車隊中,車輛的行駛軌跡并不是都位于車道中心線上,這就會對相鄰車道上的車輛產生影響,于是提出了運用交叉跟馳模型解決側向干擾對跟馳車輛帶來的影響。
3 車輛跟馳行為的發展趨勢
60多年來,學者們從交叉口類型不同、有無信號燈控制路口、車輛的安全跟車間距、非機動車與機動車跟馳行為的區別以及相鄰車道的側向干擾等不同角度對車輛跟馳行為進行研究,并給出不同情況下的跟馳模型。跟馳行為的研究結合了諸多學科理論,不同的思想方法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在對具體的問題進行研究時,需要選擇適合的研究方法,不能只用自己熟知的研究方法去擬合現有問題。跟馳行為中,駕駛員的心理和生理特性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許多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通過駕駛員對車輛安全間距的界定以及感知反應的閾值建立相應的模型,但是忽略了在不同模型中如何選擇合適的駕駛人特性因素的研究。
車輛跟馳行為是一種微觀的交通行為,然而交通的實際狀況往往需要借助宏觀現象去反映,如何在現實的交通特性下實現微觀行為和宏觀現象的統一成了重點研究目標。
交通流中的宏觀現象是車輛間微觀行為的集合,微觀行為的分析研究可以對宏觀現象作出合理解釋。在實際的宏觀交通特性中,受到較多因素的影響,因此需要從中提取較為關鍵的影響因素對其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