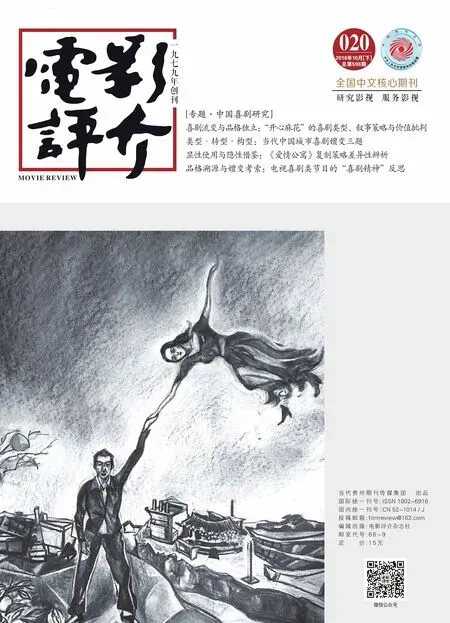類型·轉型·構型:當代中國城市喜劇嬗變三題
電影作為娛樂產品是社會政治經濟的晴雨表,反映在商業電影類型的衍化上,更能體現出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大眾心理需求和文化表征。城市喜劇是“乖僻喜劇”在當代的一種衍生類型,介乎于“愛情輕喜劇”和“家庭情節劇”之間,具備“關系”電影的基本架構,表現現代都市人群在情感關系、家庭關系及社會關系中的體驗,既能滿足大眾對于愛情、婚姻、富足生活的渴求,又對當下民眾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及大眾文化心理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和表征。梳理當下中國“城市喜劇”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它對傳統范式的繼承和發展,要從“乖僻喜劇”的類型追根溯源。

電影《我的少女時代》劇照
一、類型、文化與乖僻喜劇
“類型”(Genre)其實是指一種被反復證明的、行之有效的電影制作規范。類型電影與好萊塢商業化的制片模式、明星制度以及制片人責任制密切相關,它體現了電影藝術作為商品的特殊屬性。人們習慣按形式與風格將相似的影片歸類,“類型”的構成就是由高度典型化的明星在反復類似的場景里演出一個符合觀眾的觀賞習慣和心理預期的故事模式。
這種通俗故事的程式——“類型”傳達的不僅僅是電影的生產者,還包括電影的消費者,來自大眾的社會和文化心理感受,它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電影制作和接受的慣例系統。制作者和觀眾在“標準化”主題、人物和場景設置以及視覺風格體系中,講述和完成故事意義的生成。這一敘事系統也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會隨著社會歷史、經濟和文化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衍生、轉換和生發,通過吸納新的元素,進而生成新的范式;而造成“類型”衍生和轉換的原因,除了市場因素之外,更深層次的是社會文化內在的大眾心理動因。
“乖僻喜劇”是古典好萊塢時代最主要的類型片之一,也叫“瘋癲喜劇”或者“神經喜劇”。“神經”一詞來源于英語棒球中“曲線球”(screw ball),暗指電影主人公的離經叛道、行動不合常規,但這種特征正是對世俗權威和既定社會階層的挑戰和反叛。“乖僻喜劇”類型中,常常以一對(情侶)或者一群(家庭)成員為主角,情侶的人物設置通常為“歡喜冤家”,一位上流社會的有性格缺陷的富家千金與勞工階級出身的叛逆男主角結合,“強女主”最終與“平民男主”有個“大團圓結局”。這一類型模式在弗蘭克·卡普拉的《一夜風流》、喬治·顧柯的《費城故事》和霍華德.霍克斯的《女友禮拜五》中都有所呈現。
不同于西部片、黑幫片、偵探片這些發生在確定的、競爭性空間的類型,“乖僻喜劇”是在一個場景性不夠確定、文明的空間中實現矛盾的和解,個人和社會的沖突是內化的,藉由愛情關系象征戲劇沖突雙方的基本訴求,人際之間的對抗最終服從了社會秩序的需要,最后儀式化的“大團圓”結局包含了個體融入更主流的文明社群的價值訴求。
由于“乖僻喜劇”誕生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代,人們觀影的心理基礎是獲得精神慰藉,以此來渡過經濟低潮期。正如托馬斯·沙茲所說的,一個類型的受歡迎程度,維系在它反復處理“問題”的重要性上。類型沖突和解決包含了價值和態度的對立系統,兩者都被當代美國文化認為是很重要的。當時,“乖僻喜劇”通過“融合儀式”的方式消弭階層差異、實現社群秩序的回歸,很大程度上給予了民眾心理的支持和安慰,它的敘事策略背后包含了當時“美國夢”所推崇的以正面、樂觀、向上和家庭為核心的中產階級的主流價值觀念。
到了當代好萊塢,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乖僻喜劇”吸收了新的元素,在類型上進行了一定的衍變,發展出了“愛情輕喜劇”的模式,像《漂亮女人》《電子情書》《西雅圖夜未眠》《曼哈頓女傭》等等,這些喜劇中的男女人物設置已經轉換為現代“王子與灰姑娘”的人物模式,或者是“小妞電影”中女性主體追尋個性獨立的情感關系模式。這與整個美國社會強調平權,包括文化思潮上“女性主義”及后期的“酷兒理論”的影響都有關聯。
二、城市喜劇、轉型期的本土類型探索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城市喜劇”可以看作是“乖僻喜劇”在當下中國社會“本土化”的類型轉換范式。中國城市喜劇的發展,與中國處在轉型期的社會現狀及電影類型化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至21世紀初,不僅是世紀轉折的交替期,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型期。整個電影行業在主旋律影片、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并立的局面中,摸索著自身在政治宣傳、精英意識及娛樂文化三重功能屬性中的定位。當時占據主流的,是制片廠體系下主旋律影片所代表的“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價值觀以及改革開放浪潮下知識分子群體對于西方思潮的吸納與文化反思。一方面,電影的娛樂性和商業性不被看重;另一方面,電影的教化及文化反思功能仍然還是由主旋律和藝術電影來承載。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文化界的知識精英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嘗試用新的電影范式來表達對文化尤其是對都市人群焦慮和困惑的探討。于是,一種在政治語境和精英文化語境的夾縫中釋放現實焦慮并用調侃、戲謔的方式進行表達的喜劇片應運而生了。從“第五代”的黃建新到文學被搬上銀幕的王朔,再到后來“馮氏幽默”的馮小剛,都用喜劇這一“笑”的藝術來實現自身對社會情緒的觀照。這一時期的生活輕喜劇、黑色幽默及諷刺喜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當代中國在市場經濟、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社會形態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都市人群心理狀態的變化。當藝術電影在進行文化尋根和反思的時候,反而是喜劇類型片的創作為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印上了標記。
1988年被稱為“王朔”年,這一年王朔的四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米家山執導的《頑主》、夏鋼執導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黃建新執導的《輪回》和葉大鷹執導的《大喘氣》。王朔身為暢銷作家,精通流行文化的創作法則,他的文學改編文本天然具備了喜劇類型的結構性和情節模式,獨特的“自嘲”式的講述方式,又符合“乖僻”的特點。從王朔到后期的馮小剛,他們一脈相承的喜劇風格和價值觀,從早期的擬頑主到中期的充大腕,再到后期的偽精英,都在回應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內在焦慮。同時,調侃的“喜劇”方式又是對這種進程的解構和反諷。這就導致這一時期的喜劇對商業的態度非常矛盾,對于商業浪潮帶來的焦慮僅僅只是釋放,沒有通過價值觀的建構形成真正的紓解,而且由于商業電影的嘗試也處于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的“城市喜劇片”尚未真正成熟。
隨著WTO進程下好萊塢電影的沖擊以及中國電影放映業“院線制”改革的推行,電影作為商品的屬性被進一步確立并重視,中國電影產業化浪潮來臨了。從2002年起,中國電影開始走向全面市場化的道路。從2002—2012年的10年間,電影市場開始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電影行業的產業化升級變成了衡量電影生產力的重要指標,“商業大片”的時代由此開啟,《英雄》(2002)、《無極》(2005)、《集結號》(2007)等國產大片開始強力支撐市場。同時,適合年輕觀眾審美趣味的小成本影片也成為市場的有益補充:《瘋狂的石頭》(2006)、《瘋狂的賽車》(2009)、《人在囧途》(2010)、《失戀33天》(2011)等,這些小成本影片在制作和營銷方式上都開始注重目標受眾的定位,影片表現的主題也多為現代人的情感和心靈歸屬問題,尤其是在類型化道路上,開始有意識地嘗試類型的雜糅,喜劇、愛情、公路、犯罪元素的糅合與滲透,特別是寧浩、徐崢等“中國電影新力量”導演,他們對于類型和市場的探索,引領了接下來類型片的全產業鏈實踐,特別是為“城市喜劇片”這一類型的拓展提供了借鑒經驗。
在此之前,商業化類型的城市喜劇片主要受香港電影以及好萊塢的喜劇類型影響較多。香港電影、好萊塢美學——這兩種在文化屬性上截然不同、卻在產業運作中密切相關的異質文化的域外能量,為當時的題材分野和類型展拓貢獻著成分各異的文化基因。
香港周星馳的喜劇電影大多表現的是小人物的成長和奮斗,人物的代入感讓“草根階層”的普通人產生共鳴;基調上的喜憂參半、笑中帶淚,正暗合了喜劇中有嚴肅的人生表達和“將無價值地撕破給人看”的更高層次的美學價值;而周星馳獨有的市井智慧,成為新“城市喜劇”的基底,加上天生的喜劇節奏感,讓他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無厘頭”風格,體現“乖僻”特質的同時,又和當時整個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文化思潮不謀而合;而王晶在系列喜劇、戲仿、喜劇類型的雜糅上又為喜劇形式的極大豐富提供了范本。可以說,香港電影對于彼時以70后、80后為主的觀影群體的影響之大是不容置疑的。正是由于香港電影黃金年代盛產的喜劇、鬼怪、槍戰等類型片的滋蔭,內地觀眾才在“主旋律”、商業片、藝術片的題材分野之中重新接受了類型片的觀念,為此后內地類型片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為當今“都市喜劇片”創作在文化親緣上提供了滋養。
好萊塢類型片更多的是在形式上為“城市喜劇片”提供支撐。“乖僻喜劇”中“歡喜冤家”模式、社會階層問題及性別議題的探討、明星制與人物設置的相互作用,還是存在于經典的喜劇范式中,特別是愛情輕喜劇這一脈。不過,在好萊塢類型之外,美國獨立電影甚至包括英國電影中的黑色幽默風格,也是當代中國導演借鑒和吸收的“反類型”元素。比如,寧浩的《瘋狂的石頭》就從蓋·里奇的《兩桿大煙槍》借鑒了敘事結構和黑色幽默元素。中國“城市喜劇片”對類型的繼承和轉換,都是為了在更符合中國當下社會的民眾心理和審美需求的背景下所進行的本土化改造,也為下一個階段——“喜劇時代”類型的多樣化和大眾化改寫進行了美學和商業兩方面的積累。
三、網生代、大眾文化范式的想象建構
從2012年起,中國社會階層的結構變化導致的電影消費群體的“下沉”,使得整個電影行業的制作方式和營銷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80后、90后消費群、小鎮青年和“網生代”構成了觀影主體。而電影制作從題材、類型到視聽語言,都開始從新觀眾群體的審美習慣和娛樂消費模式入手,關注當下青年的情感體驗和生活目標,用影像進行現實投射。
一方面,以表現中產階級生存狀態和心理訴求為題材的影片構成了“城市喜劇”重要的部分。中產階級的崛起和生存空間,深刻影響了中國電影特別是“城市喜劇”的文化范式的建構。因此,緩解中產階級的焦慮、滿足中產階級對更美好生活的需求成為了創作的指向。像《泰囧》《心花怒放》這些票房驕人的“公路喜劇”片,巧妙地選擇了“在路上”和“尋找”這一公路類型樣式和喜劇模式相結合,表現的是當代人的信任危機以及對友情、對契約精神的渴求,為中產階級的精神孤獨和社會焦慮尋找到了出口。
另一支重要的“城市喜劇片”則將愛情和喜劇作為主要元素。2001年《失戀33天》票房營銷的勝利,在于它精準地鎖定了80后、90后的情感軟肋,包含了年輕一代的現代愛情觀,對于戀愛關系和兩性關系的詮釋體現了在英劇和美劇的觀影經歷中成長起來的80后更為獨立和現代的情感認知方式;《北京愛上西雅圖》盡管沿用了“乖僻喜劇”中男女主角的經典模式,但是觸及了“赴美生子”這一當今新興社會階層關注的熱門話題及由此引發的討論,在《北京愛上西雅圖2》中又通過“古典愛情”的方式喚起人們心底對傳統美好情感關系的向往;而《前任》系列,因其準確捕捉到了當下年輕人的愛情狀態而讓喜劇的方式呈現出寫實的質感,為當今年輕人在選擇焦慮和情感焦慮的迷茫中提供心靈安撫。
還有“青春”系列的“城市喜劇片”,主打懷舊牌,表現80后、90后青春將逝未逝、夢想仍在路上的追憶與追尋。

電影《一念天堂》劇照
在時間維度上,通過回憶與現實的對比交織來表現城市生活的進程及個人身在其中的成長。比如,《夏洛特煩惱》《我的少女時代》《28歲未成年》《重返20歲》中的時空穿越,《羞羞的鐵拳》中的身體互換,《港囧》中對學生時代“女神”的幻想,《超時空同居》中時空并置以及和未來的自己相遇,都是對現實生活的“替代性”想象,將“時空倒轉”的物理性假設通過類型架構的方式變成“合理性”現實,懸置人物的矛盾、危機事件,最終實現向真實生活的“回歸”。對于正在社會中奮斗打拼的主力人群來說,具有慰藉現實陣痛的作用。
從空間維度上,當前的“城市喜劇片”通過實現鮑德里亞式的“擬像”,完成了中產階級觀眾對都市空間的現代化想象。“擬像”和“仿真”不以真實為參照,而是通過視聽語言的變化,以類型化的方式把想象變成真實。比如,《整容日記》《我的美女老板》對于都市白領工作空間的設置過于美化和浪漫化,淡化了白領族群工作節奏快、職場壓力大的現實特征;《非誠勿擾2》中的亞龍灣美景,《杜拉拉升職記》《泰囧》中在東南亞取景,《小時代3》《我愿意》在歐洲取景,異國背景的架構在虛化影片現實背景的同時,營造出了中產階級觀眾的全球化想象,一定程度上也與中產階級熱衷于全球旅行的新興消費方式互為呼應,觀眾能在熒幕圖景中實現收入指標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性滿足。
可以看出,“城市喜劇片”作為表現城市生活和都市生存狀態的類型,在喚起同代際青年人的情感共鳴,特別是通過電影完成公眾想象的“替代性”滿足上,發揮了自身無可比擬的類型優勢。
而2012—2015年間,隨著“院線制”下中國電影熒幕數量的增加,三、四線城市影院的建立和觀眾群體的下移,“小鎮青年”日漸成為電影票房的主體。他們主要是生活在三、四線城市、鄉鎮以及城鄉結合部的青年人,依靠網絡而不是純影院消費來獲取觀影經驗。由于“小鎮青年”群體對于票倉的貢獻不容小覷,當今“城市喜劇片”的創作也日益體現出迎合這部分觀眾的審美趣味的趨勢,這反過來也讓“城市喜劇片”呈現出更加通俗化、草根化和“小品化”的特點。
電影《小時代》系列是“小鎮青年”成為票房主力的起點。盡管電影制作浮華,但郭敬明憑借敏銳的市場嗅覺開掘了自身品牌及文學IP的巨大商業價值,激發了他的年輕讀者對電影的期待,同時也折射出年輕一代對于都市的紙醉金迷、對消費主義盛行的生活方式充滿好奇和想象的心態。《小時代》最根本的影響在于,它讓“城市喜劇片”的發展軌跡呈現出拐點。在此之前,以“馮氏喜劇”為主體的都市喜劇占據了一、二線城市的主流市場,但是《小時代》標志著“馮氏喜劇”在三、四線城市電影市場的式微。傳統的思考性和諷喻性的文人氣質都市喜劇,無法讓“小鎮青年”笑起來,需要針對這一主體觀影人群打造新的題材風格和喜劇元素。
像“開心麻花”團隊推出的電影,憑借其自身的品牌效應和粉絲基礎,幾乎每一部電影都成為票房保證。2015年第一部電影《夏洛特煩惱》,票房超過10億,成為當年電影業的“黑馬”,之后的《驢得水》《一念天堂》《羞羞的鐵拳》直至剛上映不久的《西虹市首富》,都是票房大熱。“開心麻花”都市喜劇諳合了“小鎮青年”的審美趣味和觀影心理:依托于話劇版戲劇場的戲劇節奏、小品式的結構、充滿通俗感的笑料、小人物的夢想和尊嚴……符合依賴網絡和通俗藝術樣式生活以及喜歡短、平、快、片段式的信息觸達的“小鎮青年”的整體訴求。
當然,從市場出發迎合三、四線觀眾的審美趣味,也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文化濃重的“草根化”傾向,這也引發了人們對于粗鄙化審美,甚至“審丑”的反思,新“城市喜劇”需要進行文化深耕,因此近兩年社會觀察的深度也有所增強。比如,今年暑期檔的電影《西虹市首富》,就對當前“一夜暴富”的現象進行了批判,用巧妙的故事結構設置和漫畫式視聽語言的運用,對拜金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傾向予以諷喻和批判,但是用“喜劇”這一類型獲得了廣大觀眾的青睞,對于喚醒人們放下追名逐利的虛浮、回歸情感的本真,有著潛移默化的勸誡和引導作用,發揮了電影這一媒介基本的社會功能。
2015年是中國全面進入“互聯網+”時代的標志,電影行業卻早已呈現出符合“網生代”觀影趣味的創作熱潮。特別是近兩年,誕生了《老男孩之猛龍過江》《分手大師》《惡棍天使》《煎餅俠》等喜劇片,在文本結構、視聽語言和喜劇呈現的方式上都體現出了鮮明的互聯網傳播特點。首先,敘事上更加追求輕體量、碎片化,要尋求最直接有效觸達的傳播途徑,因此這類喜劇在題材上,很自然地放棄了宏大和厚重的敘事;其次,場景更趨于小品化、電視劇化、漫畫化,對電影視聽語言美學的要求越來越淡,大多數電影的影像質感變得簡易粗糙;再次,臺詞的喜劇效果與互聯網的關系更加密切,尤其是笑點和段子節奏更加密集,語言上也更加通俗和重口味。“互聯網的基因讓這些影片和當下的網民與用戶共享了一套通俗的價值觀和話語體系,因此在市場表現和口碑營銷方面常常出現‘事件性'的爆款。”比如,從《失戀33天》《小時代》到《煎餅俠》《超時空同居》等等。當然,當“小鎮青年”獲得更大的市場話語權之后,以網絡化特征出現的“城市喜劇”自覺地成為互聯網娛樂方式下成長的“小鎮青年”生活情緒調整和疏解的渠道,整個電影文化隨之出現“下沉”趨勢。這些基于“網生代”審美趣味的作品的確帶有“粗糙娛樂”草根化、粗俗化的特點,但隨著商業類型和市場的不斷成熟,這種審美粗鄙化的趨勢會有所改善,電影行業勢必會以價值觀和美學上更具品質的影片為主導。
從“乖僻喜劇”的分支“城市喜劇”在當下中國本土化的過程,到該類型的流變和發展,折射出中國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社會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們在價值判斷、情感歸屬、身份識別等問題上的追尋和確認及其在大眾文化心理上的表征。從“網生代”到“小鎮青年”驅動的喜劇類型范式的轉換,是文化消費對大眾心理需求的觀照和反饋。一方面,疏解了日常生活中現實壓力帶來的焦慮和困惑;另一方面,通過熒幕想象和娛樂文化的共享,完成人際交流和自我身份的想象性建構,從而獲得情感的滿足。而當下“城市喜劇”自覺的類型化追求,“架空的題材、戲劇化的風格、偶像化、游戲性、奇觀性、情感主題、草根逆襲、勵志傳奇等等,都體現了這種娛樂化的電影美學特征,也是這些作品能夠被普通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接受的時代共性”。
傳統類型中,喜劇片通過“儀式化”的融合方式彌合了階層差異,實現了秩序的回歸,而當下中國“城市喜劇”所包含的敘事策略不僅僅是基于大眾情感和心理疏解的基礎,還包含了人們對于小康社會幸福指數提高的個人訴求的表達與滿足。在這一敘事策略的過程中,從視聽語言等形式到題材等風格上的選擇和變化,深刻反映了中國當下社會消費主體的行為模式、消費習慣以及心理需求的變化。對于中國電影創作者來說,“都市喜劇”這一類型的自覺衍生和發展,也彰顯著電影人在創作上對時代特征的敏銳觸覺和對大眾文化趨勢的準確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