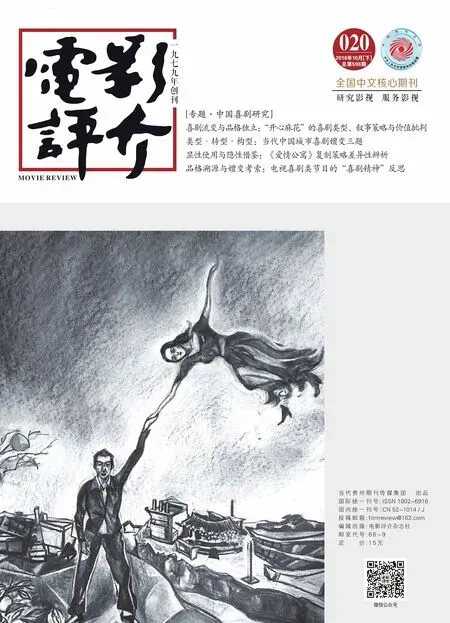顯性使用與隱性借鑒:《愛情公寓》復制策略差異性辨析
《愛情公寓》是近年來收視率頗高的一部青春情景喜劇,以其輕松幽默的風格受到了許多青年人的追捧。該劇塑造了曾小賢、胡一菲、呂子喬等鮮活的角色。劇中的情節借鑒美劇頗多,更有人說是《老友記》的中國版。其實,其中借鑒的美劇不僅《老友記》一部,還包括美劇《老爸老媽的浪漫史》《喬伊》(《joy》)等。《愛情公寓》“借鑒”以上美劇的故事情節與臺詞相當多,也確實不能諱言。雖然這種從結構、臺詞人物設置都直接借鑒自美劇,但卻屬于隱性借鑒。另一方面是該劇對20世紀90年代港臺及日本流行文化元素的使用,則屬于顯性借鑒。這些文化符號主要針對70后、80后對20世紀末域外流行文化的集體記憶。可以說,劇中文化符號的使用既是改頭換面的需要,也體現出了70后、80后文化記憶在影視領域的集體投射,而這些文化符號以日本文化所占比例居多。
但是,其對20世紀90年代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流行文化元素的復制與其借鑒美劇的故事母體在使用上的策略是迥然不同的。這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
作為該劇基礎的“起始母題”是美國文化。在《千面英雄》中,曾提到“英雄”敘事的一致性。這里的“起始母題”不僅是指具體的故事情節,還指“年輕人合租公寓”這一總的故事主題。從這一點上說,其與《老友記》是十分相似的。但要將美國故事復制成中國情景喜劇,則其過程必須經過“本土化”這一改造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其本土化工作是通過植入本土文化基因來實現的。但我們發現,這種文化基因不僅是中國內地的文化,而更多體現出的是更大范圍的東亞文化(指香港、臺灣、日本等地的文化元素)。用的是美國的故事,填充裝點的是亞洲文化的元素。前者是形式或結構,后者是外在的裝飾。從使用手法上說,前者的使用是隱性的,后者的使用則是顯性的。所謂“隱性”,即借用的外來文化信息在受眾看來其來源出處無從判斷;所謂“顯性”,即借用的外來文化信息在觀者看來其來源出處清晰可辨。二者的互動與差異,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內容。

電視劇《愛情公寓》劇照
當然,該劇也使用了許多中國內地及港臺的文化元素,表現在國產動畫片、意識形態的懷舊時代、內地影視劇、香港武俠文化、臺灣言情劇文化等。應該說,以上文化符號的使用是顯性的。然而,除了中國本土元素外,劇中呈現出的還有頗多日本、美國等文化因素。文章從其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文化特征的投射的顯性使用及對美劇進行的隱性“借鑒”來論述,而這些同時也證實其對目標觀眾群的特定設計。文中所涉及劇中的流行文化主要是日本文化、美國文化。對這些文化元素的復刻與模仿,既是該劇本土化的“剛需”,也無形中將其集體記憶投射到了當下的文化傳播中。日本與美國作為兩大流行文化的輸出國,《愛情公寓》對其使用策略并不相同。
一、《愛情公寓》對日本流行文化元素的顯性使用
本部分主要探討日本流行文化元素在該劇中的具體表現與原因:
(一)日本亞文化元素符號的使用
20世紀90年代是日本文化席卷中國大陸的時代,從動漫、影視到音樂,日本都是中國大陸重要的文化輸入國。近年來,從表面上看,日本的影響逐漸消退,主流媒介已經不太能看見日本文化如20世紀末的光景。但今天的日本動漫影視的文化傳播,已經完全不依賴電視與紙媒等傳統媒體。新生代對二次元文化的熱衷主要是通過網絡來完成的。日本文化表面上并不強勢,但潛藏在主流文化的表層之下,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該劇對日本文化的使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物設定
悲劇人物是復雜的,喜劇人物往往是類型化的、扁平化的、符號化的。意大利假面喜劇、中國的參軍戲,喜劇人物往往具有類型化的趨勢。而中國戲曲的類型化最終發展為戲曲中的“行當”。在《愛情公寓》中,也具有這樣類型化的特點,例如女漢子(胡一菲)、花花公子(呂子喬)、IT直男(陸展博)等等。這些人物人格完整、情緒飽滿,熱烈地追求幸福的生活。《愛》劇中人主要是中國人,除了關谷神奇,他的身份是漫畫家,主要工作是在房間里畫漫畫,應該屬于“宅男”類型,而他原來的職業是做壽司的。漫畫和壽司,是代表日本文化的符號。關谷神奇,正是建立在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想象基礎上臆想出來的,貼上了日本文化符號的類型化人物。
2.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在二戰后崛起,于20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大陸。一時間大街小巷、報亭書攤,鋪天蓋地,風頭無兩。20世紀90年代正是70后、80后上中小學的時候,日本漫畫對他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愛》劇的主要受眾恰是70后、80后,用漫畫元素實在“經濟實惠”“一本萬利”。就其使用的日漫類型有以下幾種:
(1)熱血格斗類
唐悠悠:“好重啊。”
關谷:“什么好重。”
唐悠悠:“圣衣好重。”(Ⅱ,1)
在20世紀末席卷大陸的日漫當推《圣斗士星矢》,該漫畫的作者是車田正美。《圣斗士星矢》無論漫畫,還是動畫,都在大陸風靡一時,成為一代人的童年記憶。圣衣是圣斗士的鎧甲,是《圣斗士》一劇的核心道具。圣衣裝在圣衣箱子里,背在圣斗士身后。身背圣衣的唐悠悠說:“圣衣好重。”這個情節應該取自《圣斗士》第一集星矢剛剛當上圣斗士、尚未能駕馭圣衣的情景。
在后面的情節中,為替胡一菲奪回曾小賢,唐悠悠與諾瀾對決,諾蘭化身《圣斗士》中的雅典娜,即暗示其(宅男)“女神”身份,也體現了諾瀾在道德上的無懈可擊。(Ⅳ,22)
(2)推理類
胡一菲:“我剛在網上買了一套《名偵探柯南》,不知哪個混蛋用筆在某個人物上畫了一個圈,然后寫上這個就是兇手。”(Ⅱ,4)
《名偵探柯南》是日本著名推理漫畫,在中國擁有大量粉絲。同樣題材的漫畫,還有《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推理是日本漫畫、小說的重要類型。喜劇中亦有一類計謀喜劇,如莫里哀《司卡班的詭計》,說的是仆人的機智勇敢。《愛》劇中還有典型的計謀成分,典型者如“秦羽墨密碼”一節,是展現胡一菲“伙同”秦羽墨擊敗幾個男生的故事。關谷扮演柯南,分析羽墨事件的推理,說出“真相只有一個,這一切都是陰謀”。當即化身一襲藍色西裝、打領結的柯南裝扮,唐悠悠說了句:“柯南君!”(Ⅱ,2)應該說,其“計謀”在整體情節設置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此時關谷扮演的“柯南君”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3)少女漫畫
關谷:“我要畫一部新漫畫,女主人公在情感上有自虐傾向,羽墨會給我靈感。”
關谷:“這種情況,簡稱,風箏斷線了。”
秦羽墨:“怪不得他一點動靜都沒有呢!太好了,我知道接下去該怎么玩了。”關谷:“少女漫畫太復雜了,我還是繼續畫貓吧。”(Ⅱ,4)
少女漫畫是日本漫畫的重要類型,其重要畫家以女性為主。代表人物有池田理代子(《凡爾賽玫瑰》《奧爾菲斯之窗》)、齊藤千惠(《白色圓舞曲》)、細川知榮子(《尼羅河女兒》)、高橋留美子(《一刻公寓》《亂馬1/2》)、成田美名子(《雙星記》《神秘王子》等)、武內直子(《美少女戰士》)等。然而,少女漫畫并非只能是女性作者,如少女漫畫一時風頭甚勁,連漫畫之神手冢治蟲也曾嘗試過。所以,關谷想要從事少女漫畫的創作也并不稀奇。雖然漫畫家不一定是女性,但受眾大多是女生。所以,可以看出《愛情公寓》使用“少女漫畫”這一元素,也是兼顧到了女性觀眾,達到了對漫畫人群的全覆蓋。
(4)日本影視
曾小賢:“就是有你們這樣的好事人群,我們作公眾人物的容易嗎?”
呂子喬:“他算公眾人物,你最多算是在話筒前接聽《午夜兇鈴》的。”
曾小賢:“呂子喬,我是一個電臺主持人。”
呂子喬:“是一個接聽午夜兇鈴的電臺主持人。”(Ⅱ,2)
日本是恐怖片大國,《午夜兇鈴》是20世紀在中國知名度頗高的日本恐怖片。《午夜兇鈴》的典故在《愛》劇經常出現。關谷給悠悠講故事“我就是來自《午夜兇鈴》的故鄉”。(Ⅲ,12)除了臺詞中的體現,而《愛情公寓》亦有恐怖片的橋段。曾小賢離公寓出走,公寓的朋友們找不到他,于是腦洞大開地推理是曾小賢碰到一個小女孩,將其帶到租住的公寓,小女孩說要喝牛奶,半夜時小女孩起床偷偷把奶粉倒掉,把骨灰裝到了奶粉盒!(Ⅰ,13)盡管觀眾有心理預期,都知道這是一次對恐怖片喜劇式的解構,但效果還是頗有些驚悚的。
關谷:“我不睡了,看會兒碟片。”張偉:“關谷,這部片子好看嗎?”
“《求婚大作戰》,日劇收視冠軍。”“你不字幕不累嗎?”“我是日本人啊。”
“你居然會追這么老的劇。”“我喜歡長澤雅美不可以嗎?”(Ⅱ,4)
20世紀90年代是日劇的黃金十年,《東京愛情故事》《東京仙履奇緣》等更成為偶像劇的代名詞。而《求婚大作戰》是稍晚的日劇,日本富士電視臺于2007年4月16日至6月25日播出的愛情電視劇。70后看這部劇的人不多,年齡應該是85后居多,可以視作黃金十年日劇風潮的延續。
在第三季中,也屢次提到“北野武”。在70后、80后的觀影認知里,北野武、巖井俊二或許比黑澤明、小津安二郎要更有名氣。劇中還有翻拍咸蛋超人“奧特曼”的戲份(《愛情公寓》外傳)。當然,其中也少不了艷星。
“子喬買了一個8 G的u盤。”
“8G能裝多少東西。”
“講道理,8 G的種子。”
“瀧澤蘿拉的種子,開花了沒?”(《愛情公寓》外傳)
瀧澤蘿拉是日本的色情明星,在這里正好表現了日本宅男文化在中國的影響。從日劇到艷星,日本影視文化在劇中比比皆是。
(5)電子游戲
在第三季中,愛情公寓里的所有人準備參演電影《決戰紫禁之巔》,出現的人物有關谷扮演的服部半藏、胡一菲扮演的東方不敗、呂子喬扮演的呂布。三個人物分別代表大陸、香港、日本的文化,這種無厘頭的混搭也體現出《愛情公寓》一劇的文化混合性。該段落特效酷炫,實為翻拍段落的華彩。在這一橋段中,服部半藏使用“無雙技”“忍者分身術”“奧義·天魔覆滅”等招式。服部半藏是日本戰國至江戶時代初期時德川氏麾下的武士一族。而中國人認識忍者服部半藏,是其作為格斗類游戲《侍魂》的重要人物。該游戲是90年代知名度頗高的格斗類游戲。90年代在街頭打電游的70后、80后們對其印象深刻。(Ⅲ,14)廣大觀眾對日本史沒有多少了解,但對游戲人物卻耳熟能詳。從任天堂的紅白機到街機,再到X box等,70后、80后們對日本游戲情感并不亞于漫畫,所以看到服部半藏倍感親切,而看到呂子喬扮演的呂布是不是也多多少少聯想到了日本的三國游戲呢?
綜上可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以日本流行文化為代表的東亞元素的使用的案例很多,不必查閱資料,大多數70后80后一看就懂、津津樂道,而這恰恰是該劇有意達到的對東亞文化的顯性使用。
(二)顯性使用日本亞文化符號的原因
推究如此廣泛使用日本文化素材的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受眾認知基礎。約定俗成的文化符號在觀眾中具有廣泛的認知,引用這樣的符號可以更節約篇幅、以少勝多,達到預期的效果。喜劇往往要建立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使用典故可以迅速有效地達到喜劇效果。
其次,喚醒集體記憶的審美共鳴。所引用的漫畫、日劇、游戲,正是70后、80后成長過程中的90年代,這些文化符號幾乎與其童年的成長經歷融為一體。引用這些東亞文化符號,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起70后、80后觀眾的審美共鳴——輕松、愉悅、童年記憶等,使作品具有更好的代入感。
再次,解構經典所帶來的“喜劇感”。康德說,喜劇感是“一種從緊張的期待突然轉化為虛無的感情”。我們崇拜偶像,但潛意識中希望看到偶像被拉下神壇。經典是高高在上的,而解構經典卻會獲得心理上的愉悅,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這大概就是人性的悖論。在《愛》劇中多次出現對經典的翻拍,與其說是致敬,不如說是解構和顛覆。翻拍經典并將其解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將緊張的期待(預期)突然轉化為虛無,由此帶來釋放緊張感的喜劇效果,從而打破生活表層幻覺來進行諷刺。這就類似于波普藝術對流行文化符號——連環畫、招貼、海報、雜志、商業設計等——的拼貼組合。波普藝術僅是將流行文化元素和符號當作素材,加工成新的藝術品,表達新的藝術觀念。波普藝術的特點是將大眾文化的一些碎片,如連環畫、快餐及印有商標的包裝進行放大復制,其所表現的特點是流行、轉瞬即逝、廉價的、批量生產的、年輕人的、詼諧風趣的、惡搞的。從文化拼貼的意義上說,《愛情公寓》正暗合了波普藝術的特點。
在《大百科全書—戲劇卷》里的“喜劇”詞條中,曾列舉過許多喜劇類型。依據其劃分,與其說《愛情公寓》是愛情喜劇,不如說屬于“歡樂喜劇”。因為劇中人盡管各有各的缺點,但總體上每個人的人格是完整的,總是充滿樂觀情緒去積極追求幸福生活,起碼是表面上的積極。而這些表層的喜劇性往往是靠這些東亞的文化符號來拼湊連接的。
二、明與暗——文化符號的顯性使用與故事母題的隱性借鑒
相較對日本(東亞)文化的大幅度使用,對美國文化符號的顯性使用卻是十分謹慎與克制的,如:
1.胡一菲問:“什么烏龜使用兩條腿走路的?”張偉:“忍者神龜!”(Ⅱ,4)
2.展博不顧婉瑜的要求執意要看《變形金剛4》(Ⅱ,22)
總之,相較東亞文化來說,對美國文化符號的使用比例少得多。另一方面,對美劇情節的借鑒是大量的,而手法則相當隱含、晦澀,一般對美劇沒有廣泛接觸的觀眾根本無從察覺,而這恰是結構性的、核心性的。當然,還有一些顯性的母題使用,如曾小賢《百萬富翁》的答題、呂子喬《盜夢空間》的橋段,普通觀眾一看便知是借用電影大片的主題。這些也可以算為顯性使用。但本文主要涉及探討的是其中借用的美劇核心情節,如《老友記》《尋媽記》(HIMYM)《喬伊》(joey)等,則是結構性十分隱晦的。以下略舉幾例:
《愛情公寓》第一季13集“記憶碎片”段落,借鑒自《尋媽記》(HIMYM)第一季第9集;第一季第13集 “尋找曾小賢”段落,借鑒自《尋媽記》(HIMYM)第二季第1集、《尋媽記》(HIMYM)第二季第2集;第一季14集“蟑螂鼠”段落,借鑒自《尋媽記》第一季第7集;第一季第10集“趙無量”段落,借鑒自《喬伊》(joey)第一季第3集等。
在以上段落,從故事到臺詞,真是“相似度極高”的生吞活剝。但此種借鑒的手法則比較隱性,普通觀眾基本無從辨別其出處。可以看出,《愛》劇對于流行文化(符號與母題)的使用與母題借鑒是兩種策略。一種是明,即顯性的方式;一種是暗,即隱性的方式。
明的方式,即顯性借鑒,如以上對東亞文化的借鑒。在使用上,力圖使觀眾有效接受、簡單明了、直截了當。對于70后、80后觀眾來說是親切的,具有很強的代入感。同時,顯性使用是碎片化的、不成系統的。即拿掉一兩個,對故事主題結構無根本性損害。暗的方式,即對美劇情節的隱性借鑒。而這是結構性的、核心性的,這與美劇的相似性很高,如果更改其中的細節往往該單元的故事就不成立了。可以說,表層的喜劇性是靠這些東亞的文化符號來連接的,由情節的突轉和發現帶來的內在喜劇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所借鑒的美劇提供的。
三、抄襲還是揚棄——戲劇史上的改編
《愛情公寓》的確難避抄襲之嫌,屢屢被人貼上美劇“盜版”的標簽。但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原有故事進行加工改造,在中外文學藝術史上并不少見。而針對某一母體,不斷地進行新的創作,更是編劇改編歷史上的常事。
古羅馬戲劇家普勞圖斯曾寫過喜劇《孿生兄弟》,描寫一對孿生兄弟所發生的種種誤會。莎士比亞將其改寫成《錯中錯》;普勞圖斯還寫過《一罐金子》,寫守財奴的吝嗇;莫里哀在其基礎上寫成《慳吝人》。同為羅馬時代的劇作家泰倫斯作有喜劇《佛爾繆》,莫里哀在其基礎上寫成《司卡班的詭計》),莫里哀又把泰倫斯的另一部作品《兩兄弟》改寫成《丈夫學堂》。故事還是原來的故事,但時代的風尚改變了。“啟蒙時期的嚴肅喜劇與傷感喜劇是以泰倫斯的作品為楷模的。”
古希臘曾有悲劇《美狄亞》《俄狄浦斯》《安提戈涅》《厄拉克忒拉》《阿伽門農》《俄瑞斯忒亞》等經典作品。古羅馬的塞內加重新寫過《美狄亞》《俄狄浦斯王》《費德爾》(即《厄拉克忒拉》),到了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重新寫了《俄狄浦斯王》。
18世紀,西班牙作家阿爾菲愛里重寫了《安提戈涅》《阿伽門農》《俄瑞斯忒》《克麗奧佩特拉》(莎士比亞的劇作)。而1942年法國劇作家讓·阿努伊又寫了新一版的《安提戈涅》。
浮士德的故事是西歐中世紀傳說。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的馬婁創作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劇史》。歌德在19世紀利用這一故事,創作了巨作《浮士德》。同一母題往往會凸顯出不同的時代精神。古希臘要通過英雄的毀滅達到靈魂的凈化,文藝復興是要彰顯人文精神,啟蒙運動要宣傳自由平等,20世紀的作家要追問存在的意義。
東方的中國戲曲中也存在這樣一再改寫的“母題”。而元明戲曲中有一類神仙度化劇,其中就經常出現這一類道教母題。道家思想的開創者莊周,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形象。以莊周為主人公的戲曲《蝴蝶夢》為元明之間無名氏作。故事根據《莊子》中“莊周夢蝴蝶”“莊周鼓盆而歌”等典故演化而成:莊子欲試探妻子田氏,詐死。田氏為救新夫,持斧頭要劈開莊子的棺材,取其腦髓。棺木破裂,莊周坐起,田氏慚愧自盡。
戲曲《蝴蝶夢》的后世演變,亦名為《大劈棺》。川劇有《南華堂》,河北梆子有《莊子扇墳》。根據《大劈棺》,拍攝有電影《莊周試妻》。中央實驗話劇院還排有同名話劇《莊周試妻》。如果說《蝴蝶夢》是看破紅塵,灰心入道;后世的《大劈棺》《莊周試妻》則是探討兩性關系。故事還是原來的故事,探討的主題已經不一樣了。
正如坎貝爾所說:“無論英雄是可笑的還是崇高的,是希臘人還是野蠻人,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他們的旅行計劃在本質上極少有差異。”神話的相似性自有其心理上的深層基礎,而戲劇影視的“母題”也是如此。
以上種種,可見圍繞同一主題進行再創作,在戲劇史上由來已久。老故事穿上新衣,但從中反映出不同時代或地域的新精神、新面貌。毋庸諱言,《愛情公寓》對美劇的隱性使用的確存在照搬;但從另一方面,寬容地說,也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借鑒”和“改編”。這也促使我們思考當今影視劇改編的邊界問題。
從美國到中國的“改編”,需要有一個“語境轉譯”的過程。搬演老故事只是“語境轉譯”的第一步,其后還要加入新的元素。語境轉譯需要更多本土化的文化符號的植入,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流行文化恰恰實現了這一功能。以上對日本動漫、影視、游戲的文化符號的使用就是具體的體現,而這些符號的使用必然是顯性的。這樣,日美文化在結構上互為“表里”,在手法上互為“顯隱”,從而造成這一劇在劇情結構上的吸引力,且細節十分貼近中國青年觀眾。
對于日本和美國文化,該劇選擇一明一暗、一顯一隱兩種借鑒方式,是頗值得玩味的。《愛》涉嫌抄襲美劇,但其中顯性引用的美國文化痕跡卻很少。為了使該劇改頭換面,加入新的文化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對東亞文化則用的毫無顧忌、理直氣壯,但對東亞文化的借鑒只是符號性的、點綴性的。可以說,越是不相干,借鑒得越是理直氣壯、明目張膽;越是血脈相連,越需改頭換面、遮遮掩掩。東亞的文化符號與美劇的情節,二者共同構成了《愛情公寓》一劇的拼湊性與雜糅性——表和里。從表面上說,當今的日本文化并不算強勢,日劇動漫也難再掀萬人空巷的風潮。但日本文化在該劇的使用上卻是顯性的,而美國文化是當下的強勢文化,但在該劇中的使用卻是隱性的。如此“弱者明顯,強者隱晦”,著實有些吊詭。這在創作者或許是不自覺的,但卻是勢必如此的。
結語
約定俗成的文化符號的引用體現了集體文化及背后的80后的懷舊情懷。當下,日本文化雖在表面上看不到,但作為亞文化潛存于主流文化之下,勢力依然巨大,其對年輕人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對70后、80后來說,是青少年的回憶;對90后、00后來說,是強勁的二次元。《愛情公寓》對日本文化符號的顯性使用是有效的,而美國文化在華的勢頭更勝日本一籌,但《愛情公寓》的符號引用則很少,更多的是故事素材和臺詞等核心劇情的借用,其手法則是非常隱晦的。我們可以說,這種隱性借鑒就是抄襲,但泛觀戲劇史卻不乏先例。對于喜劇影視來說,翻拍是票房保證的有效手段。近年來,翻拍美國喜劇的例子在中國屢見不鮮,如影片《我最好朋友的婚禮》翻拍自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同名喜劇電影。由Angelababy、倪妮等主演的喜劇電影《新娘大作戰》翻拍自美國20世紀福克斯同名浪漫喜劇電影。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完成的就是本土化問題,而本土化就要植入本國文化符號來完成。
本文無意為《愛情公寓》辯護,其與若干美劇相似度頗高,不容諱言;亦無意貶損,畢竟舊瓶新酒也是文藝創作的老路。本文只是通過分析該劇對日美文化使用的這兩種手法,以探討喜劇創作的若干方式,并探討其與域外文化的互動關系。最終實現的是,在流行文化符號的拼貼下的母題本土化改編。前者是顯而易見,而后者則是不易察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