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方戒(六題)
吳魯言
1、紅燒青鲇魚
這次,老華在自家小區的商鋪中盤了個門面,開了家快餐店。
之前,他和妻子開過水果鋪、水產行、洗車店,都不太成功。
快餐店營業三個月了,生意依然不紅不火。老華想,圖個離家近,小生意過得去就行。
初秋的一個傍晚,一位保姆推著一輛輪椅來了,輪椅上的老人不會說話,只會指指點點。老人點了一份排骨蘿卜湯,一份炒面,還有一份紅燒青鲇魚。在點最后一個菜時,老人笑了,笑時他的嘴是歪的,露出了下唇中隱藏的一粒小小黑痣,似乎是一顆掛嘴上的小芝麻,顯得有些俏皮。
老華猛地叫了起來:“你是歪痣,歪痣哥?”
老人驚訝地抬頭,看著他,手舞足蹈起來,眼神里帶著強烈的疑問。
老華說:“歪痣哥,我是華斌啊,華勇的弟弟,還記得不?當年你和我哥是同桌,我天天跟在你倆后面的!”
老人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努力想站起來,可站不起來,又執意地伸出右手,那手布滿了凹凸不平的青筋,像一根失去水分的老藤,在半空中作搖搖欲墜狀,老華急忙從柜臺后走了出來,緊緊握住老人的手,告訴他華勇已在五年前去世了,臨走時還曾提到過他。
老人心里清楚,華勇是他小學里最要好的同學,可他參軍回來后就去外地創業了,一走四十年,如今落葉歸根,可身體完全垮了,但這些話他說不出來。聽到小時候的伙伴一直記得他,念叨著他,心里酸酸的,眼圈泛紅了,老華看出了點什么,把老人推到餐桌邊,示意他先吃飯,可老人卻要保姆先付錢。保姆問:“多少錢?”
老華推推手說:“哪能要哥的錢?不要,不要。”這時老人坐不穩了,又開始在輪椅上動起來,急了。保姆代替表達:“錢一定要收的,否則他不吃了。”然后,老華看了一眼菜,說:“23元,收20元吧。”但保姆一定要給老華23元,保姆說老人很固執的,她不敢隨意更改他的主意。但老華說:“我與他的關系非同一般,他是我哥的發小啊。3元零錢怎么能收呢,這從小的情還不頂3元錢?下次,只要歪痣哥來我這里吃飯,零頭都抹去。”
說完,老華對著老人爽朗地笑,老人再一次雞啄米般的不住點頭,也笑了。保姆驚奇地看著老人,付了20元錢。因為老人很久沒笑了。
之后,老人又來過一次,依然點了23元的菜,其中一盆還是紅燒青鲇魚,老華還是說:“3元零錢抹去。”
可后來,老華再也沒見歪痣哥來。
不久后,小區邊上開設了一個老年活動中心,每天早上九點需要送兩份切好的水果,生意落在了老華的快餐店。這是老華從來沒想到過的。
又過了兩個月,鎮養老院院長來了,說有人出資,隔天要給每位老年人加一個蔬菜和一份魚湯,而且要保證是當地農民自己種植或養殖的。老華兒子在村里經營著一個魚塘,魚塘周圍種了各類時令蔬菜。這不,老華的快餐店和兒子的魚塘,就這樣多了一份穩定的生意。養老院就在鎮政府邊上,也即山腳下,臨湖靠山,環境優美,是養老養生天堂。經過擴建的養老院比原先還要大三倍,聽說床位增加到了八百張,可依然供不應求。
不知過了多久。
那天,歪痣哥的保姆來了,只買一份紅燒青鲇魚。
老華問:“為什么不見我歪痣哥?”
保姆:“他徹底中風了,只能躺在床上。”
老華急了:“啊,那歪痣哥還住在老家嗎?
保姆:“住養老院。”
“怎么住養老院?不是說他很有錢嗎?”
“是的,很有錢。他的兒子孫子都在美國,有很大的事業,也很有錢,可有錢沒人花,他就把錢都捐給了村上和鎮上。這小區邊上的老年活動中心的設備都是他捐的,鎮上養老院擴建工程也是他捐的。”
“啊?那他們從我這里取水果,買菜肴也是?”老華的嘴張得如鱷魚般,停在半空中。
“你抹去了他三元錢零頭,老人很感動,只有你還記著與他小時候的情誼。只有你不看重錢,那天晚上回去,老人流淚了。”保姆平靜地說完一切,急著離去,老人等著紅燒青鲇魚呢。
老華突然想起,哥哥在世時也很喜歡吃紅燒青鲇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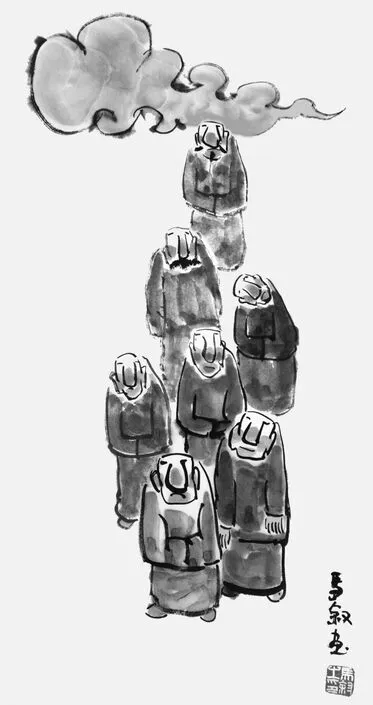
2、再見,孩子
這是個擁有一千多戶家庭的安置小區,清晨,人們買早點,買菜,送孩子上學、上班,都一陣風似的從小區的各個角落里交替穿梭出來,場面熱氣騰騰,堪比高速發展的大城市。
小區內,第6幢六層樓左邊那一間——6601室,總是靜悄悄的,甚至靜得有些窒息。
房屋的主人姓肖,名山,是位七十出頭的老人,腿略有小疾,行動不便,血糖血壓都偏高,他的房門總是緊緊關閉著。縱使有社區志愿者或親戚來探望,門也總是被輕輕地打開,又被輕輕地關上。老人很少出來,對面的鄰居幾乎不認識他。
其實,小區里少數鄰里見過他,只知老人不善言辭,出來時拄一根拐杖,總是慢慢地移動,眼睛穩穩地平視前方,即使有相識的鄰居經過,也很少與人打招呼。
很多愛在小區門衛閑聊的老人說起6601室,都說那是個怪老頭!很怪的老頭!從來沒聽他發出過一點聲音。
是啊,一個獨居多年、閉門不出的老人,有什么聲音可發呢。
其實,老人在家,很多時候也是靜靜地坐著。坐等日出、坐等日落。無論外面是明媚的陽光,還是瀟瀟風雨,似乎都與他無關。
早晨,老人坐在陽臺上,手捧一個小鏡框,鏡框里是個漂亮的小女孩,那是他的孫女,在北京,小學四年級學生。孫女有三年沒有來了,那張照片是三年前那次送給他的,現在,只有逢年過節會來一個電話。或許,老人每天的靜坐都為等待某一個節日的到來。
中午,社區老年服務中心會為老人送來一素一湯一飯,這是他自己點的。其實,老年服務中心的菜系還是比較豐盛的,可老人就是喜歡吃素,偶爾加一個魚或肉。晚飯亦如此。只有早餐是自己做的白粥,就著冰箱里存放的醬菜、榨菜、果醬等應付一餐。偶爾下樓,老人一般也就在小區的便利店買些日用品,更多時候由社區志愿者幫忙采購。
很多時候老人常看著墻上掛著的那張照片發呆。照片里的女人五十出頭,一席漆黑的頭發,精神飽滿,風韻猶存,微微笑著,似乎正欲啟朱唇與他對話。那是他的老伴,12年前在北京帶孫女,某天清晨從市場買菜回來,拐角處被一輛飛馳的電瓶車撞出很遠很遠。
當肖山趕到北京時,看到的是妻子僵硬的身體,沒有一絲血色的臉,神情卻略有微笑,就像那張照片上的模樣,似乎對著他說:你來了,來接我啦。當年的肖山才六十歲,完全不像老人,頂多算個壯年。怎么會想到,妻子來北京半年,再見時卻已成永別。肖山一下子從壯年過渡到了老年,神情一度恍惚。
從北京回來,除了帶回妻子的骨灰盒,還有一個枕頭。至今,這個枕頭沒有被清洗過,并排放在臥室的大床上,每晚臨睡,他都會聞一聞枕頭上妻子留下的味道。總是在那份熟悉的味道中迷迷糊糊地睡去。
早上,都會被對面6602室的聲音吵醒,雖然老人不熟識對面鄰居,卻知道他們是一個五口之家,小夫妻恩愛,老夫妻和諧,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剛剛上一年級,伶牙俐齒,走樓梯總是一蹦三跳,她的每一次上學和放學之際,整個樓道的空氣都在舞動,都變得鮮活起來。老人很享受這樣的被吵醒,似乎沒有這個吵鬧聲他是不愿意真正地醒來的。
六點三刻,又一個清早,外面熱氣騰騰,靜靜的樓道響起了小女孩準點上學的聲音:再見,媽媽,再見,爸爸。再見,爺爺,再見,奶奶。
這時,6601室里的老人肖山,每每總會自言自語地跟上一句:再見,孩子。
3、螞蟻
2008年的那個夏天,史姑娘的命運被徹底改變。
一個農村姑娘,大專畢業,找不到工作,在鎮上就近的個體幼兒園里當輔導員,拿著一千元的月薪,如數上交,卻依然要聽母親不停的嘮叨聲。
母親嘮叨女兒的不努力,也嘮叨丈夫的無能,更嘮叨夫家的赤貧。祖上四代為農,如何改變命運?爺爺奶奶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已近七旬,父親和母親雖然有了農保,有了比城里人更大更舒適的樓房,但畢竟只是周邊私營企業的打工者。那個年代,人人向往公務員。獨木橋上有很多小小的螞蟻在擠著,大家都想順利過道,可最終很多螞蟻還是掉進了獨木橋下的河流中,被淘汰。還有很多小螞蟻連爬上橋的資格都沒有。當然,也有極少數本沒資格爬橋的螞蟻根本不需要努力靠近橋身,直接過了河。那遇上的不是權貴之族,便是金錢的掌柜。
姑娘的叔叔在百公里外的城市打拼,成為了當地有名的建筑商之一。鄉間很多農民工都去當了建筑工人,因為,市里有好幾個像叔叔一樣的知名建筑商。父親也想去,母親不同意。理由:憑什么給你弟打工?他有錢了應該關照我們。
叔叔回來時,西裝革履,紅光滿面。母親嘴里還是不停地嘮叨著,有點指桑罵槐。可小叔子還是上前一步恭敬地叫了聲:嫂子,并遞上了一堆禮物。
母親并沒有因為叔叔的好客而停止嘮叨。當然,叔叔是自己人,怎會不了解自家嫂子呢。一個大男人何必與小女子計較?
重要的是,叔叔帶回了一張表格,讓她填好,還要侄女帶上行李隨他去市里。
不久后,也就是那個夏天,姑娘 “考入”了公務員,母親的眉間終于有了笑意,爺爺奶奶和父親的耳朵清凈了許多。
經過20年的努力,史姑娘已不再是當年的那個姑娘,被人尊稱為史處長。
村莊里的人早已記不起史處長當年在農村時的情景。如今的史處長,走路昂首挺胸,每一次出現都是嶄新的衣裳,臉上還戴著一副透明的眼鏡,村中有人問她母親:你家閨女讀書時沒近視,怎么現在才四十幾歲就老花眼了?母親回頭狠狠地啐了村民一口。
對于沒見過世面的村民,有什么好解釋的?史處長從來不屑于和村民搭話,當然,村民主動叫她時,她會微微地點一下頭,就像她正在視察村莊,面上似笑非笑,村民們基本上是看不懂的。
史處長和母親正走向一家水果店,店鋪上“兄弟水果行”幾個金燦燦的大字。
這家水果行還真是史處長的兄弟開的,堂兄弟,她唯一的比她小整整十五歲的堂兄弟。
原來十年前,也就在史處長剛當上副處長時,叔叔被抓。聽說是行賄罪,行的是市里最大官的賄——市委書記。書記何許人也?本鎮人,與叔叔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學呢。當年,鎮上很多人至市里搞建筑行業,都是因為有了市委書記的關照。
當然,市委書記也被雙規了。
叔叔出事時,史副處長的小膽吊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叔叔進去后,倒是干凈利落,沒有涉及九族之類的蝦兵蟹將。
嬸子帶著剛大專畢業的兒子回到了農村。市委書記的兒子比堂弟還小,當年也因父親的權勢,不求上進,只混了個職高畢業。于是,嬸子拿出手上僅有的一些小錢,租了店面由堂弟和原市委書記的兒子在鎮上開了 “兄弟水果行”。
聽說,母親經常去關照 “兄弟水果行”的生意,這倒讓史處長心有安慰。這不,她今天回老家也要去看望高齡的爺爺奶奶,就買些水果吧。
母親跟在姑娘的后面,一進門就開始挑,這個捏幾下,那個搖幾下,堂弟遠遠地站在柜臺后,似乎沒看到這個當大官的堂姐。母親開始叫:阿玖,這柿子多少錢一斤?被叫作阿玖的堂弟只是咧嘴笑了一下,不搭話。邊上有個年紀相似的小老板回話了:“四元五角一斤。”母親又說:“便宜點,我家的生意全給你們做了,三元怎么樣?”小老板說:“大媽,不行啊,這個柿子進來都要四元的。”母親皺了皺眉,表示不信:“你這小老板,年紀輕輕的,我不與你爭論,我是來關照阿玖生意的,不是阿拉阿玖與你一起開這個水果行,我才不來你的店里買什么水果呢。”
誰知,小老板一下子扔掉了本打算裝水果的塑料袋,瞪著眼睛喊:“你說的什么屁話啊?阿玖每次賣給你比批發價都便宜,那是他關照你!不是你關照他!懂不懂?”
史處長站在邊上始終沒說話,見此情景,立即拉了母親走出兄弟水果行。
4、感冒
快到中秋了,老邵的心開始熱起來,像小伙子一樣有些激動,為啥呢?
原來他要在中秋之日去省城會妻子,當然還要看看孫子,看看兒子和兒媳婦。
兒媳婦是去年元旦進的家門,婚禮過后的二月份老伴退休了。老伴比他小五歲,50周歲準時從鎮上的郵政局退休。用現在的標準,50歲的女人仍像花一朵,還未進入老年行列。老邵是鎮里一名科級干部,已進入二線崗位,工作輕松。本想,夫妻倆可經常外出周游列國了。誰知,不久省城傳來喜訊,兒媳婦懷上了。小夫妻倆都不會做飯,天天吃美團外賣。老伴怕兒媳婦吃太多地溝油傷害胎兒,急急地進城當煮飯婆去了,這不,一對三十年的老夫妻被活生生地分離了。
如今,孫子快周歲了,老伴還沒回來過一次,只有老邵進省城去看他們的份。每次去前都從鎮上買好最新鮮的魚肉和土特產,就像古時進貢似的。這次,老邵打算帶上戰友老林送的兩盒流沙月餅,聽說是他女兒親手做的,還在網上開了店,生意火爆。老林見女兒忙很想去幫忙,卻遭婉拒,說小兩口自己能行,老爸如果想送人盡管開口提要求。于是,老林向女兒要了十盒月餅,分送五位老戰友。老林送來的時候一個勁地囑咐:“老邵,這手工月餅可是咱閨女親手制作的,材料講究,工序復雜,質量保證,千萬別送人,知道嗎?”老邵被老林的話感動了,緊緊回握他的手,承諾著:“自己吃,一定自己吃!全家人在中秋那天吃!”老林這才舒展開他那彎彎的八字眉,笑了。
之前,老邵每月進省城一次,都開車去的。可半年前,老邵得了一次重感冒后,身體狀況直線下降,省城來回開得五百公里,累得過了好幾天才緩過來。這不,已有四個月沒去了。
想到此,老邵給老伴撥電話。在第一個嘟聲還未響完之前電話就被接起:“喂,什么時候來啊?”神了,難道老伴是千里眼。老邵在這邊嘿嘿地笑著,回答:“明天下午提前點下班就來。”“你請個假吧,中飯前趕到這兒。”老伴的聲音像小姑娘一樣輕快,聲調也是活潑的。在老邵的眼里,老伴永遠是那個最美麗的姑娘,還如他當年追求時那樣有情趣,老伴是盼著他在小兩口回家前抵達呢。
次日中餐時,老邵準時到兒子家,卻敲不開門,以為老伴與他躲迷藏呢,可怎么也沒聽到孫子的聲音,按理說這小屁孩不會如此安靜。等了半天沒回應,只能掏出鑰匙。里面靜悄悄的,沒人。老邵剛放下大包小包,聽到外面有人進來了。一看是老伴抱著孫子,后面還跟著兒子和兒媳婦。剛要張口,他們仨一致向他作了一個“噓”的噤聲動作。原來,這幾天孫子感冒了,昨晚吵鬧了一夜。看著一臉疲憊的老伴,老邵有點心疼,想去抱孫子,老伴已把孩子抱進房間了,小床一直放奶奶那間。
老伴進去了,兒媳婦撣了幾下新衣服,往自己房里去,兒子上來輕聲地喊了一聲:“爸”。老邵斜眼瞅他一眼,正想罵時,里屋的孫子哭了起來。
老邵急著跑了進去,問:“怎么了,怎么哭了?”老伴把孫子重新從小床上抱起來,說:“孩子這次感冒鼻涕特別多,一躺下,估計里面的鼻涕又使他呼吸不暢,難受了就醒了,昨晚老這樣,我都不敢睡,一直在幫他擦鼻涕。”這時,老邵才看到孫子的兩個小鼻孔四周都發紅了。兒媳婦聞聲進來了:“媽,你不要用濕巾擦了,你看那兩個小鼻子都成什么了?”兒子也跟進來了,反問:“那用干的東西擦濕鼻涕就不會紅了?”說著,兒子從母親那兒抱過孩子:“媽,您休息一會兒,孩子我來抱著,仰著頭應該不難受,不哭不哭。”可孫子在親爹懷里還是哭,看來這個年輕的爹不太像爹,老伴還是抱了回去。老邵看到這兒,當機立斷說:“這孩子的鼻涕吸出來就行了。” “吸,怎么吸?”兒媳婦第一個問。“用你的嘴,去吸孩子的鼻孔啊!”兒媳婦裝出一副厭惡的狀態,擰著鼻子轉過了頭,似乎孩子不是她親生的,兒子也聽得木木的,只有老伴用期待的目光看著他,老邵輕輕地抱過孫子的小臉,柔柔地把孫子的小鼻涕給吸了出來。
那一晚,老邵什么也沒干,就在那兒替孫子吸鼻涕。聽說孫子一晚沒哭,還被爺爺逗得咯咯笑。
可老邵回來后又感冒了。
5、一枚方戒
這里是1009室,里面空蕩蕩的,沒有任何裝修,沒有任何家具,當然也沒有任何被居住過的跡象,但實實在在的卻有人居住在這里。
請看,墻上那幅掛得有點歪的、雜志般大小的帶框遺照,照片里的人便是唯一的房主,他已經在這里 “住”了三年。
房主姓孫,名立強。老人臨走前,除了這套房子,還有一枚方戒。
所有的故事已成為過去,但還是值得說道說道。
孫立強老人出生在1931年,中國大地抗日戰爭正如荼如火地進行,日本鬼子所到之處硝煙彌漫,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老孫家前兩個生的是女兒,對于這個兒子的出生特別高興,父母都把他疼在心尖兒上。可那年代實在太苦了,能有一口吃已經不錯,等到中國人民終于把鬼子趕了出去時,家里又增加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而母親卻在生下雙胞胎弟妹后難產而去了,全家生活一下子陷入無邊的苦海。
解放后,孫立強參加了人民解放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退伍回來時,一個腿瘸了,身上還有沒取出的彈片。在農村,一個失去力量的腿比失去一個眼睛更重要。與他一起參軍退伍的鄰村老王一個眼睛沒了,仍娶到了一個標致的媳婦,而孫立強卻遲遲未娶,有人說,是他們家實在太窮了,有人說因為他沒有母親的疼愛,一個沒有女人的家庭娶兒媳婦當然難。還有,他的大姐夫是反革命,被鎮壓了,這在當地可是轟轟烈烈的臭名遠揚啊。或許,命中注定孫立強一輩子打光棍。
他的弟弟也是在三十歲才娶上媳婦,娶的是鄰村一位老姑娘,一位左鄰右舍都懼怕的老姑娘,當然,弟弟娶了這個老姑娘也變成了怕老婆的男人。
弟媳婦生了三個女兒,說是為了照顧單身的哥哥,把最小的女兒過繼給他。說是過繼,其實兩家的房子緊挨著,小侄女并沒住到孫立強家,倒是孫立強的東西從此都理所當然地屬于了小侄女。小侄女從出生時吃用都由孫立強負責,當然孫立強很樂意,他從內心深處視小侄女為己出。幼時,每天抱著她玩;入學后,每天來回接送;考上大學了,費用自然仍由他供;侄女大學畢業找了個好單位,孫立強比誰都高興,逢人夸孩子聰明能干。可侄女除了偶爾給他買過幾個單位食堂自己做的包子或小蛋糕,什么也沒孝敬過他,但孫立強吃著侄女拿來的包子還是滿心的歡喜。侄女結婚時,他把一輩子的積蓄全給買了嫁妝。當侄女生孩子時,孫立強已經六十多歲了,由于身上原先的彈片未取出的,舊疾復發,健康每況愈下。但孫立強還是努力幫侄女帶外孫,直到孩子隨父母進了城上幼兒園。
恰時,農村的土地被征遷了,政府給了二萬多元的賠償費,孫立強想與別的老人一樣用這筆錢為自己買一個農村醫保,可侄女來電了,要買學區房,于是,孫立強有點為難,但還是全額拿出。他想著以后還是要依靠侄女養老送終的,于是,自己每月除了民政局的極小部分殘疾軍人補助費,失去了其它生活來源。侄女每次來基本兩手空空,而孫立強以前總是盡自己所能給她帶去些土特產,給孩子一些零花錢,可現在外孫來時,他再也拿不出零花錢了。
侄女也很久沒來了。
年三十,侄女給他送來了六根年糕,一袋糖,兩個面包。二十多年來孫立強一直在弟弟家過年,今年,他們沒叫,但他想,自己人何必見外,而且他已把前幾天民政局和鎮上慰問的棉被、米、油都給了弟媳婦,于是就過去了。飯桌上,沒有人與他搭話,他說的幾句話也沒人接,弟弟面露怯色,弟媳婦只顧管孫輩們吃飯,侄女夫婦對他愛理不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完這餐年夜飯的,這是他這輩子吃的最尷尬的一餐飯,如同乞丐。見她們收拾碗筷之際,孫立強偷偷地把預先準備的紅包給了外孫,出來時,臉上掛了淚珠。
每年春節初三,輪到侄女家請客,包括娘家和夫家的親戚。以前孫立強負責燒水、擇菜、搬遞東西等雜活,等眾親吃完,他隨便點吃剩菜,完了繼續整理杯盤狼藉。多年以來,侄女從沒正兒八經地請這個伯伯或者說養父上正桌。可這次,孫立強舊病復發,連基本的勞動能力也難以支撐,所以,只能坐在家里等著侄女來叫他,哪怕仍是讓他吃些殘羹冷炙。但已過午時,沒有一個人來叫他,連小孫子的電話都沒有。那一天,孫立強也沒做飯,一直坐到天黑。
年后,孫立強的身體好了些。聽說老王兒子開的那所駕駛學校門衛嫌工資低不干了,他就上門請求老王,他不要工資,他只是想離開家,求個住地。
從此,孫立強吃住都在簡陋的門衛屋,老家出租給了外來打工者,而老王的兒子也給他每月1200元的工資,但他舍不得用,他在門衛邊上開墾了一塊菜地,一年四季只吃蔬菜,偶爾買點豬油見點葷氣。周邊鄰里知道他的苦,有好心人想來照顧他,都被一一拒絕。
半年后,孫立強用積下來的錢在金店里打了一枚大大的方戒,每天戴在右手中指上。
侄女來了,沒有請他回去的意思,只訴說著自己養育孩子的不易,家庭開支巨大,孫立強沒回應她,只說,自己每天省吃儉用是想買一個壽穴,以便老了回到父母身邊。
不久,孫立強傳出話,如果哪天誰幫他收尸,那枚方戒就歸誰,侄女除外。
此話,使侄女及弟弟家的任何人都視他為敵人,徹底翻臉了,似乎孫立強這一輩子真的做了對不起弟弟家的大事。
時光又推進了三年,全村被整體拆遷了。
孫立強也想住新房,可他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已從門衛轉到了醫院。
臨終前,他寫下遺囑,拆遷所分得房產捐給村里,做集體資產處置。唯一條件,讓他的遺像在新房里掛三年,他是多么想住一下寬暢亮堂的好房子啊,多么想享受一下人世間的天倫之樂啊。
6、贈衣
兒子的畢業典禮結束,一大批學生和教師從里面蜂擁而出,她混在眾多家長中翹首張望著。
終于,兒子小學畢業了,六年的接送可告一段落。
這時,她看到兒時的伙伴史海燕,從校門走了出來,于是,有意識地在一位高個子的男家長后躲閃了一下。
“袁芳!你來接兒子啊?”史海燕直呼其名。這令她受寵若驚,又有點難為情,臉頰似乎被烙了一下,微燙,虧得天色已晚,應該看不出來吧。
她將自己從人群中剝離出來,上前輕輕地喚了聲:“史局長,你也來參加畢業典禮?”
旁邊幾位家長聽到有人稱 “史局長”,目光轉向了她們。
“什么史局長,我的名字你不知道啊?”史海燕沒有一點兒官架子,拉起袁芳的手,示意到一邊。
“這星期回老家不?幫我帶個東西給老媽,最近局里事情特別多。”史海燕向來是直來直去的主兒。逢年過節在村里碰上了,她也只是向史局長點個頭或微笑一下,盡量避開正面接觸。最近一次,在全村拆遷搬到新的安置小區時遇見了,也是史海燕大聲叫她的,其實,史海燕一直很熱情的,但她有自知之明,一介平民,何必太接近一位教育局副局長呢。小時候歸小時候,畢竟,現在都長大了嘛。
“什么東西?到時我去你那兒取吧。”袁芳不得不接受這份信任和委托。
“老媽年紀大了,有些便秘,我托人從外面帶來一些土蜂蜜,聽說效果特好。”史海燕如是說。
“上年紀的人,大多這樣。”袁芳勸慰道,“這周兒子畢業了,是要帶他去外婆家走一走的。”
“那我明天早上把東西放局門衛,你有空時取一下。”史海燕知道她就在離市教育局不遠處的市建交局工作,只是她不是正式編制用工。當然,史海燕心里也知道,袁芳避她,是因工作上的差距。當年,袁芳的成績并不比她差。袁芳考的是初中中專,成績好的學生才能考上中專,成績稍差的就只能上普高,而史海燕就是后者。但史海燕在普高畢業后,考入了大專,直接被分配到區委辦公室工作。袁芳中專畢業后分配在一家國有建筑公司上班。前幾年,國有企業轉制了,再聰明的袁芳也逃不脫被改制的命運,幸好她的業務水平一流,手上有各類建筑方面的資質證書。市建交局下面某部門重新聘用了她,于是,袁芳成為了國家機關里的工作人員,但這個工作人員的身份和性質,與史局長的公務員身份完全兩回事。說句難聽的話,袁芳業務做得再強,為單位賺的錢再多,頂多年底被評個優秀,拿幾百元獎勵,一切行政職務永遠與她無關。
“對了,你兒子畢業了,那些校服如果還沒送出去的話,留給我兒子吧?”史海燕問。
袁芳回過神來,笑答:“沒問題。只是局長的兒子還穿舊衣服?”
“怎么不能啊,他才讀三年級呢,到高年級段不是還要買春夏秋冬四套校服啊,那四套加起來可不便宜哦。”
“那好,我去找出來,洗干凈了。”袁芳應承道。
“謝謝啦,那我先走了。明天別忘了哦。”史海燕邊說邊離去。她的背影依然如姑娘時一樣輕快,活潑,只是韻味更佳。
第二天,袁芳在教育局門衛拿到了史局長的土蜂蜜。
幾天后,又及時地把土蜂蜜交給了娘家同社區的史媽媽。
可一個月后,當她再次看到洗得干干凈凈、疊得整整齊齊的小學生校服時,不知道怎么辦才好。
畢竟那只是幾套舊衣服,說不定史局長只是隨口說說呢。難道,真要拿到市教育局門衛去“顯眼”?還是送到她家里去?放教育局門衛肯定不太妥當,去她家里更不妥了,兒子的成績已經出來了,正在重點中學的前后搖擺,讀哪個學校還沒定呢。去了,史海燕肯定要問她兒子讀哪個學校的事兒。當然,她也想兒子讀好點的學校,哪怕出個十萬二十萬的資助費。雖然,夫妻倆都只是工薪階層,但為了兒子的將來,這點錢,平時省吃儉用還是備下的。此時此刻,說心里不想求著一個當官的,那是假的,她多么希望自己就是教育局局長,哪怕教育局一個科員也好,那些重點學校的校長們也會高抬貴手的啊。
舊衣送,還是不送?
這些天袁芳根本沒法認真工作,沒法認真吃飯,腦子里凈想的是如何去送這四套舊校服。
晚飯時,丈夫看她心緒不寧,勸道:“想開點,孩子讀哪個學校都沒關系。”
她搖搖頭,又點點頭。
兒子看到媽媽仍在糾結中,懂事地說:“媽媽,你放心,無論上哪個學校,我都會認真學習的。”
袁芳看了看父子倆,隔了一會兒說:“今天,樓下小斌媽媽問我要你的舊校服呢,可我答應了史海燕,就是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為了省幾塊錢。我又怎樣能把舊校服送給她呢?”
“啊?”丈夫抬頭,停止了吃飯。
兒子卻說:“小事一樁,史局長兒子每天晚上在我們學校操場上運動,我飯后就把校服給他送去。”
校服送出去幾天后,兒子錄取通知書也來了,普通中學。
但這次,袁芳的心情很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