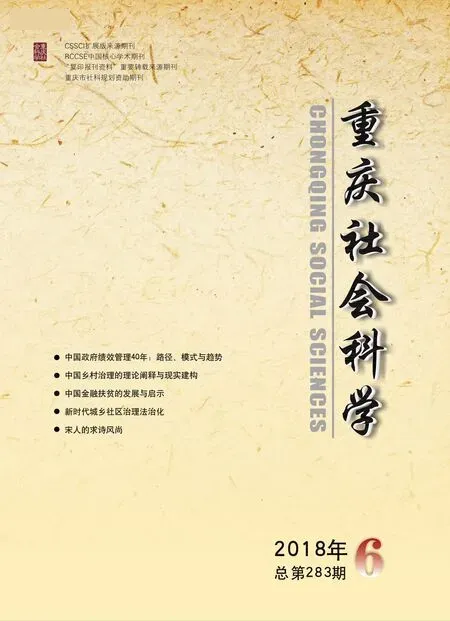馬克思的幸福觀及其勞動價值論解讀
徐小芳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上海 200241)
馬克思青年時代就確立了追求人類幸福的職業目標,并且終其一生踐行了這個偉大理想。馬克思指出,人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在于人能夠按照美的樣子組織世界,能夠把自己的生命活動當成自己意志的對象,并且在這個對象化過程中實現人的本質。因此他并未像之前的哲學家或經濟學家那樣將幸福泛化,而是指出幸福只有在改變現實中人的異化、實現人的本質對象化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但是人通過勞動實現人的本質的這個對象化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被異化了。
馬克思指出人的異化包括個人與其自身的異化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但是個人與其自身的異化需要在人與人的社會聯系中實現和表達,“人的異化,一般地說人同自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同其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但是馬克思之前的古典哲學家或如黑格爾將人的本質等同于人的精神,或如費爾巴哈割裂了人與人的社會聯系的歷史性,因此他們所能提出的人追求幸福的方式也割裂了理想與現實。比如青年黑格爾學派認為只要從思維中清除資本主義制度這個令人不幸的范疇,就會消滅資本本身。又比如費爾巴哈認為“生命本身就是幸福”,只要“對己克制,對人以愛”也就能夠幸福了。
馬克思在確立了他歷史唯物主義中對人的本質的科學理解之后,便致力于闡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如何將人與人的聯系異化為物與物的關系的。因為人與人的聯系始于交換勞動產品,因此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商品開始分析。初始的商品只是人的勞動對象化的產物,商品的交換也反映了人的社會價值。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交換價值固定在貨幣上之后,人也就迷失在異化的世界之中了。馬克思批判國民經濟學家看不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了異化勞動,因此即便亞當·斯密抽象出了一般人類勞動,也無非是異化勞動的規律而已,這也是他們將不勞動、安逸視為幸福的原因。因此馬克思指出,只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變異化世界對人的異化,才能真正實現人的幸福。
一、馬克思幸福觀的來源及基本內涵
馬克思年輕時候就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表達了為人類的幸福而奮斗的人生追求和社會理想,而這也成為他一生理論研究和革命斗爭的內在主線。
(一)馬克思幸福觀的來源
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既是馬克思哲學理論的主要來源,也是他幸福觀的重要來源。眾所周知,黑格爾試圖構建連接市民社會與政治生活的一元體系,他的思路是用“人”這個主體將二者聯系在一起。但是在黑格爾看來,人等同于人的本質、人的思維。或者說黑格爾把“邏輯的、思辨的”精神等同于人的本質,這樣宗教、國家、權力等就成了反映人的精神本質的東西,也就是與“人的本質相異化的本質”[1]162。正因為黑格爾對人的本質的錯誤理解,他將這種理念的、精神的東西上升到了最高的地位,并變成了獨立的主體,卻把真正的現實活動者以及現實關系變成了這種思維理念的想象活動[2]250-251。所以黑格爾把人的本質等同于人的思維,忽略了現實的存在物才是“真正主體”[2]273,他這種一元的嘗試就變成了真正的二元,結果便陷入了自相矛盾當中。這樣一來,一方面他將國家、社會權力等看作人所能夠形成的最至高無上的東西,而且如果國家現實的制度與這種人的意識相違背的話,就說明發生了異化,就說明“這個國家就不是真正的國家”[2]268。而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從現實的人出發去研究“國家”等社會存在,所以在考察個體對國家的責任時,他找到了現實社會中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普遍的唯一的價值,即“金錢的財富”,這樣個體只需向國家繳納“金錢”就履行了自己的義務[2]318。所以馬克思戲謔黑格爾說“愛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出錢就行!”[2]319
所以,在黑格爾這里人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現的,人的本質的一切異化不過是自我意識的異化。雖然他的思想摧毀了上帝的權威,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追求幸福的可能性,但是卻將這種邏輯可能性歸結在抽象的理性之中。在黑格爾這種絕對精神的指導下,后來的青年黑格爾學派甚至認為只要從思維中去除資本主義這個概念范疇,就能夠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在現實中給人帶來的不幸了。這無疑是可笑的。所以馬克思在《神圣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指出,要想站起來,單純靠思想上站起來,卻不考慮套在思想頭上的現實枷鎖,是不行的。
另一位對馬克思哲學觀影響最大的哲學家是費爾巴哈。費爾巴哈證明了黑格爾的哲學無非是由人的思想思考之后形成的“宗教”,本質上是對人的異化的另外一種“形式和存在方式”。費爾巴哈認為世界是人與人的世界,并且他將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1]158變成了他的理論基礎。但是盡管費爾巴哈相較于其他唯物主義者的優越性在于承認人是“感性的對象”[3]50,但是在他這里,人的感性活動依然只是停留在“抽象的人”的理論層面,這就導致他認為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僅限于“感情范圍內”。換言之,費爾巴哈的錯誤在于他沒能批判現實的生活關系,“人”在費爾巴哈這里只是感性的對象,而他沒有看到人本身也是感性的活動。這樣一來,除了理想化的愛與友情之外,費爾巴哈便看不到人與人之間還有什么其他屬于“人的關系”[3]50。所以盡管費爾巴哈在客觀世界中是唯物主義,但是在歷史觀中他又會陷入唯心[3]6。
費爾巴哈雖然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當成他的理論基礎,但是他認為人的異化在于宗教的異化,因而只要將宗教世俗化,由人代替神,“對己克制,對人以愛”,就可以解放人類。但是費爾巴哈對人的定義依然是抽象的,不是現實的、實踐的人,因此他不能意識到世俗世界已經是異化了的類存在,在這個異化的世界中人也是被異化了、與人的本質相“分離”的了。
黑格爾與費爾巴哈都是通過“人”來構建他們的理論。他們對“人”以及“人的本質”的不同定義導致他們對幸福的不同理解,而且也導致他們提出了不同實現幸福的手段和方式。馬克思也是從“人”與“人的本質”出發構建他的理論體系,但是他認為黑格爾將“人的本質”等同于精神,未能考察現實的實際經驗,又認為費爾巴哈等唯物主義者未能將事物、現實、感性等活動當成實踐的、“感性的人的活動”、割裂了人的主觀與現實之間的聯系[3]6,所以馬克思對人的定義是現實實在的實踐中的“人”,并且據此提出最終目標是實現“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1]120。因此,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不同于舊唯物主義在于“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3]6,而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3]30。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于人是人本身,因此人既是個體又是總體,作為個體只是現實類存在的一個存在物,作為總體是被思考感知到的社會主體的“自為存在”[1]125。
(二)馬克思勞動幸福觀的基本內涵
馬克思在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對于“人的本質”的看法。馬克思指出人是人本身,人的本質其實是一切社會聯系的總和。這樣,馬克思所講的人就不再單純停留在概念層面,而是現實實踐的人了。馬克思又指出,人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在于人能夠按照美的樣子組織世界,能夠把自己的生命活動當成自己意志的對象,并且在這個對象化過程中實現人的本質。人通過勞動完成對象化的過程,或者說勞動只是人實現人的本質并確證自身的途徑。
馬克思認為勞動對象化的這個過程本身是自由、自然、沒有占有的,是人的本質的一個外化體現,因此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過程本來是幸福的。但是如果人在自己的對象里面迷失自身的時候人就會發生異化[1]98。換句話說,如果對象對人而言不是人的對象或者人對對象而言不是占主體地位的對象的人的時候,人就會發生異化。所以馬克思總結人的異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作為個體的人同人的本質相異化,另一方面是由于類存在本身發生了異化,使得每個人都同其他人的關系發生了異化[1]125。但是馬克思認為人會將自身當成是普遍的有生命的“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1]95,人同自身的關系也只有同他人之間的關系對象化為現實的關系才能得以“實現和表現”[4]22。所以馬克思認為人的任何自我異化只是體現在人同他人發生的關系上[1]99,這樣他對于人的異化的分析就著重于類存在的異化上了[1]98。
馬克思指出勞動“是人在外化范圍內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是人改造對象世界并將人的類生活對象化從而實現自我確證的途徑,不僅包括精神勞動也包括體力勞動。但是勞動不一定是自由自覺的,也不一定是積極的[1]63。在異化的類存在中,人的勞動是異化的勞動。異化的勞動把人的本質變成維持生存的手段,這不僅剝奪了人的生產對象和真正的人的生活,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異化且對立。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從世俗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中去理解,然后通過排除這些矛盾的方式“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人是人本身,“人的本質”是社會化的,是自然化的,是在歷史中發展的,而人的對象在歷史發展中表現為人所創造的生產力、社會狀況和意識,以及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文化、宗教、國家等。“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人的本質的實現過程本來只是對象化的過程,但是倘若類存在發生了異化,這種對象化過程也就被異化了,人也就變成“自身異化的存在物”,人的幸福也就無從談起了。所以人的幸福或者人的本質的回歸意味著對人的異化的積極的揚棄,使人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質,“人的一切異化、一切壓迫性的生存狀況和境遇的消解”[5]。而要想實現人的幸福,就必須改變異化的類存在,用物質的力量改變物質的世界。
二、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了異化勞動與人的不幸
馬克思肯定了黑格爾對勞動本質的發現,認為他正確地指出了現實的真正的“對象性的人”其實也只是每個人勞動的結果。換言之,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也是需要人通過勞動在現實生活中自我確證并將人的類生活對象化。但是他批評黑格爾把勞動看成人的本質,并將所有的勞動都視為是有用的積極的勞動。黑格爾的錯誤是因為他在現實社會基礎層面“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1]63。
國民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成天然的生產方式,看不到歷史的發展并不只有私有制這一種形式,也看不到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勞動的外化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1]63。他們甚至把這種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當作“本質的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因此馬克思指出國民經濟學本質是異化勞動的經濟規律。異化勞動一方面導致“物的異化”,這樣工人創造的勞動產品就成了“統治著他的對象關系”,勞動過程對于工人而言成了“不屬于他的活動”[1]100。另一方面,隨著異化勞動的發展,整個外在世界都變成了異化的世界。這時就會發生“人的異化”。物的異化中人類社會還可以是人與人的關系,比如古時候通過等級制度維持社會關系,而當發生“人的異化”的時候,人與人的關系卻消失在物與物的關系之中。
因為在異化的世界中人生產的目的只是“占有”,而不是實現“人的本質”[1]34,作為社會聯系的主體——人就成了“自身異化的存在物”。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剩余價值的增殖,而不是人的發展,這樣整個現實世界都被異化成了資本控制人的異化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勞動不管是體力還是智力,都變成了“不依賴于他、不屬于他、轉過來反對他自身的活動”,即發生了“自我異化”[1]25,工人本身變成了他所創造的對象的奴隸[1]95。
國民經濟學家不僅不能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歷史中存在的一種形式,還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成“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4]99。這就導致他們看不到“人的異化”的歷史過程,并把“個人的需要和利己主義”當成天經地義的了[1]30。正因為如此,國民經濟學家即便認為找到了生產的靈魂——勞動,也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現實中工人的勞動與工人的勞動對象以及精神相分離[1]57,而工人也只是創造財富的工具和“勞動的動物”[1]36。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使得工人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工人只能得到他作為“資本家的自由奴隸”而不是作為“人”的勞動產品。這樣工人的勞動看似由工資等價支付,但是實際上工人被支付的工資只是工人的勞動力價值,而這種異化語言卻被認為是“人類尊嚴的東西”[3]38。
三、馬克思通過勞動價值論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
馬克思指出由于分工與私有制導致了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不均,使得人想去占有外物,并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國家等社會活動。隨著這些社會活動的固定化,人類創造的對象越來越成為控制人類的外在力量,人本身的產物卻變成了統治控制人、與人愿望背道而馳的“物質力量”[6]121。資本主義世界是異化的世界,人是異化的非人,勞動是異化的勞動。因為生產是反映人的本質的鏡子,因此要想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這種異化的局面,就必須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商品”是馬克思歷史地辯證地分析之后提取的市民社會的細胞。
人的勞動作用于某個對象進而產生產品,但是為了獲得別人的產品,或者是為了交換使用價值,慢慢地發展出了交換價值。在交換過程中,某些商品逐漸成為一般等價物,并從商品中分離出來,進而具備社會公認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就如同一面能反映商品價值的鏡子,其本身并不需要有價值。但是現實中交換價值這面鏡子需要真正的“價值”作為承載體,也就是作為交換價值的物體本身原來得是商品并有價值。所以人們誤以為貨幣只是一種符號的觀點會掩蓋價值的“中介”——交換價值的來源及歷史。實際上貨幣的本質首先是商品,是人類社會勞動的化身。所以如果不考慮社會生產,單純通過貨幣來看價格,就可能使得價格與商品的價值不符合,因為價格可以完全與價值無關,“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1]25,比如良心、信任等都可以有價格,只要能被所有者出賣并換取金錢就有了商品的形式和價格了。
商品自己不能到市場上交換,要通過人來交換,人們只是作為商品的所有者來交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通過物與物來表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6]103。在歷史發展的初期,物與物的關系還沒有完全取代人與人的關系,原因是資本還沒有取代一切。或者說,人類社會還是按照人的樣子來組織社會。在這個時期人們交換商品主要還是交換使用價值,資本也多表現為“住房、手工勞動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襲的主顧”等自然形式的資本,這種資本是與所有者及其上面固定的勞動密不可分的等級資本[3]59。后來隨著商人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不同地域之間的聯系被打破,社會生產發展,貨幣成為唯一的交換價值。因此貨幣越來越成為了社會財富的象征,擁有更多貨幣也便擁有了更多的社會權力,所以就會出現貯藏貨幣的行為,這也是最初信貸萌芽的原因。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貨幣逐漸控制了所有的生產部門,并變成“契約上的一般商品”[6]161了。而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控制了所有部門,貨幣取得衡量社會價值的唯一交換價值的地位的時候,貨幣就會表現出異化的物對人的全面統治,“人”也就完全迷失在用“金錢”來衡量一切社會價值的異化的類存在中了。在這種社會中,生產的目的是“利潤”,這并非是資本家的本性不好或者是某個人的人性有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就是這樣進行的。此時工人的勞動被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所掩蓋了,而社會需要也被經濟學中的“需要”,即愿意而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掩蓋了,“人”的地位和價值已經不重要了。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達,資本取得的社會權力越大、越多樣化,人就會變得更加利己、缺乏社會性,也就“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質相異化”[1]29。
通過交換價值的歷史起源可以知道“價值”這個概念首先是“人”的,是由“人”創造和衡量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魯濱遜一個人在荒島上的行為實際上體現了所有的價值就說明了這個問題。但是隨著人占有人創造的生產對象,人的勞動發生了異化。歷史發展初期只是物的異化,因為有些人并不被認為是人,資本也是固定的自然形式的等級資本。后來隨著貨幣資本逐漸控制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目的就是交換價值的增值,就發生了人的異化,所以這個時候價值就完全被物來衡量了。而之所以會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種概念,是因為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價值”是馬克思歷史地辯證地分析之后找到的生產方式的共性,具有一般性。而第三卷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基于特定生產方式的社會需要與社會分工之上的,因此第三卷中的市場價值是在特定生產方式中某個部門內部競爭之后形成的,而不像薩繆爾森或者龐巴維克等認為的馬克思在第三卷中完全放棄了價值這個概念。因此在資本主義市場上,資本控制了一切,資本逐利的本性使得一切使用價值的存在都是為了利潤,商品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獲得“利潤”,兌換用貨幣衡量的“價格”。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為了利潤進行生產的商品可能既違背了商品的市場價值,又形成了虛假的社會價值和社會需要。比如近年來流行的“網紅”,不過是資本投資包裝,卻引得少男少女們趨之若鶩。
鮑德里亞認為馬克思沒有反思使用價值 “意味著他并未超越他所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7],這其實是不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人的異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價值本身就是由物來衡量,因此也就不能通過批判使用價值而改變價值。“產品作為使用價值,它的尺度是對這種特殊產品的需要量,產品作為價值,它的尺度是流通中存在的物化勞動量。這樣一來,認為價值本身同使用價值無關,或者另一方面認為物化勞動本身是價值的實體和尺度,這兩種說法都同樣是錯誤的了”[8]39。
馬克思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什么是“人的幸福”,但是他從青年時期就開始思考人的幸福,并在青年時期就曾對選擇職業的考慮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認為只有為了人類的完美和幸福的工作才是偉大而幸福[9]。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幸福不應該只屬于某個階級或等級[10]304,所有人都有同樣的人的特性和對幸福追求的渴望。但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所有東西都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人們活著的目的也是賺錢發財,除此之外便不知道還有什么幸福[10]564,所以人類和人類命運一開始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礎上”[10]432。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馬克思才會反思人的本質以及人的異化的問題。馬克思指出人本是通過勞動確證自己,通過勞動對象化過程實現個體的價值,這個過程本是真、善、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不觸碰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空談泛泛的幸福或者臆造某種可以使所有階級都能夠“協調和幸福的制度”[11]是荒謬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使生產工人成了一種不幸[6]487。但是馬克思之前的哲學家未能從現實世界批判,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又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成天然存在的生產方式來對待,甚至又為了能夠解釋這種異化了的生產方式中的經濟現象設置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樣一個前提[1]25,結果使每個人的勞動都成為只為一己私利而不關心社會福利[10]606的勞動。正是懷著這種對人的幸福的渴望,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最重要的并不是高喊“幸福”的口號,而是要認識到幸福不是靠虛假的妥協和合作就能實現的[12],必須建筑于一個“靠和平交換和共同協作”并且能夠“安排勞動、交往和消費”的偉大民族之上[13]。因此只有使“交換、生產及其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到人的支配[3]40,才能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以及人自身的異化,才能真正實現人的幸福。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楊楹.馬克思哲學的最高價值訴求:“人民的現實幸福”[J].哲學研究,2012(2):9-1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M].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A)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89.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6.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