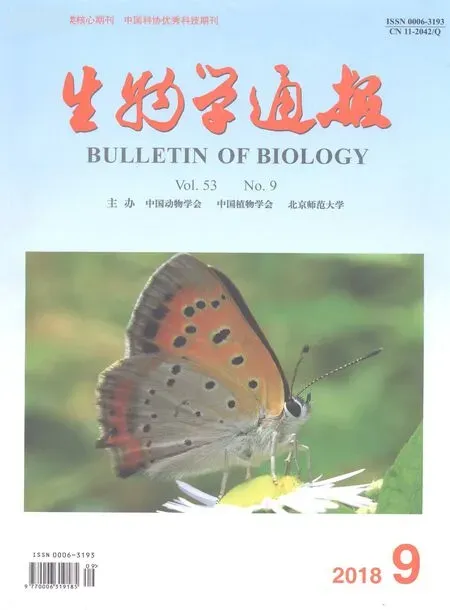基礎教育中的工程學:與科學探究同樣重要的問題解決途徑
王海蘭 劉恩山
(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北京 100875)
21世紀,科學、工程和技術幾乎滲透了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們也是人類面對現在生活和未來挑戰的關鍵。隨著知識的迅速發展,科學教育已不可能要求學生掌握某一學科的全部內容,而應注重在有限的基礎教育的時間內為學生提供充分的學習體驗,培養學生獲取、理解和運用知識的能力。2013年,美國頒布了《下一代科學教育標準》,其中將科學探究和工程實踐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2017年,我國頒布了《義務教育小學科學課程標準》[1],其中明確提出了“技術與工程領域”的學習要求。在我國2018年初頒布的《普通高中生物學課程標準(2017年版)》中,尤其是選修模塊“生物技術與工程”,十分強調將科學、技術、工程學、數學融入相關的課程內容當中[2]。隨著工程學逐漸進入科學教育之中,對基礎教育中工程學的內涵、特點、課程開展方式的理解就變得尤為重要。
1 工程學定義
“科學”一詞起源于拉丁語scientia,意思是知識;而“工程”一詞起源于中世紀拉丁語ingeniare,意思是設計和發明。對于工程學的定義,不同的研究者和研究機構有著不同的理解。1998年,美國國家工程院主席伍爾夫(Wulf)提出,工程學是指“在限制條件下進行設計”。這里的限制條件既包括科學規律,也包括技術、經濟、政治、社會及倫理等。2009年,美國K-12工程學教育委員會在《K-12教育中的工程學?》中指出,工程學是“設計人造世界的過程”。2010年,美國國家工程院在《K-12工程學教育標準》中指出,工程學是“為滿足人們的需求而進行的系統設計”。2013年,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在《下一代科學教育標準》中指出,工程學是“參與系統的設計,從而解決特定的人類問題”。
綜上所述,工程學是指工程師以滿足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各類需求為導向進行設計的過程。劉恩山教授認為,工程學的宗旨與自然科學不同,科學的目的是揭示自然的規律,而工程學在于引發變革,因此力圖改進是工程設計的核心[3]。
2 工程設計的定義、過程與特點
正如在《國家科學教育標準》中的定義,科學探究指的是科學家用以研究自然界并基于此種研究獲得的證據提出種種解釋的多種不同途徑。相似地,工程設計指的是工程師用以解決工程難題的方法,并基于此創造能滿足人類需求的設備或過程[4]。
對于工程設計的過程,不同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的定義。帕爾(Pahl,1996)等將工程設計的過程分為4個主要的步驟,分別是:①明確任務并規劃產品;②概念設計;③具化設計;④細化設計。其中,因需求而觸發工程設計,明確基本問題、建立功能標準和改進解決方法是完成設計的基本思路。弗倫希(French,1998)在4個步驟的基礎上,將工程設計的過程具體分為8個步驟,分別是:①明確需求;②分析問題;③陳述問題;④概念設計;⑤選擇方案;⑥具化方案;⑦細化方法;⑧形成施工圖紙。其中,概念設計是最核心的,需綜合考慮科學原理、生產實踐、商業利益等多個方面;并指出工程設計的過程是迭代的,而非線性的。美國馬薩諸塞州率先將工程設計融入其技術教育中,在2001年頒布的《馬薩諸塞州科學、技術和工程課程框架》中,將工程設計的過程分為8個步驟,分別是:①明確需求或問題;②研究需求或問題;③開發可能的解決方案;④選擇最佳的可能的解決方案;⑤構建原型;⑥測試和評價解決方案;⑦交流和討論解決方案;⑧再設計。
盡管目前對工程設計的過程并沒有普遍認同的一般流程,但一些步驟被公認為是必要和重要的[4-6]。例如,第1,明確工程難題。工程設計的發生源于實際難題、需求或欲望,一個社會性難題可引發一系列的工程難題,明確的工程難題可使工程師的工作更具有目的性。第2,收集解決這一難題的各種不同想法。工程師通常需要通過頭腦風暴和試驗提出一系列不同的可能的設計方案,從而進行下一步的研究。第3,構建并測試模型和技術原型。通過模擬和測試,工程師可獲得真實且有參考價值的測試數據,并基于此分析各種潛在解決方案的優點和局限性。第4,最優化。每種解決辦法的提出都要經過權衡工藝可行性、相競爭的功能標準、成本、安全、美觀和合法性要求等過程。通常,不會只有一個正確的解決方案,而是一系列的方案,最優方案的選擇取決于評價標準。
3 工程學中的核心概念與基本能力
盡管下文將分別介紹工程學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能力,但在實際的工程學設計過程中,概念的理解和應用與能力的提升和應用是相互融合的,二者密切相關,無法獨立分開。
2008年,美國國家工程院和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聯合委托西爾克(Silk)、彼得羅(Petrosino)等,就理解和提升K-12工程學教育所需的概念和能力分別進行綜述研究。如上所述,工程設計的過程含有多個重要的步驟,在這些步驟中涉及到3類概念:基礎的科學和數學概念、具體領域的工程學概念和通用的工程學概念。西爾克等綜述了美國及國際的技術和工程學教育標準及研究文章,提出了通用的工程學核心概念及其類別下的工程學概念,其中最重要的2個核心概念為“系統”和“最優化”[7]。
系統是由相互協作的多個獨立組件構成,從而共同完成一項功能的物體或過程,工程師需要從系統的角度考慮:①各個獨立組件的功能是什么?②各個獨立組件之間的關系是什么?③各個獨立組件或組件組合對于系統的功能有什么影響?
系統中組件的結構、它們的功能,以及行使其功能時的行為,稱為結構-行為-功能,簡稱SBF。研究發現,兒童在語前時期已具有強烈的因果關系意識,但低學段(2~5年級)的學生尚不能自發使用因果關系[8],即他們更能夠認識到某一物體的功能,但不能意識到物體潛在的結構是如何行使功能的。在參與設計模型時,逐漸增加模型的復雜度能培養和提高學生對結構-行為-功能這一概念的理解。有效的教學策略為:①指出班級所構建模型的局限性;②當學生自己無法發現更多的信息時給予適當的提示;③鼓勵學生小組追求更具體的設計挑戰。
系統中各組件之間因相互作用會產生某些特性,而在系統組成前的單個組件并不具有此性質,這種特性在系統中稱之為涌現性質,是一種總體大于個體之和的概念。雷斯尼克(Resnick,1996)認為,人類傾向于將系統行為歸因于某個核心組件,而這種傾向是頑固的,甚至是天生的,而且這種傾向是理解涌現性質的主要妨礙。在課堂中開展模擬活動有助于學生理清系統不同層級之間的關系,進而幫助學生轉變其固有傾向。與參與式模擬相比,基于計算機軟件的模擬更便于學生進行操作和探索,從而能更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涌現性質等跨系統水平的概念。
最優化指的是使設計的功能或效率最大化的過程,即對多重變量的權衡過程。
多重變量,指的是工程設計過程中的各類輸入變量,對這些變量進行不同處理可得到最佳的解決方案。認知負荷理論(CLT)表明,在各個年齡段,短期記憶的最大限度一般為5~7個變量。在不使用分塊、捆綁或線性處理等策略加強記憶時,即使是有經驗的成年人也只能同時處理3~4個變量[9]。在K-12工程學教學中,簡化任務和使用數學及物理學方法表示是有效的教學策略,具體的教學方法有構建多變量系統的分析模式、構建記憶組塊、功能式分解系統、數字化筆記等。
權衡,是指對輸入變量和輸出變量的考量,當改變某一個輸入變量影響了其他輸入變量對設計結果的作用,權衡就發生了。權衡并不是各個輸入變量簡單相加的過程,各個輸入變量之間還可能存在拮抗作用。K-12學生也許不能規范地理解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因而也不易理解權衡的概念。用數學方法表示可明確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讓學生參與從單個變量到多個變量連續的權衡過程,可幫助學生理解權衡的概念[10]。
為了理解和進行工程設計,在理解工程學核心概念的同時,還必須習得工程學基本能力。彼得羅[11]提出了參與工程學設計與再設計的基本能力:定義難題,明確需求,分解系統,提出解決方案,繪圖和創建模型,試驗和測試。其中,對繪圖和創建模型、試驗和測試等能力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多。
關于繪圖和創建模型,學生傾向于用繪圖記錄個人經歷或表達個人情感,并傾向于認為設計是一個線性過程,而不是繪圖-修改的迭代過程,傾向于認為模型就是真實物體小型的簡單模仿。為了培養學生繪圖和創建模型的能力,有效的教學方法包括:①在不同學段按從易到難的順序逐漸開展合適的建模活動;②學生以小組的形式參與探究活動,并在探究活動中強調建立和使用不同類型的模型;③組織學生討論和評價自制的模型,從而提升其繪圖和創建模型的能力[12]。
試驗和測試在工程設計過程中用于檢測最優化的水平及是否滿足各類功能標準。測試對象既可以是完整或部分的原型,也可以是虛擬模型。測試時常含有多個變量,學生傾向于注重結果而不是分析,傾向于一次改變多個變量且將結果的變化歸因于每個變量。在教學中,測試和評價通常是由教師進行的,教師應將評價與最初的設計相聯系,促進學生元認知的發展。此外,在教師評價的基礎上,應豐富學生所設計產品的消費對象,當消費者是學生本人或其家人時,學生的表現會更好。
在理解工程學核心概念和習得工程學基本能力的過程中,智力發展水平和相關知識背景是2類主要的限制因素,但采取合適的教學方法能有效突破限制。教學過程需注意以下3點:①保證足夠的課堂時間,開展深入的工程設計活動;②從易到難連貫一致地進行工程學概念的教學;③有目的地迭代工程學設計過程,在逐步精致設計的過程中,鍛煉并提升學生的工程學能力[4]。
4 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展工程學教育的方式
科學、數學、技術都有其學習標準和較長的K-12課程史,與之相比,基礎教育中的工程學仍處于起步階段,既沒有內容標準,也沒有教師專業發展指導,更沒有國家或州所制定的學習成就評價[3]。如何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展工程學教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006年,美國國家工程院和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教育中心成立了K-12工程學教育委員會,在長達2年的時間里,委員會召開了5次會議,分析了現有的K-12工程學教育,提出了工程學課程設計的3 項原則[4]。
原則1:K-12工程學教育應強調工程設計。“工程設計”是工程學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工程設計是一個潛在的有用的教學策略,工程設計的課程或活動需具有以下的特征:工程設計必須具有高度的系統性迭代性,考慮多方面的限制條件,認為難題具有多種解決辦法,為學習科學、技術、數學等重要概念提供有意義的內容。
原則2:K-12工程學教育應融合與兒童認知發展相適宜的數學、科學、技術的知識和技能。工程設計中包含許多科學、數學和技術的跨學科概念,例如科學概念和科學探究方法可支持工程實踐活動;數學概念和計算方法可支持數據分析和建模過程;技術概念和技術可展示工程設計的成果。
原則3:K-12工程學教育應促進工程學思維。工程學思維與21世紀重要的公民技能保持一致。工程學思維包括:系統思維、創造力、樂觀、合作、交流、道德考慮。其中,較之于基礎及高等教育中工程學教育的現狀,原則3應是重點培養對象。
為了評估發展K-12工程學內容標準的潛在價值和可行性,美國國家工程院于2008年贊助K-12工程學教育標準委員會進行了一項長達2年的研究。2010年該委員會發布報告《Standards for K-12 Engineering Education? 》[13],其中總結了支持和反對開發工程學內容標準的理由,以及委員會的最終建議。
支持開發工程學內容標準的理由包括:1)內容標準的建立可以最有力地表明工程學的課程地位,從而提高學校開設高質量的工程學課程的可能性;2)內容標準可以為課程設計者和教師提供指導,并促進教學材料和教師培養項目的發展;3)內容標準可以為課程改革提供連續一致的知識框架,并依據最新的認知科學的發現對現有的工程學課程進行改進。
反對開發工程學內容標準的理由包括:1)實踐經驗不足,既不知道如何有效指導學生進行工程設計,也不知道如何科學評價學生在工程學課程中的表現;2)師資力量匱乏;3)學生的課程負擔已較重,為工程學開辟獨立的時間和空間非常困難。
綜合以上觀點,K-12工程學教育標準委員建議暫不開發K-12工程學內容標準,而是將工程學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能力嵌入到科學、技術、數學等課程標準中。
2013年,美國頒布了《下一代科學教育標準》。此前,在美國的50個州中僅有12個州明確在其課程標準中包含工程學相關內容,但仍有14個州的課程標準中不含有相關內容。《下一代科學教育標準》的頒布顯著提高了美國基礎教育中工程學的范圍和質量[14]。在我國,隨著2017年《義務教育小學科學課程標準》和2018年《高中生物學課程標準(2017年版)》的頒布,工程學已正式進入基礎教育。這將有效推進我國基礎教育中的工程學教育逐步走向正規。然而,學生、教師,以及各級政策決定人員如何理解工程學的價值,學校如何解決資源匱乏、經驗不足的難題,社會資源如何有效融入并促進工程學教育活動的開展……這些都是目前推進工程學教育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如何全面有效地推進工程學教育,仍然需要進一步摸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