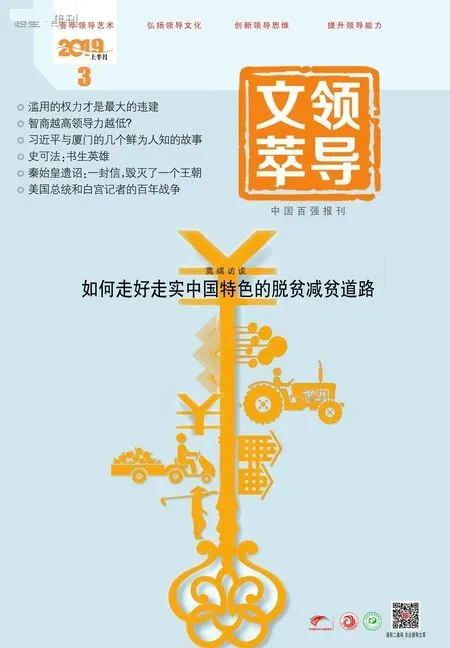宮廷政變與晚清政局
琳琳
晚清內(nèi)部勢(shì)力變化
1861年在北京發(fā)生的辛酉政變是晚清政治格局變化的一個(gè)重大轉(zhuǎn)折點(diǎn),西太后慈禧通過聯(lián)合恭親王奕發(fā)動(dòng)了奪取政務(wù)大臣肅順等人中央權(quán)力的政變,掌握了清廷大權(quán),改變了咸豐帝生前預(yù)想的權(quán)力制衡的局面。政變后,慈禧太后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大力拉攏恭親王奕,給予奕諸多特權(quán)。而奕則羅致文祥、李堂階等人做智囊和助手,培植自己的勢(shì)力。我們不難看出,辛酉政變導(dǎo)致的清廷內(nèi)部人事調(diào)整在一定程度上給晚清政局帶來了一些新的動(dòng)力,以奕為首的中央官員,以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為首的地方官員的雄起,甚至是洋務(wù)運(yùn)動(dòng)的興起也與辛酉政變的爆發(fā)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這一人事調(diào)整在一定程度上對(duì)鞏固晚清政局的穩(wěn)定有益,但與此同時(shí)也為后來清朝內(nèi)部分崩離析埋下了伏筆。
慈禧與奕在聯(lián)手奪權(quán)、排斥肅順等人這一戰(zhàn)線上顯得格外團(tuán)結(jié),但當(dāng)奕在中央的勢(shì)力足夠強(qiáng)大以致威脅到慈禧時(shí),權(quán)力心極強(qiáng)的慈禧便不能容忍,于是便有了1884年的甲申易樞。和辛酉政變一樣,二者都是晚清朝廷內(nèi)部的權(quán)力爭(zhēng)奪,但此次政變沒能給晚清帶來新的活力,中央大權(quán)收歸慈禧,清廷更加腐敗。甲申易樞發(fā)生在中法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之際,二者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甲申易樞爆發(fā)的表面原因是前線清軍在中法戰(zhàn)爭(zhēng)初期的接連失利,但其深層原因則是權(quán)力的轉(zhuǎn)換。1884年4月,慈禧太后與醇親王奕譞(xuān)一起策劃,以“委蛇保榮,辦事不力”的罪名,把奕、李鴻藻、翁同龢等一概逐出了軍機(jī)處,任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等五人為軍機(jī)處大臣。慈禧的此舉看似是要懲治在中法戰(zhàn)爭(zhēng)中的軟弱妥協(xié)派,其實(shí)只是慈禧計(jì)劃好的一場(chǎng)奪取奕中央大權(quán)的政變。從有關(guān)資料可以看出:新的軍機(jī)處并沒有積極組織力量準(zhǔn)備戰(zhàn)守,只是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把一些清流派重要人物派到地方上去擔(dān)任官職。甲申易樞,它不僅是慈禧太后對(duì)奕一個(gè)人的警告,也是對(duì)以奕為首的洋務(wù)派和地方實(shí)力派的一個(gè)警告。政變使一群更加沒有能力和智慧的封建官員掌握了晚清的實(shí)權(quán),慈禧太后的地位得到更加鞏固,但也使中國處于更加危險(xiǎn)的境地。
1895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zhēng)的大敗,使全國有識(shí)之士都為之震撼。以康有為、梁?jiǎn)⒊瑸槭椎木S新派在光緒帝的支持下開始了向西方深層次學(xué)習(xí)的征程。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的詔書,宣布變法。光緒的改革運(yùn)動(dòng)日趨激進(jìn),并預(yù)示了最后要對(duì)清帝國全部政治機(jī)構(gòu)進(jìn)行激烈改造的前景。如此,勢(shì)必會(huì)威脅到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發(fā)動(dòng)了政變,剝奪了光緒帝的權(quán)力,并把他幽禁起來。同一天,她還宣布重新當(dāng)權(quán)“訓(xùn)政”,開始了她的第三次攝政。戊戌政變的發(fā)生對(duì)晚清內(nèi)部的派別勢(shì)力消長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慈禧太后鏟除了以維新派為代表的一批相對(duì)激進(jìn)的勢(shì)力,控制了光緒帝,把重要的兵權(quán)牢牢掌握在自己親信的手中,使短時(shí)間內(nèi)出現(xiàn)的帝后兩黨之爭(zhēng)的局面戛然而止,再一次重新掌握了晚清政局。
與中國近代化的關(guān)系
中國的近代化是以生產(chǎn)工業(yè)化和政治民主化為標(biāo)志的,當(dāng)然它還包括了外交、制度、思想近代化等等,從一定程度上說它是隨著列強(qiáng)的入侵在中國逐漸發(fā)展起來的。而晚清每一次宮廷政變,都會(huì)深刻地影響著清朝的內(nèi)政外交,故亦對(duì)中國近代化的開啟和發(fā)展有著重要影響。
1861年辛酉政變成功發(fā)動(dòng)之后,慈禧和奕上臺(tái)。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yàn)檗鹊纳吓_(tái)以及奕集團(tuán)的形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啟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隨著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得以奕為首的清廷官員開始萌發(fā)“求強(qiáng)”意識(shí),發(fā)動(dòng)了洋務(wù)運(yùn)動(dòng),開啟了中國工業(yè)近代化之路。洋務(wù)派興辦近代軍事工業(yè)和民用工業(yè);創(chuàng)辦當(dāng)時(shí)亞洲最大的海軍基地,設(shè)立海軍衙門;興辦新式學(xué)堂,派遣留學(xué)生;翻譯、學(xué)習(xí)西方文化和科技用以求強(qiáng)于中國。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更是開啟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序幕。雖然以奕為首的開明士大夫們的努力對(duì)晚清政局的改變只是杯水車薪,但是我們?nèi)匀徊荒芊穸ㄐ劣险兒蟮耐砬瀹?dāng)局者企圖挽救政局的努力。
以奕為首的開明士大夫在中國近代化進(jìn)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然而在開明士大夫們與頑固派爭(zhēng)權(quán)的宮廷政變中,奕敗下陣來。他的失勢(shì)勢(shì)必會(huì)一定程度上影響近代化發(fā)展的步伐。1884年的甲申易樞政變,慈禧剝奪了奕的實(shí)權(quán),對(duì)正在進(jìn)行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造成了嚴(yán)重的后果。其他的洋務(wù)派在奕的這次厄運(yùn)中看出了慈禧太后的本意,為明哲保身,他們不得不有所收斂。80年代后期以后,除了張之洞仍有作為外,幾乎不再有什么轟轟烈烈的舉措,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呈衰弱之勢(shì)。中法戰(zhàn)爭(zhēng)、中日戰(zhàn)爭(zhēng)的慘敗導(dǎo)致了洋務(wù)運(yùn)動(dòng)的結(jié)束,同時(shí)也讓國人對(duì)西方列強(qiáng)的認(rèn)識(shí)更進(jìn)一步,特別是從甲午中日戰(zhàn)爭(zhēng)的結(jié)果來看,先進(jìn)的中國人不再僅僅滿足于學(xué)習(xí)西方的科學(xué)技術(shù),把重點(diǎn)逐漸地從物器層面擴(kuò)展到制度乃至思想層面。
晚清的宮廷政變有一個(gè)很突出的特點(diǎn),就是三次重大的宮廷政變都由慈禧組織發(fā)動(dòng)并統(tǒng)統(tǒng)取得成功,三次宮廷政變似乎就是慈禧奪權(quán)、固權(quán)的一個(gè)發(fā)展過程。不得不說慈禧太后是一個(gè)政變行家,利用宮廷政變獨(dú)掌朝廷大權(quán),但這些政變不同于改朝換代、新勢(shì)力的奪權(quán),更沒有新的動(dòng)力注入,只是朝廷內(nèi)部勢(shì)力的角逐,因此當(dāng)然不能使晚清政局得到一個(gè)根本性的轉(zhuǎn)變。不過,雖然這些政變沒有使晚清擺脫亡國之危,但是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晚清政局,在晚清政局向下的走勢(shì)中充當(dāng)了一劑調(diào)味劑,影響重大。
(摘自《法制與社會(huì)》)
- 領(lǐng)導(dǎo)文萃的其它文章
- 漫畫二則
- 小幽默6則
- 資訊四則
- 采英拾貝
- 《價(jià)值視野下的國家治理》等5則
- 精神充電 是持久發(fā)展的動(dòng)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