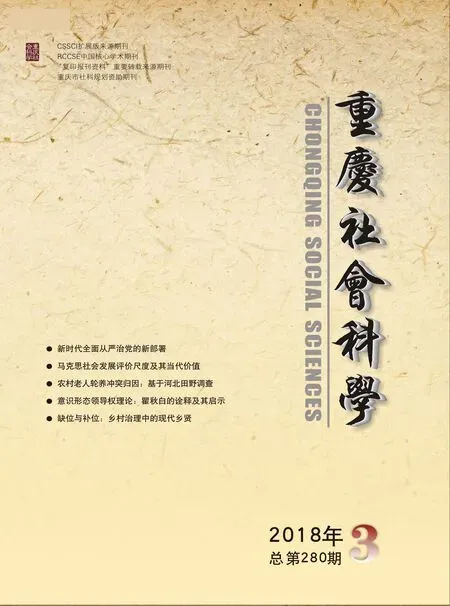西方史學界對古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的研究綜述
李偉芳
(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陜西西安,710062)
古羅馬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形成了發達的法律體系,該體系構成了其社會制度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而且,不同于中國古代社會法律倫理化的發展特征,古羅馬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它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在法與道德的矛盾運動中,沿著一條將道德不斷法律化的途徑而發展起來的。鑒于這一問題的重要價值,西方的羅馬史學界亦早在古羅馬時期就開始從不同角度對于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進行了探討。相較而言,該領域尚未引起國內史學界的充分重視。①國內史學界已有部分學者注意到了相關問題并產出了一些成果,有關古羅馬道德風尚的衰落的代表性成果如林中澤的《羅馬全盛期的道德危機》[《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楊俊明的《社會道德的變遷與羅馬帝國的興亡——古羅馬公民社會道德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有關奢侈問題及其相關法令的研究如向東的《與九頭蛇的戰斗——羅馬共和國和我國唐代反奢侈制度的比較》(《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向東、陳榮文的《奢侈行為的法律規制:從古羅馬到現代》[《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有關廉政及其相關法律問題的研究如耿壽輝的《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廉政初探》(曲阜師范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劉小青的《羅馬共和國后期反選舉舞弊斗爭與共和國的衰亡》(《世界歷史》2016年第3期),王振霞、田德全的《羅馬共和國早期廉政初探》(《北方論叢》2007年第6期)等。這些成果對進一步推動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但總體來說,現有研究成果多以期刊文章為主,而且多以某一具體領域為研究對象,宏觀縱深的研究并不多見。因此這里擬從公民道德淪喪與共和衰亡之間的關聯、公民道德衰敗與立法規制的研究等方面對西方相關學術成果加以概述②由于資料和語言的限制,本研究所評述對象僅限于以英文發表或有中文譯文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研究的特點以及局限性加以初步探討,以期推動國內史學界對此問題的認識和了解。
一、關于公民道德淪喪與羅馬共和衰亡問題的研究
作為羅馬歷史發展、特別是共和后期歷史變革的產物,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的重要歷史背景即共和危機與公民道德淪喪,因此對這兩者之間關聯的探討構成了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
共和末年以降,古羅馬人就開始了對共和衰亡原因的反思,他們主要是從人的品行而不是體制的角度來進行審視,認為古羅馬人的道德史觀——傳統民族美德——造就了羅馬共和的輝煌、而道德的腐敗導致了共和的滅亡。對歷史發展進行道德詮釋的做法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羅馬史研究中產生了回響。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強調人的品質和貢獻、以人性取代神性作為考察歷史的尺度,故而對古羅馬的歷史和羅馬公民道德品質之間的關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馬基雅維里[1]、孟德斯鳩[2]和愛德華·吉本[3]等都對羅馬共和衰亡與公民道德淪喪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了解讀。他們強調人類歷史進步中的人的制度、法律和道德精神等因素的重要性,批判中世紀神學一統天下的蒙昧與落后,體現了啟蒙精神的本質,但是他們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強于精神而弱于實證的時代局限。
十九世紀以來實證主義史學蔚為大觀,對社會政治制度而不是人的道德品行的探究構成羅馬史研究的重點。但是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令西方世界的體制自信遭受重挫,體現在史學方面就是一些史家提出應在體制之外的精神層面去尋求社會興衰的原因。代表性史家理查德·E.史密斯就強調了作為羅馬精神(Romanism)基礎的mos maiorum(傳統道德習俗)的重要性。在他看來,mos maiorum是羅馬社會的根基;共和的失敗正是由于mos maiorum的失敗,即共和精神的衰敗;奧古斯都恢復了傳統道德規范,使羅馬重新具有活力和目標。[4]
二十世紀后半葉,西方學者進一步就古羅馬作家提出的道德衰敗與共和衰亡存在因果關系的命題的可信性進行論證。兩篇非常有影響力的論文分別出自安德魯·威廉姆·林托特(1972)[5]和芭芭拉·萊維克(1982)[6]。林托特的結論是羅馬史家將共和衰亡歸咎于希臘化影響下的道德衰腐的源頭在于格拉古時代,當時羅馬人在面臨格拉古事件帶來的巨大災難時,重申了納西卡有關迦太基滅亡和東方財富導致羅馬道德滑坡的觀點,并經皮索、波賽東尼奧、狄奧多羅斯、薩魯斯特等作家的記錄而流傳后世。萊維克在林托特有關研究的基礎上將問題更推進一步,通過分析羅馬人道德觀的矛盾之處,萊維克指出,羅馬人對共和衰亡的道德解讀其實是由于他們沒有認識到羅馬共和機制中個人—集體的內在張力關系。在她看來,共和末年羅馬國家面臨的困境,并非由于公民道德品行的失范,而是強人政治的興起打破了原有的張力關系,從而導致了共和國向帝國的轉變。
林托特和萊維克的論斷反映了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古典史研究者對羅馬道德衰敗與共和衰敗之因果關系的主流態度——認為古典史家用以解讀共和興衰的道德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是修辭性的、重復的、層壘的內容,故而主張現當代史家在從事探究時應盡量避免受其左右。
二、關于羅馬公民道德傳統及其特征的研究
如上所述,二十世紀以來的史學界主流已基本摒棄了對羅馬共和國興衰進行道德解讀的做法,但是對羅馬社會歷史發展中道德傳統及其特征,史學界仍保持了較高的學術熱情,并產出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成果。其中唐納德·厄爾的《羅馬的道德和政治傳統》是英語學界有關羅馬倫理道德傳統的重要論著。[7]該書的突出特色在于其強調了羅馬歷史發展中政治與道德緊密交織的傳統,揭示了羅馬政治理論和行動所依賴的道德基礎。厄爾認為,“羅馬人都是從個人和社會的角度,即道德的角度來看待政治問題”[8]。該書在材料的使用上相當廣泛,在歷史、文學等傳統史料之外,還運用了墓志銘、頌詞等補充材料,全書雖篇幅不大,但是論點明晰、論證有力,因而被稱為英語世界對羅馬道德倫理學思想傳統的最佳導論。[9]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受人類學、文化學和社會學的影響日益加深,羅馬道德傳統的研究也反映了這一研究動向。凱瑟琳·愛德華茲的《古羅馬不道德政治》[10]一定程度上正是福柯有關性、權力和話語理論影響的產物。在福柯的理論框架下,愛德華茲將精英階層所進行的道德抨擊視為象征性話語和實施政治控制的手段。她試圖通過分析羅馬人所認為的“不道德”行為來揭示蘊含其中的羅馬人的價值理念,特別是他們如何用道德的語言來進行自我認識和身份界定。但是,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愛德華茲的研究強于思想觀念,但在史料的駕馭上略顯薄弱,其中某些史料的運用失誤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該書的價值。[11]
同樣體現出文化學和社會學對歷史學影響的相關研究還有與愛德華茲基本同一時期的卡爾·卡林斯基[12]。在其對奧古斯都時期文化史的研究中,他對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價值觀、理想和思想進行論述,著重揭示奧古斯都auctoritas(權力)的思想文化根基。卡林斯基認為權力是奧古斯都時期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方面,在文化層面對權力的構建是奧古斯都樹立其作為統治者和道德領袖的合法化形象的重要手段。
二十一世紀初,邁爾斯·麥克唐納[13]考察了羅馬倫理道德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概念之一——virtus(美德)的詞義和內涵在共和最后兩個世紀中的歷史變化。盡管同樣以virtus為考察對象,麥克唐納與近半個世紀之前的厄爾在考察視角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麥克唐納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其所運用了類似于詞典編撰法的研究方法并細致考察了核心詞匯virtus的歷史演變。雖然他對virtus過于狹窄的定義和材料使用上的不夠嚴謹也受到指摘,但是他所強調的應對核心概念進行歷史考證的態度對于古史研究者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
三、關于羅馬公民政治道德立法的研究
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進程的主要成果是大量的道德法律,即以公民道德行為為規約對象的法律規定。這些法律的出臺主要集中在共和后期和奧古斯都時期,主要以公民公共道德特別是政治道德以及家庭倫理道德為規約范疇。針對上述立法范疇進行的研究是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研究中成果最為豐富的領域。其中針對奢侈和選舉腐敗及其立法的論述尤為多樣。究其原因,是由于奢侈和選舉腐敗是古羅馬權力階層道德腐化的最主要體現,也是古羅馬人眼中導致國家陷入危機的核心因素,因此,歷史學界圍繞這兩個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針對奢侈及相關立法的研究成果。奢侈是古羅馬人眼中最具破壞力的道德墮落,古羅馬共和最后兩百年頻繁出臺抑奢法,以期遏制奢侈問題的進一步惡化。英語史學界對相關法律的研究極為豐富,以下僅選取近二三十年來的代表作品進行簡要介紹。
道斯特(1996)對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間的抑奢法令進行了研究。[14]他指出抑奢立法的目的不僅僅在于規范政治精英的道德和自律,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確保富有的“外來者”必須經過精英階層的斡旋方能進入這一最高等級;另一方面,控制或限制傳統庇護人制度在新形式下所面臨的壓力。
朱塞佩·達理-馬蒂亞奇和安娜·普利塞卡(2010)對古羅馬歷史上從公元前182年的法尼亞法到公元前18年尤利亞法的共計11項與抑奢有關的法規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觀點:古羅馬禁奢立法的產生是源于共和羅馬的最后兩個世紀里軍事和經濟擴張而形成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不對等。[15]在他們看來,古羅馬統治階層通過相關抑奢法律并不是為了執行而只是為了表明政治立場。他們這種著意抑奢法律的表達功能而無視其社會規范作用的觀點比較片面且說服力不足。
此外,埃馬努埃拉·贊達(2011)的專著是近年來這一論題的重要成果。[16]他一方面強調了抑奢法令與同時期的道德譴責之間的關聯,但另一方面明確指出對于奢侈問題法律化這一復雜問題,任何單一因素都不足以得出全面的解釋,需要從道德、社會、經濟、政治等多角度進行分析。贊達專著的突出價值在于以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國、意大利、日本的抑奢法令為參照項,對古羅馬抑奢法令的動機和目的進行了多元解讀,避免了單一論的片面和誤導。
整體說來,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界針對奢侈和抑奢立法的歷史研究角度和方法更為多樣,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時期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影響,其研究重點也從考證相關史實(如抑奢法令的頒布者、時間、具體內容)到更進一步深入挖掘奢侈的政治、社會和人類學意義,從而多方面、多層次地探索抑奢法的動機和價值。
除針對羅馬歷史上的奢侈和抑奢法令的研究之外,圍繞反選舉舞弊的立法歷史考察也是羅馬道德法令歷史研究的重點,其中安德魯·威廉姆·林托特(1990)的《羅馬共和國的賄選》是一篇極具有影響力的論文。[17]該文探討了羅馬共和時期的賄選與當代賄選問題的不同本質,并指出,在羅馬,賄選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因庇護制度而形成的競選者與選民之間的聯系,使得選舉的結果更加難以預測,而且在羅馬賄選是人們所共同認可的政治場景的組成部分。林托特該文的一大特點在于為彌補共和歷史有關賄選和立法的資料的相對不足,運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以英國歷史上的賄選現象為類比對象,揭示賄選在顛覆既有依附關系、建立起新的社會關系方面的正當作用。該文體現了林托特史學研究的資料翔實、論證有力的學術特點。
同樣對羅馬選舉舞弊現象持有理解態度的還有艾倫·A.鮑厄勒(1990)和亞歷山大·雅克布森(1992)。鮑厄勒的博士論文對凱撒獨裁之前的羅馬選舉舞弊現象及其相關立法進行了研究。[18]鮑厄勒認為選舉舞弊現象是羅馬選舉體制的邏輯產物,它和羅馬社會的幾個基本特征都相關,包括榮譽階梯、新人對社會、政治體制形成的挑戰、門客制度。因此,產生于羅馬政治體制內在特征的選舉舞弊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是不可根除的社會特征,故而約束選舉舞弊的法律也就不可能產生任何實際的約束作用。雅克布森也對羅馬共和的選舉制度和晚期的期賄選問題進行了研究。[19]他的研究旨趣在于通過深入分析羅馬的選舉制度、賄選的范圍、特征以及與選舉有關的各種慷慨贈與行為,來揭示羅馬共和后期政治制度的本質以及民眾在政治體制中的參與程度和影響力。雅克布森認為賄選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精英關心平民的需求,緩解了階級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該文的產生是在二十世紀末期有關羅馬政治貴族制-民主制之爭的大背景下,因此,雅克布森更為注重的是賄選與民主政治的關聯而不是其道德意義。總的說來,林托特、鮑厄勒和雅克布森都否認了賄選必然有害的現代觀點,而是從具體的歷史背景層面探究賄選的意義。
西方學界之所以對羅馬上述涉及奢侈和選舉舞弊的權力階層道德腐敗現象始終保持較高的研究興趣,不僅僅在于這些問題本身是羅馬歷史發展的重要特點及內容,更重要的是在古代羅馬奢侈和舞弊行為都不僅僅是道德腐敗的結果,還和政治制度尤其是選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對相關問題的研究熱情不僅僅是學術熱情,更是對現實問題追本溯源的需要。
四、關于羅馬公民家庭倫理道德立法的研究
除上述政治道德及其法律化的研究之外,羅馬公民家庭倫理道德及其立法問題也是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奧古斯都所通過的反通奸法和婚姻法,首次以強制性法律手段干預公民家庭倫理道德問題,故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由于時代的歷史重要性和史料的相對豐富,該問題歷來是西方史學中的研究重點,相關研究成果不勝枚舉,內容涉及對其法律文本復原、歷史背景、立法目的、歷史價值等多方面,這里僅選擇二十世紀以來不同階段研究視角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論述予以介紹。
二十世紀上半葉,科比特出版了至今仍被認為是研究羅馬婚姻家庭法律方面標桿著作的《羅馬婚姻法》,他認為通奸法是“對女性不斷增加的自由和輕率行為的必要的抑制”[20]。同一時代的拉斯特[21]強調奧古斯都的婚姻立法是為了提高大同盟戰爭后嚴重下降的意大利人口。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者的視野更為寬廣,他們不再將視線局限于奧古斯都道德立法的人口和倫理意義,而是將之放在更為宏大的背景下、探討奧古斯都道德立法與其帝國發展的關聯,特別是其對初建時期新舊整體接替的意義。理查德·弗蘭克則強調家庭立法作為奧古斯都意識形態組成部分的意義,認為立法真正達到的結果是加強了帝國文章中保守的、仿古的傾向。當這個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的道德習俗正在變得愈發城市化和個人主義時,鄉村的、家長制的、傳統的機制被樹立為社會的典范。奧古斯都的立法是針對改革和復蘇的,但它事實上只是造就了對古老價值觀的懷舊和對新現實的鄙視。[22]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礎上,卡爾·蓋林斯基進一步論證了從人口的角度來解釋立法動機的不充分性,他把奧古斯都的道德立法和其整個統治計劃相聯系,提出其中貫穿了奧古斯都帝國主義擴張的思想,是“奧古斯都帝國主義野心的必然結果”[23]。他認為奧古斯都深受斯多葛派哲學的影響,尤其將該理論中道德優秀者治國的思想運用到自己的元首制統治政策中,從而也對奧古斯都的立法進行了意識形態的解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研究視角對歷史學構成的影響日漸顯著,并在八十年代達到了高點,這一時期也掀起了婦女史的研究熱潮。在此背景下,貝麗爾·羅森在科比特基礎上對女性通奸行為做出了新的解讀,她認為羅馬女性“在尋求一種與以往不同的關系時(這種關系很有可能是與同社會地位的人的通婚),一些女性會選擇不僅僅是與人通婚,還會與比自己身份低微的人發生關系或是結婚,而對于相關法律(由男性制定)對這種行為的反對不屑一顧。”[24]她的這一觀點實際上是把羅馬上層女性的性不當行為視為是對強加在特權階層女性身上的約束的一種可理解的反抗。
在有關奧古斯都道德改革研究已經取得極為豐富成果的前提下,二十一世紀的研究者挖掘出更為獨特的研究視角,如卡特里娜·約克[25]以受法律制約者——羅馬貴族女性——的反抗為切入點,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誠然,由于資料的限制,有關羅馬婦女反抗立法的證據極為缺乏,故而帶有極大的推測性,但是約克的研究不失為十分有益的嘗試,為我們從不同視角進行道德立法研究打下了基礎,研究者亦可借鑒他所提供的線索繼續挖掘論證女性在道德立法中的作用和影響。
五、其他相關研究
除上述研究成果之外,英語學界還在其他領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對古羅馬社會某一時期內道德法律的綜合性研究。此類研究成果相對較為匱乏,這應當與學界尚未對道德法律的概念和范疇形成統一界定有關。在現有成果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路易斯·克萊頓·圖爾加(1967)的博士論文《元首制早期帝國對道德和行為的規范》[26]和德里·波德·邁爾斯(1987)的博士論文《被禁止的歡娛:古羅馬抑奢法及道德衰敗的意識形態》[27]。
圖爾加對奧古斯都到圖密善之間的針對公民道德和行為的國家法律和規約進行了研究,并將這一時期針對道德行為的法律和規約劃分在兩大范疇之下,一是旨在維護羅馬風尚的內容,另一是旨在維護公共秩序的內容。圖爾加的論文是當時少有的關于元首制早期道德法律化問題的專題討論,他的文章對相關資料的收集和匯總也為后續研究打下了基礎。但是作為此一論題的初始性研究,圖爾加論文的缺陷也是比較明顯的。其一,該文篇幅較短,且結構過于簡約,難以對主題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其二,文章以述為主,側重于對相關法規內容的描述,而缺乏對其更深層次內容的討論;其三,結論部分僅限于對相關法令的簡要總結,而未能將其特點和意義進行概括和歸納,這也是這篇論文的最大弱點所在。
邁爾斯的博士論文雖然以抑奢法為主題,但事實上他對所論階段內的婚姻法和性道德法律也有所涉及,在古代羅馬的道德問題及其相關立法領域而進行的研究當中,稱得上非常有分量的成果。邁爾斯論文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所涉歷史階段中羅馬社會變化的方面、奢侈的體現形式、抑奢法令、其他相關限制歡娛的禁令等均以列表的形式呈現在附錄當中,有助于勾勒出這一復雜歷史問題的簡筆畫,易于讀者把握主體脈絡。但是邁爾斯的論文在文章架構、排版布局、篇章銜接等方面稍有欠缺,文章整體上有些雜亂,缺乏主線的有機貫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文的整體價值。
此外,一些學者的成果雖然未以公民道德和相關法律為主題,但其研究也對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有所涉及并且意義匪淺。如凱麗·威廉姆森(2005)借用了統計學的方法和模型大膽嘗試將從公元前509年共和國建立開始到公元1世紀末年約600年的歷史中散落在文獻中的立法提案和最終得以制定的法律進行了匯總分類。[28]她的匯總對于學人梳理羅馬歷史上的道德法律具有較高的意義。雖然該書的內容過于龐雜,且存在法律分類牽強、論證不夠充分的缺點,但是她的研究思路確實對于理解立法如何促成羅馬人的團結一致有積極的意義。
此外,安德魯·華萊士-哈迪爾在其專著《羅馬文化革命》中借鑒了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他從語言轉碼的角度來探討共和后期至帝制初期之間的文化轉型,并在這一轉型歷史背景下,探討了共和末期統治精英對道德習俗控制力的喪失和轉型社會中奢侈話語及奢侈立法的意義。[29]該書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對于多層次、多角度開展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如上所述,長期以來西方史學界對羅馬公民道德建設及其法制化發展保持了一定的研究興趣。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史學界在從事相關研究時所運用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也呈現新的面貌。特別是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社會學和人類學等跨學科理論的引入使得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如二十世紀后期至今對羅馬奢侈和相關法令的研究的相對豐富就是受到了社會人類學的影響,從而使史學家對羅馬社會的捐贈、宴會、公共娛樂等問題產生了新的興趣。史學界對道德法律化與文化權力、意識形態等問題的關注是由于受到了社會學的影響。除過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及方法之外,經濟學、人口學、統計學、語言學、法史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模型也被參考和借鑒。史學比較的方法也得到更多的重視并在具體研究中予以運用。
總的來說,羅馬公民道德法律化問題在西方史學界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鑒于這一問題的重大意義,未來的研究勢必更加深入和廣泛。就其發展動向而言,公民道德法律化作為共和向帝制這一歷史巨變的產物,其與帝國發展的關聯也自然需要更深入的考察。此外,現有的道德法律化研究因為研究視角和材料的限制,基本上局限于對羅馬精英階層男性公民的研究,伴隨著婦女史和自下而上歷史觀的發展,更多的關注力將會被置于女性以及普通羅馬民眾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規范以及道德法律對他們的影響。對我國羅馬史研究者而言,當代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社會轉型時期道德法制建設問題需要研究者更加關注羅馬道德法律化對轉型時期價值危機、道德失范等問題的意義。特別是隨著近年來我國道德建設、法制進程的不斷深入,借鑒羅馬道德法律化進程的經驗來完善我國的道德和法制建設是深入羅馬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現實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國—羅馬的比較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發展蔚為大觀,這一趨勢對中國羅馬史學研究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契機。
[1](意)馬基雅維里.論李維[M].馮克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法)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M].婉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3](英)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M].黃宜思,黃雨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4]Richard E.Smith,The Failure of the Roman Republic[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
[5]Andrew.W.Lintott,Imperial Expansion and the Moral Decline in the Roman Republic[J].Historia,1972-21(4):626-638.
[6]Barbara Levick,Morals,Politics,and the Fall of Roman Republic[J].Greece&Rome,1982-29(1):53-62.
[7][8]Donald Earl,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of Rome[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p17.
[9]L.C.Becker&C.B.Becker ed.,Encyclopedia of Ethics[M].Garland Publishing,1992:480.
[10]Catharine Edwards,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 in Ancient Rom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1]Miriam Griffin,Review of 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94(184):186-188.
[12]Karl Galinsky,Ideas,Ideals,and Values,in Galinsky ed.,Augustan Culture:An Interpretive Introduction[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13]Myles McDonnell,Roman Manliness:Virtus and the Roman Republic[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4]Molly Ann Rosser Dauster,Roman Sumptuary Legislation of the Republican Era C.200-100 B.C.[D].Dissertation of Texas Tech University,1996.
[15]Dari-Mattiacci,G.&Plisecka.A.E.,Luxury in Ancient Rome:Scope,Timing and Enforcement of Sumptuary Law[J].Legal Roots,2010(1):pp1-27.
[16]Emanuela Zanda,Fighting Hydra-Like Luxury:Sumptuary Regulation in the Roman Republic[M].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11.
[17]Andrew W.Lintott.Lintott,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90-80(1):1-16.
[18]Ellen A.Bauerle,Procuring an election:Ambitus in the Roman republic,432-49 BC[D].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Michigan University,1990.
[19]Alexander Yakobsen,Petitio et largitio: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J].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92(82):32-52.
[20]P.E.Corbett,The Roman Law of Marria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
[21]H.Last,The Social Policy of Augustu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0[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4.
[22]Richard I.Frank.Augustus’Legislation on Marriage and Children[J].California Stud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1975(8):41-52.
[23]Karl Galinsky.Augustus’Legislation on Morals and Marriage[J].Philologus,1981-125(1):126-144.
[24]Beryl Rawson,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New Perspectives[M].London:Croom Helm,1986.
[25]Katrina York,Feminine Resistance to Moral Legislation in the Early Empire[J].Studies in Mediter-ranean Antiquity and Classics,2006(1):1-15.
[26]Louis Creighton Tulga,Imperial Regulation of Morals and Conducts in the Early Principate[D].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Ohio University,1967.
[27]Deri Pode Miles,Forbidden Pleasures:Sumptuary Laws and the Ideology of Moral Decline in Ancient Rome[D].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1987.
[28]Callie Willimson,Public Law in the Expansion and Decline of the Roman Republic[M].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2005.
[29]Andrew Wallen-Hadrill,Rome’s Cultural Revolu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