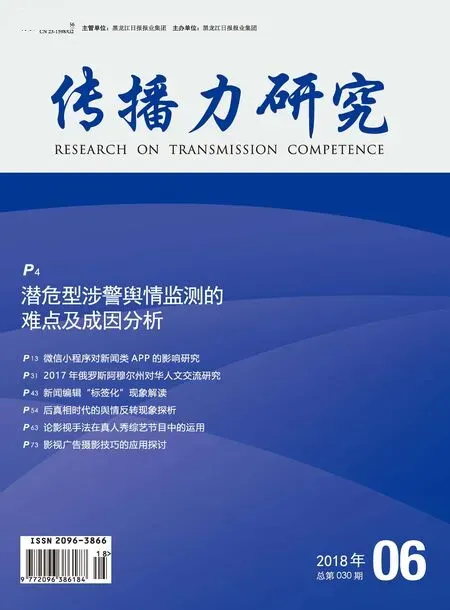全景敞視:西方反烏托邦電影的一種建筑學形象
西北大學文學院
近年來,隨著青少年亞文化的勃興、變動和滋長,美國的電影市場上迎合青少年的反烏托邦電影也興盛起來。其中,《移動迷宮》(The Maze Runner)、《分歧者》(Divergent)等好萊塢電影以序列形式出現,票房可觀,牢牢吸引著主流觀影者的注意力。青少年反烏托邦是當代文化焦慮的生動快照: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物種在面對未來可能時,不得不害怕[1]。但是年輕人可以得到足夠的鼓勵和啟發,實際上可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反烏托邦電影用視聽語言表達了對僵化教條主義的批判,對狂熱理想主義的否定,對威權主義的蔑視,對“目的至上論”的抗議和對“人神一體化”的反叛。而邊沁所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筑概念”,在反烏托邦電影所構建的世界里,無疑是相當重要的敘事要素。這種建筑學形象,一方面用來建構傳統權力觀(或曰“成人權力觀)的核心單元,另一方面,成為青少年反抗和摧毀的對象。無論是《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中那扇月亮型的控制塔,還是《饑餓游戲》(The Hunger Games)中游戲生成室,基本都是一個遠離于主人公行動場域的明亮的、繁忙的、主動執行和被動傳達的,用于遞攜命令和作用力的場所。福柯認為,敞視建筑機制在安排空間單位時,使之可以隨意被觀看可一眼辨認[2]。我們將會在電影中發現,全景敞視建筑的存在,更加有效地推動故事的發展。而故事主人公一定會保持其可見性,在與規訓的反抗、戰斗中,捕捉和逃脫、監視和隱藏、施加和解放等一系列動作性就連貫而出。這樣,青少年反烏托邦電影的敘事張力就被建立起來。
邊沁認為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所謂可見的,即當被囚禁者應當不斷地目睹著窺視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輪廓。所謂“無法確知的”,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3]。本文以電影文本《饑餓游戲》為例,將分析全景敞視在青少年反烏托邦電影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使權力可見
《饑餓游戲》因其描繪一位頭腦強硬的年輕女性凱蒂斯(Katniss)而廣受歡迎,作為電影和電影中游戲的主體,凱蒂斯事實上被兩種人所凝視,一是觀影者,他們觀看影像并與現實縫合;一是電影中的游戲控制者,他們生成場景、道具和補給等,虛擬的真實與二次元的身體結合,形成觀眾電子海洛因似的滿足。當凱蒂斯進入管道,上升,緩慢的白閃后,即喻示她進入了游戲的空間。此空間是人為的、全景敞視的空間,權力得以此而施加。福柯認為全景敞視建筑的主要后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可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這樣安排為的是使監視具有持續的效果,成為一個創作和維系權力行使者的權力關系的機制[4]。總之,被囚禁者應該被一種權力局勢所制約,而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權力局勢的載體。
《饑餓游戲I》中為我們展示了全景敞視建筑的特定具象:環形室內,藍色基調,光線明亮充足,人員按部就班,機器運作有序,像極了正常運轉的國家機器。但是,即可而來的殺戮在全景監視下展開,所有游戲參與者頃刻變成赤裸生命,以“貢品”名義可以殺害他人或被他人所殺害而不必擔負法律責任的生命。阿甘本指出,生產赤裸生命是至高權力最原始的活動,它要求:(1)對掌控死亡的權力的臣服,以及(2)生命無法挽回地暴露于棄置狀態[5]。亦即,全景敞視建筑建立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的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游戲操縱師能觀看一切,但不能被看到。通過這一重要機制,至高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于肉體、表面、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系。電影《饑餓游戲》由施惠國總統斯諾(Snow)的命令,在饑餓游戲的發生盤里出現了人物之間的對殺、毒蜂、怪獸等自然或非自然生命體,施于凱蒂斯們以不可抗拒的權力壓力。這是一種確保不對稱、不平衡和差異的機制,并由此,一種虛構的關系自動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保證一個被規訓機制徹底滲透的社會在一種易于轉換的基礎層次上的基本程序如常運作。正如電影中斯諾所期待的那樣——“讓他們臣服。”
二、使權力無法確知
西方反烏托邦電影中的權力狀態復雜而有效,通過全景敞視建筑上行下達。首先,在這種建筑物內,囚犯可以被觀看,但他自己卻不能觀看。與傳統那種由外部無法直接看到內部的黑暗牢房不同,在這個監獄里,監控對象需要被不可逆的單向的目光直接看到,這是監視和規訓能夠無所不在的前提[6]。全景敞視的環形監獄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可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楚門的世界》里楚門知道有人在設計他的生活后,試圖找到設計他生活的人,他沿著那個虛假世界的邊緣找到一扇門,此時,權力關系就此終結,電影戛然而止。這里,“被囚禁者應該被一種權力情景所制約,而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權力情景的載體”。權力情景,是指規訓權力的場景存在狀態;它與傳統權力的可見壓迫是異質的,它不再是點對點的直接暴力,而是在現實權力關系中建構出來的彌撒式的支配場景,所以它才會形成無處不在的毛細血管式分布和突顯的權力場景[7]。權力情景最終會被打破、被摧毀——《分歧者》中超越基因改造局的拯救行動、《移動迷宮》中末日之都的淪陷、《大都會》中總統的死亡——這本是西方青少年反烏托邦應有之意。
其次,福柯認為全景敞視建筑是權力支配機器。在開發性的隔離和可見性、規訓式的征服在肉體本身的存在中悄然生根,生成為被支配著自己的慣性生存機制。與傳統暴力型強制下的外部征服不同,規訓權力下的真實的征服是被征服者心甘情愿擁戴和自覺身體化的,它甚至表現為從野蠻到文明的實質邁進[8]。至高權力的根本生存意愿是存續權力,與反抗其權力狀態的主角們展開殊死搏斗。由于至高權力的不可預測,電影中凱蒂斯需要用不斷的行動來躲避至高權力的屠戮。這樣,電影人物行動性就豐富多姿,精彩紛呈。
至高權力是那個看到一切、監視一切和規訓一切的無臉大寫主人無面孔的治安權力,它沒有面孔,卻能感知一切。所有社會生活活動都成了治安權力的感知場合無形支配的等級網絡。《饑餓游戲》小說的作者柯林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饑餓游戲的社會政治色彩是特別有意創造的,以描述當前和過去的世界事件,包括利用饑餓作為控制人口的武器[9]。”
三、必要區隔
至高權力需要對權力對象做出區分和隔離,制造出差別,以否定人的平等性,為全景敞視隔離出必要的心理與物理空間,至高權力籍此獲得合法性。通過制造戰爭、饑饉等人為災難,資本階級獲得生命權力。電影《分歧者》的背景設定在反烏托邦的未來芝加哥,社會已經分化為五個派別;《饑餓游戲》影片一開始就設置了12個分區,饑餓游戲的目的就是挑起公民間的仇恨和殺戮。福柯認為,一旦權力形式直接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個人就會被分類。權力通過對個人進行標記,添加身份,并應用一套日常規則,以便他和其他人能夠識別。權力的形式使個人成為主體。“主體”這個詞在這里有雙重含義:通過控制和依賴來屈服于他人;并且通過良心和自我認知受到自己的身份的約束。這兩種意義都表明征服了權力的形式[10]。《饑餓游戲》中施惠國總統斯諾通過必要的區分和隔離——身份、地位、文化、財富等要件——他以分區的名義進行固化、扎緊籬笆、設定圈限,并進而挑起分區之間的歧視、嘲諷乃至仇恨,最終以所有的民眾都成為赤裸生命作為其統治的籌碼,可以任意剝奪他們的生命,這大概就是《饑餓游戲》游戲中視覺化的資本主義國家治理術。因此,對全景敞視監獄的摧毀和對至高權力的反抗,毫無疑問,形成反烏托邦電影敘事骨架。
對于年輕人來說,反烏托邦式電影的存在是為了慶祝個人和物種進步的可能性,而不會對我們和我們的后代在后現代環境中所面臨的非常真實的危險施加糖衣。青少年反烏托邦電影是種促進反思和批判的當代世界的虛構版本,它們興盛和普及日益表明,我們生活在人類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就像青少年觀眾的成員正在經歷他們自身發展的關鍵時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