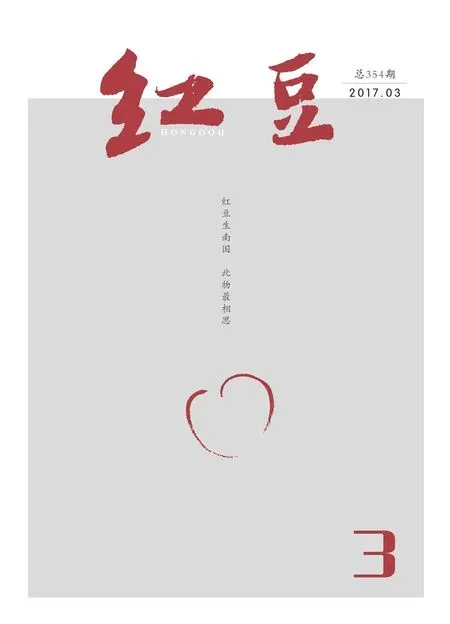沉默不是金(微篇小說)
何燕,女,廣西陸川人,廣西作家協會會員,廣西小小說學會理事,魯迅文學院西南作家班學員,玉林師范學院文傳院聘任導師。曾獲首屆浩然文學獎、首屆馮夢龍杯文學獎、第二十屆梁斌文學獎。
一聽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她就開始發抖。可邁進門口的那刻,她還告誡自己:什么都不能說。
你大膽地檢舉出來,我們會保護你的。瘦個子說。
保護?屁話!楊新和鐘寧當年就是信了這話,才被校長調走的。
她和楊新、鐘寧是同一批分到這個學校的。工作一年后,紀檢組突然來檢查,說學校有亂收費、報假賬現象。楊新和鐘寧被傳去協助調查。年輕的楊新和鐘寧經不起敲問,在他們許諾保護的情況下,道出了實情。而其他被調查的教師則守口如瓶。就這樣,楊新和鐘寧的如實相告,讓校長的工資降了一級,還挨了警告處分。
半年后,楊新和鐘寧成了支教對象,被調離縣城。這一去,就三年多,聽說離歸來日期還相差甚遠呢。
想到這,她就打了個寒戰。萬一自己也被調到遠離縣城的鄉村,那臥病在床的母親怎么辦?父親早逝,母親含辛茹苦帶大自己……為了母親,她咬了咬牙,更堅定什么都不能說。
任憑他們推心置腹地問、勸,她就是一字不說。她記得頭兒在大會上教過,只要沉默,就是勝利!現在對她來說,要想勝利,要想留在這個學校工作,要想照顧母親和弟弟,她唯有沉默。
瘦個子剜了她兩眼,走了出去。約二十分鐘后,他走了進來,讓她吃驚的是,他背后跟著她的學生——班長。班長看見她,臉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小聲說,老師,對不起,班上的同學都對他說了。
你再說一遍,瘦個子拿著筆對班長說。班長臉紅耳赤地看著她,不知所措。說吧,沒事,胖個子鼓勵著班長。
這個學期收的費用有:早餐費三百三十元;資料三套,一套是市的五十元,一套是縣的七十元,一套是學校的九十元;校服費八十元……班長停頓了一下,看了看她。
她的臉漲得通紅,眼里噙著淚水。胖個子咳了兩下,對班長說,你繼續。
教師節慰問費十元,班會費十元,自行車保管費二十元……
她的頭頂好像正上升的直升機,耳朵轟隆轟隆的,班長的嘴巴還在一張一合,可她什么也聽不見……
不知過了多久,“直升機”飛走了,班長不知什么時候走了出去,一切恢復平靜。
在鐵證如山面前,她無助地啜泣了起來。
胖個子遞過去紙巾。她接過擦了淚,說,好吧,我交代,其實不經上級批準擅自購買資料的,是我自己,這事學校不知道……
你現在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證據,是要負法律責任的!瘦個子氣呼呼地站起來嚷道。
她神色緊張地愣了一下。
胖個子說,你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攬,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弄不好會……
她低下頭,又哽咽了起來。好一會兒,她擦干了淚,咬了咬唇,說,真是我自己擅自收的錢,與學校無關!我錯了,我不該鬼迷心竅地要那些回扣錢,我馬上把錢給學生退回去,訂校服的錢我還沒上交,也馬上退回去……
她記不清自己是怎么走出來的,只記得出來前他們讓她簽了名,按了指印,她還清楚記得按指印時手是如何的抖。
出來后,她馬上撥通了頭兒的電話,急切地說,“校長,我可什么都沒說,自己全攬下了……
她笑了,因為她聽到了頭兒的表揚,說她好樣的,堅強、勇敢!還說有他在,讓她放心呢!
一星期后,和她同一批被調查的兩個老師被叫到了辦公室。同一天,這兩個老師被調到印刷室。她暗慶:幸好我什么都沒說!
一月后,她接到通知:由于作偽證,工資連降兩級,調到山巖鎮小嶂村任教。
她哭喊著給頭兒撥打電話,電話處于關機狀態,這時,她才想起有一段時間沒看見頭兒了。她逢人就說,我可是什么都沒說的呀!要知道,山巖鎮是離縣城最偏遠的一個小鎮。
她到處找頭兒,說什么都要讓頭兒知道,她可是什么都沒說呀!
頭兒的妻子拗不過她,給了她一個找頭兒的地址。
費了一番功夫,她終于找到頭兒的“隱身”之地陽光看守所!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去山巖鎮的路上時,楊新和鐘寧已回到原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