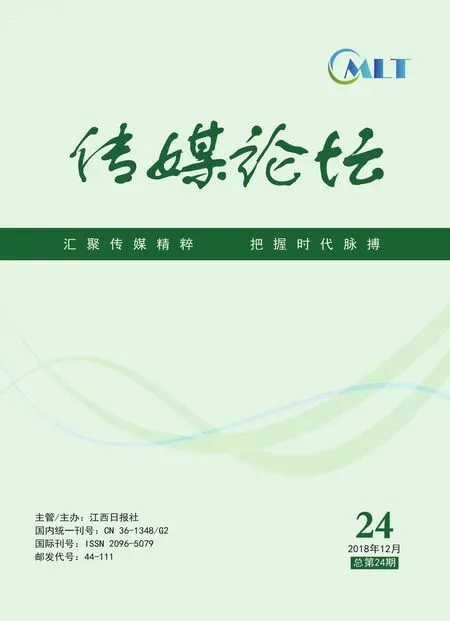新時代中國獨立紀錄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國 巍 劉雯嫻
(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一同步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文藝工作者講話中指出:“堅定自信、展示力量:讓中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不忘初心、服務人民:引導人們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樂的源泉;堅守理想、勇于創新:文藝創作是艱苦的創造性勞動,來不得半點虛假。”在黨和人民的熱烈期盼下,文藝工作者應該走出一條符合我們黨和國家利益、廣大人民利益的創新之路。
中國獨立紀錄片一路走來歷經坎坷,從1990年吳文光先生獨立制作《流浪北京》起,一部部獨立紀錄片如雨后春筍映入我們眼簾。隨著小型家用攝像機的技術發展和價格的親民化,民間編導的人數進一步壯大,更有大批電視臺編導離開電視臺嘗試獨立制片作品。這些編導紛紛與民間影像扶持機構合作,進行產業化的紀錄片創作,在作品數量上,逐漸取代了外籍作者、國有電視臺和中國港臺編導的話語地位,成為了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中堅力量。也從那時起,獨立制作的紀錄片工作者也成為了中國紀錄片創作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階段中國獨立紀錄片傳播途徑依然有限、接受主體群較為小眾、創作的現實意義難以實現。從紀錄片的整體來看,主流紀錄片的發展正趨于逐漸向好方向,一定意義上這種向好發展背后有著創作人員的不斷創新,但也離不開國家主流意志的推動和政策的支持,但紀錄片整體在社會文化中依然沒有將影片的現實意義充分發揮出來。
一、夾縫中苦苦支撐的紀錄片
目前,紀錄片與商業電影及各種大眾文化的長期“較量”中仍處于劣勢地位。《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7》數據顯示,在2016年中只有五部紀錄片走進了我們的院線,國家允許生產的紀錄片數量也不到30部。那么這與一年進入院線上百上千部的商業電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雖然有部分進入院線的紀錄電影突破了自我獲得了數千萬元票房,對于整個紀錄電影市場來說值得欣喜,但與商業電影動輒數億的票房相比仍是距之千里。再加之進入院線后,排片遭影院冷落,更多的需要通過點映來召集影迷集體觀影,觀影人數并不穩定。優秀紀錄電影《喜馬拉雅天梯》由導演蕭寒精心拍攝制作數年,進入院線后,一度勢頭很猛,但最終也只收獲了1153萬的票房。而同年上映的商業電影《夏洛特煩惱》輕松獲得14.41億元的票房。根據《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8》顯示,2017年相較于2016年紀錄片進入院線的紀錄片數量增加了一半之多,但仍然有經過審批、允許生產的79.5%的紀錄片沒有進入院線。雖然票房并不是紀錄電影的唯一追求,但紀錄電影也不應該是“院線毒藥”更不應該是“票房黑洞”,那么面對著紀錄片在傳播上與各類大眾文化競爭中的長期處于劣勢的現狀,需要紀錄片工作者們共同努力、堅持不懈地去做更多的事情。
二、中國獨立紀錄片的表達泥沼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對中國社會問題題材的持續性關注所體現的創作者個人的人文關懷、社會責任、個人意識尚未與主流表達達成“和解”。“苦大仇深”甚至成了中國獨立紀錄片部分創作者的代名詞,甚至有學者總結中國獨立紀錄片可以用“窮山惡水黑社會,小偷妓女長鏡頭”基本概括。中國獨立紀錄片在面對“敏感社會現象”時大多遵循直接電影式的不加干預的拍攝手法,認為這是在美學上遵循著所謂紀錄片的真實要求,其實直接電影的美學早已被證實不能完全還原真實。因為缺少引導會導致觀眾的理解可能會過于淺顯,從而在直接電影后出現了真實電影、自我反射式紀錄電影、行為表述式紀錄電影等各種紀錄片類型。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逃避現實,社會中的“敏感問題”我們需要去正視,但不能“為直面而直面”,要在解決問題的出發點之上,進行揭露和批判。如果一心堅持所謂的“紀錄”卻缺乏引導,缺少解決問題的誠意,只單單將社會現象進行簡單呈現,這對于消解問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并無實質性作用。
三、對于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意見及建議
在新時代的語境之下,筆者認為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主動改變,不斷與主流表達進行磨合,共同講述好中國故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一分屬于獨立影人的力量。
(一)時代脈搏與自身視點相結合
堅守中國獨立紀錄片的自身特色,在保持對具有現實性問題的關注、對底層人群的人文關懷以及用影像記錄生活的紀實美學的基礎之上,把握時代脈搏,關注新時代身邊發生的切實性改變,用影像發聲,展現中國自信、中國力量。第八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長片(提名)《自行車與舊電鋼》,導演邵攀在堅持對小人物的關注下并沒有選擇抨擊社會,反而通過對張鵬程和張宜蘇兩位主人公的建構顯示出了小人物對夢想的堅持、對生活的熱愛。張宜蘇這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卻有著屬于他自己的小人物哲學觀“戰勝世間一切的方法——不戰。”在他的世界中只有音樂,他熱愛音樂但堅持音樂是分享的。邵攀導演說初次進張宜蘇家中被其生活環境的臟亂差所震驚。張宜蘇收了很多徒弟卻始終分文不取,自己依靠著在“電子垃圾”市場倒賣電子產品謀生。影像所刻畫的兩位主人公有著很多普通人無法理解的行為、普通人無法接受的生活方式,但他們沉浸在音樂世界中,他們是熠熠生輝的,他們沉迷在自己藝術中的模樣,值得我們為他們鼓掌,他們的熱情也可以不斷激勵著每一個人不顧一切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二)增強影片的故事性和戲劇性
在獨立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發揚“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進一步探索紀錄片故事化、戲劇化的發展。這并不等于“背叛”,而是在基于現實狀況,從有益于中國獨立紀錄片可以長期發展的立場出發,做出的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自主選擇、自我完善。增加獨立紀錄片的故事性、戲劇性并不是向故事片進行“妥協”,只要我們講述的故事、傳遞的影像、訴說的信息是真實的、不為我們所虛構的,那么就無愧于“紀錄”二字。周浩導演的《大同》將我們帶入了一位中國市長的生活,影片以耿彥波在大同的拆遷改造工程作為主線,影片一方面從大局出發深度發掘耿彥波采取政策的初衷,另一方面毫不隱瞞地展示利益相關者的激勵抨擊,影片充分展示了耿彥波作為一名市長在人文關懷與城市發展之間的內心煎熬與掙扎。影片節奏有張有弛,通過剪輯將影像故事化、戲劇化,增加了影片的可視性,增強了思想沖擊。
(三)開拓影片的市場化和商業化道路
中國獨立紀錄片應該積極開辟獨立紀錄片市場化、商業化道路,現如今中國獨立紀錄片因為種種原因陷入了孤芳自賞的境地,缺少藝術消費過程,部分導演往往自己制作完成后只進行小范圍的、內部的傳閱,或是直接參加國外一些影展來獲取自身身份定位。彭吉象在《藝術學概論》中這樣說:“藝術作品被創作出來,是為了供人們閱讀或欣賞,如果沒人欣賞,它就還只是潛在的作品。”中國獨立紀錄片目前的發展是有待商榷的。在一定程度上,其發展違背了藝術發展規律、脫離了馬克思的藝術生產理論。彭吉象在對藝術鑒賞一般規律論述中這樣說道:“藝術家創造出來的藝術品,必須通過鑒賞主體的審美再創造活動,才能真正發揮它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如若中國獨立紀錄片再不充分市場化、商業化,會很難有效地發揮我們一直追求的初衷。當今,中國獨立影像點映機制已開始嘗試建立,以瓢蟲映像、大象點映為代表的新型放映機構也在探索著中國獨立紀錄片市場化、商業化道路。
四、結語
中國獨立紀錄片在持續改變中不斷發展自身,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因為多種原因自身生存現狀依然不佳。國內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在今后的創作中要把握時代脈搏和自身視點,不斷增強獨立紀錄片的故事性和戲劇性,從而增加影片的觀賞性,繼續開拓獨立紀錄片的市場化、商業化道路。不斷推動中國獨立紀錄片走向成熟,在新時代語境下講述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