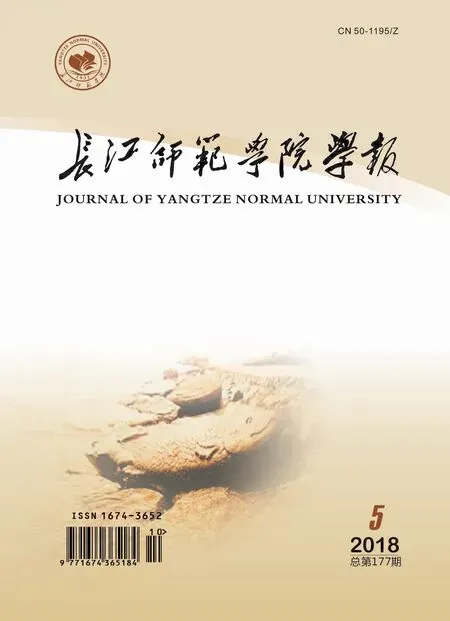黑格爾批判施萊格爾“反諷”說的思考
來慶婕
(中國海洋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青島 266100)
“反諷”是西方文論中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在德國浪漫派尚未誕生之時,“反諷”主要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在文學中得以應用,意指“言”與“意”在形式上的悖謬。18世紀德國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萊格爾從費希特的“自我”理論出發,將“反諷”的意蘊擴大到一種藝術創作甚至于一種人生態度的層面,進而上升到一種追求普遍真理的高度。但這一舉動卻招致了黑格爾的批判,黑格爾認為,施萊格爾將“自我”置于一種絕對自由狀態,將主體精神延伸至無限的領域,基于這種絕對自我的“反諷”也不再受到社會歷史等種種客觀現實的羈絆,從而忽視與現實人生與經驗世界的融合,造成理論的空洞性和現實不可操作性。基于對施萊格爾“反諷”說的批判,黑格爾認為,真正的美必須產生于客觀唯心,即主客相融的基礎之上,必須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一、對“反諷”目的論的批判
“反諷”是施萊格爾提出的重要文學理論概念,其具體內涵零散見于施萊格爾所著《批評斷片集》中。施萊格爾并未對其下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后世學者也認為“反諷”在施萊格爾的理論中并未得到系統化的闡述:“19世紀早期(這個時期人們對反諷問題進行著最為敏銳的反思),在這個時期里,對于反諷多有文論,德國浪漫主義對反諷已具理論體系。然而,甚至在這個時期,要對反諷做一界定亦似乎甚難把握。”[1]310但可以明確的是,它的提出是基于費希特哲學中“絕對自我”的理論。浪漫派主張藝術創作應以“自我”為中心和出發點,通過自我意識的運動變化,突破客觀物的阻礙,延伸到真理的范疇,以達到揭示普遍真理的目的,但這一主張卻招致了黑格爾的激烈批判。
早期德國的浪漫派受費希特哲學的影響。浪漫派的產生不是偶然,當現代技術以混混之勢侵入歐洲大陸,自然科學已經徹底瓦解了以往的信仰體系,當時無論唯理派還是經驗派,都急于為這種新變尋求智性的哲學支撐。靈魂無處皈依,人們再也無法通過自我反思和純粹信仰達到至高的精神境界,有限與無限之間開始出現巨大的鴻溝。正當人的內在靈性由于現代文明的沖擊而岌岌可危的關頭,德國浪漫派應運而生,其目的是為了弭平當時面臨的有限與無限的巨大鴻溝。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始終是橫亙在此岸與彼岸世界中的人類的永恒課題。費希特的“自我”理論恰好契合這一目的。費希特在《全部知識學的基礎》中提出:“我們必須找出人類一切知識的絕對第一的、全然無條件的原理。如果它真是絕對第一的原理,它就是不可證明的,或者說是不可規定的”[2]500,只有這個原理證明并規定他物。經過一系列邏輯推演,費希特將其設定為“自我”,而這便契合了浪漫派欲抬高自我意識和情感、將“絕對自我”看作最高本體的趨向,確定了它在形式上的不可動搖性。根據費希特的“絕對自我”理論,德國浪漫派認為藝術家作為創作主體是絕對凌駕于作品之上的,作品的形式、內容都要由主體來設定,這無疑帶有明顯的費希特哲學的痕跡。
施萊格爾對費希特的“反思”備加推崇:“費希特的形式中的優點是設定,然后就是走出自身并回復自身——即反思的形式。”[3]在《雅典娜神殿》中,施萊格爾稱贊費希特的“反思”深刻至極,似乎延伸進無限之中。費希特為確立絕對無條件的原理,提出應該對“最初可能認為‘是’的東西進行反思,把一切與此實際無關的東西抽出去”[2]500。因為反思作為最初的本原行動,可以從隨便一個點出發,既然是無條件的原理,自然不拘于具體經驗意識,從任意命題都可推演得出。在確定命題之后,便需要從中把經驗的規定性分離出去,“繼續分離直到最后再沒有什么可以從它身上分離出去時,剩下來的這個自己本身絕對不能被思維掉的東西就是純粹的”[2]501。這種推演方法類似于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唯一不可懷疑的是“我在懷疑”本身。同樣在《雅典娜神殿》里,施萊格爾對諷刺作出了三種基本表述:第一,“自我創造與自我毀滅的不斷轉換”或“作為作者與作品關系的自我限定”;第二,優美的自我鏡像和詩性反思的現象,這是施萊格爾對諷刺的象征性表述;第三,整體直觀的標志和中介。我們可以這么理解,諷刺是自我通過意識的自由拓展和詩化的語言將作品納入自身,其中的哲學術語則是借用了費希特的思想:自我創造,自我毀滅,還有費希特所認為的自我局限性或自我限定——費希特辯證法的三個環節。也有學者也認同將“反思”和“反諷”的具體指導思想看作同一的:“反思也是反諷的基礎,也就是說,它在藝術作品中與象征形式是完全同一的。”[4]121如此看來,費希特的“自我”和“反思”理論可以被視為“反諷”理論的策源地。
然而實際上,施萊格爾的“反諷”對費希特哲學的沿襲雖然有跡可循,但又并非簡單套用。作為對浪漫派文學創作的理論提升,施萊格爾借“反諷”闡釋了浪漫派文學創作的目的。而浪漫派的目的,簡單來說,就是若想實現有限與無限這一對立范疇的統一,勢必要高揚主觀性,使主體橫跨有限與無限兩大領域,以無限趨近真理。這也是施萊格爾提出“反諷”概念的初衷。施萊格爾既然是為了解決有限與無限這一矛盾,勢必要使真理在有限的物質世界即人生存的有限世界得到顯現,這就涉及到真理的傳達與昭示的問題,也即真理與語言的問題。真理由意識進入語言之中,便成為一個語言事件,換句話說,真理的性質發生了轉變。“這是因為宇宙間一切都處于‘轉換變化’之中,時間的維度中沒有任何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語言一經因果關系的劃分便僵化了,浪漫反諷所要打破的就是這種桎梏,而其所采用的方法則是‘悖理’。”[3]為保持主體思維和絕對真理的自由性和完整性,創作主體需要盡可能在不同領域、不同世界乃至整個宇宙之間自由跳躍移動。“人身上的宇宙詩人的火花,激發人的意志去把世界浪漫化。從而,人的這種渴念已不再是一種有限的力量,因為宇宙生成的無限之力已在如此渴念身上萌發,并急切地要返回自身,其結果是要求通過消滅有限的經驗性東西的自律性來造成一種更高的統一。”[5]95木心在《文學回憶錄》中這樣解釋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原理呢,可以講的,但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講;要給萬物定位稱呼呢,也可以的,但不能用通俗的既成見解來分類。”同樣的道理,如果用一般的方法、通俗的見解來對待真理,不僅不能達到目的,反而會離真理越來越遠。施萊格爾借用費希特的理論,用于真理的言說,從而破除有限與無限這一永恒課題的壁障和矛盾性。“對這樣一種產生于不受條件限制關聯之中的反諷,要談論的不是主觀主義和游戲,而是有限的作品對絕對物的接近,是作品以消亡為代價的完全客觀化。”[4]105施萊格爾接受了“自我”的設定,但否定了其中的邏輯規則,而是發展成為動態的、自由的“絕對自我”。如果說費希特是從“自我”中設定了“非我”,那么施萊格爾在“自我”中否定了“非我”,為達到“自我”的絕對真實,他不容“非我”在內容上與“自我”有所背離。所以說,浪漫反諷既是費希特主觀唯心主義的特定產物,同時又在本質上區別于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
要探究黑格爾對“反諷”說持何種批判態度,首先要明確黑格爾對于費希特哲學的評價。黑格爾本人對費希特哲學并非持全面批判的態度,相反,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的建立便是部分汲取了費希特“自我”理論的營養。費希特不滿康德在超驗世界即物自體和經驗世界“腳踏兩只船”的二元思想,只接受康德哲學中主體性即“自我”的一面,發展成為“純粹自我”,通過“自我”設定“非我”,將“非我”看作“自我”的衍生物和自我確證的對象,納入到“自我”的管轄范圍內。“純粹自我”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大力發揚“理智直觀”,以接通先驗世界和現象世界,由此建立一個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這種理論建構的思路是黑格爾所肯定的:“費希特哲學的最大優點和重要之點,在于指出了哲學必須是從最高原則出發,從必然性推演出一切規定性的科學。其偉大之處在于指出原則的統一性,并試圖從其中把意識的整個內容一貫地、科學地發展出來,或者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構造整個世界。”[6]311這也成為黑格爾唯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雖然黑格爾對費希特哲學并非全部肯定,比如黑格爾從客觀唯心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費希特并沒有將“自我”貫徹到底,“自我”設定了“非我”,卻最終無法返回到絕對的自我意識,由此造成的“自我”與“非我”的尖銳對立是不可避免的。但費希特能夠把著眼點放到絕對自我的一元論高度,是對康德哲學的一種批判性繼承。而黑格爾之所以對建構在“自我”理論基礎上的“反諷”說進行激烈批判,是基于施萊格爾等批評家對這個理論的消極延伸和發展,由此產生的理論成果幾乎與黑格爾的藝術哲學理論背道而馳。
黑格爾在《美學》中提到:“從一方面看,每個特性,每個屬性,每個內容在這種‘自我’里都被否定了,因為一切積極的內容都淹沒到這種抽象的自由和統一里而被消滅了;從另一方面看,每個對于‘自我’有意義的內容都只有通過‘自我’才得到它的地位和承認……一切東西都只能看作由‘自我’的主觀性的產品了。”[7]80黑格爾認為,施萊格爾全盤接受了費希特的“絕對自我”,并對它進行了極端演繹,由此導致主體的絕對權威,“自我”的獨裁使其可以在藝術創作領域橫行霸道,任意擺布、生發、消滅客觀存在,這完全是對費希特哲學片面且消極的歪曲,違背了費希特哲學的精神實質。費希特視“自我”為最高原則,但從未否定過由此衍生出來的客觀世界,而施萊格爾則拒絕承認自我意識之外的客觀現實。換句話說,施萊格爾的出發點是通過絕對自我的建立發現并統攝真理性的存在,但他最終陷入絕對自我的怪圈,否定掉意識之外的現實,沒有獲得他所希求的真理。黑格爾由此看到,盡管施萊格爾借用了費希特的“自我”理論,卻應用在其他的道路上,以致其“反諷”出現了巨大的空洞。
黑格爾對浪漫反諷說理論來源的批判,集中在“主觀性”之上,一方面指出了“反諷”說過于強調主體意識的問題,一方面在論述“反諷”說的目的論上面出現偏差,其評價帶有很強的主觀性。
二、對“反諷”藝術形式的批判
在完成對施萊格爾“反諷”說目的論的批判之后,黑格爾的批判便延伸到“反諷”的藝術表現形式,因為反諷主要體現于藝術形式中,是“邏輯事物范圍里的美”。施萊格爾曾在《批評斷片集》中對以往古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詩歌藝術大加鞭撻:“一切古典詩的體裁,在其嚴格的純粹性上,在當今都是可笑的……嚴格說來,科學的詩的概念,就像詩的科學的概念一樣是荒唐的。”[8]51這與當時德國浪漫主義所提倡的詩歌本體論有密切關系。在荷爾德林、謝林與黑格爾共同完成的《德意志唯心主義最早的系統綱領》一文中,浪漫派詩哲們公然將詩歌提升到本體論,也即存在論的地位:“它(詩歌)到最后會重新成為它起初所是之物——人類的導師;因為再沒有什么哲學、歷史;當其它學科和藝術門類湮滅,唯有詩歌藝術將存留。”[8]17詩歌成為人們精神的家園,成為人們存在的依據,這種“藝術絕對論”固然是具有人文關懷的意蘊在內,但這種言論在當時是超前的,頗具先鋒性質,招致了無數批判之聲,以致在百年之后的20世紀,才有遙遙相應者。
對古典主義的不屑一顧,意味著浪漫主義必須開辟另外一處與此截然不同的天地。施萊格爾對此早有準備,那便是通過“反諷”將古典主義的法度盡數拋棄。“(浪漫主義的)首要法則是……詩人的任意性不能容忍任何法則。”[4]101“每一首好的詩里,一切都必須是意圖,一切又都必須是直覺。這樣,詩才成為理想的。”[8]46施萊格爾推崇直覺主義的表現方法,提倡抒情詩應該完全的個性化、自由和真實,由此,施萊格爾認為應該將一切“詩和散文、天賦和批評、藝術詩和自然詩時而混合在一起,時而融合起來”,將詩化的自我向外投射,形成一個詩化的世界:“詩的哲學通常始于美的自主性,始于這樣一個定理:美有別于也應該有別于善和真,與真和善有同等權力。”[8]95美不被看作是匍匐在真和善腳下的事物,美成為詩的哲學。但黑格爾對浪漫派的這種“一切為詩而生”的藝術理念頗不以為然。依據施萊格爾的這種思想,黑格爾認為“反諷”說將導致作家創作的作品沒有任何嚴肅性,具有“反諷”基調的作品特別喜歡運用惡劣的題材,或者將道德、法律、宗教等具有真理性的東西在創作中進行平板化、諷刺化,將其中高尚的部分抽離,這種真理性的東西在“反諷”中將完全失去其神圣的地位,而淪為表現美的工具。“在通過個別人物、性格和行動來顯示這種品質之中,這種品質就否定了并毀滅了自己,因此這種滑稽對它自己也采取了滑稽態度”[7]84。而且黑格爾通過比較浪漫反諷和喜劇來進一步說明反諷的非嚴肅性,在他看來,喜劇是把一條貌似可靠、實則不可靠的原則,或是一句貌似精確、實則空洞的格言表現為空洞無聊。換言之,喜劇是讓原本無意義的內容通過諷刺的方式顯現出它的無意義和空洞,而浪漫反諷則是強行抽出對象的意義,使之成為無意義。“所以滑稽(反諷)的和喜劇的在本質上的分別就在于被毀滅的那東西的內容究竟如何。”[7]84而如果把這種諷刺態度運用到藝術創作中,不外乎三種結果:形象平滑呆板,內容意義空洞無味,導致精神的空虛且不能解決實際發生的矛盾。而這種虛偽惡劣的東西是不能打動讀者的。
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藝術哲學是低于道德、法律等上層建筑的,所以他對施萊格爾將后者低俗化的處理方式感到不滿,而且,黑格爾一向認為美的東西應該富有意蘊。在《美學》中黑格爾曾引用歌德的一句話來說明這個問題:“古人的最高原則是意蘊,而成功的藝術處理的最高成就就是美。”[7]24黑格爾認為,浪漫反諷中存在的非嚴肅性和意義缺失等問題,會徹底破壞作品的意蘊。
上面提到黑格爾認為施萊格爾通過詩化的方式降低了道德、法律等社會內容的地位,造成作品“理念”的缺失,但不止于此,黑格爾認為這種方式還過分抬高了主體精神的地位,造成主體精神的膨脹。黑格爾把藝術哲學分為三種類型:象征性藝術、古典型藝術和浪漫型藝術,而只有古典型藝術是最符合美的表現方式。“內容和完全適合內容的形式達到獨立完整的統一,因而形成一種自由的整體,這就是藝術的中心……向古典型藝術提供內容和形式的是理想,古典型藝術用恰當的表現方式實現了按照藝術概念的真正的藝術。”[7]157而在浪漫型藝術中,精神力求達到與自身絕對的同一性,相對于精神,外在世界只是一個偶然性的世界。“絕對須跳出這偶然性的世界而把自己集中到精神的內在方面去……外在方面就變成一種可有可無的因素,精神對它就毫不信任,也不把它當作自己的棲身之所了。”[7]285如此,內容和形式就無法像古典型藝術一樣達到完美的統一,無限上升的精神由于過度的抽象化而無法納入適當的表現形式中,這也是黑格爾所詬病的地方。而“浪漫反諷”就被歸入到“浪漫型藝術”當中。黑格爾在《美學》第二卷“浪漫型藝術”的“騎士風”部分中談到施萊格爾的作品《阿拉柯斯》,認為這部作品是用“可鄙的情緒和惡劣的觀念在冒充崇高無限的東西”[7]324,即用主體方面的低于最高理念的意識來充當理念,這就決定了浪漫藝術無法達到古典藝術的高度。這是黑格爾對“反諷”藝術形式批判的兩大方面。
三、對“反諷”理論內涵的批判
仍然是從費希特的“絕對自我”出發,施萊格爾認為:“在反諷中,應當既有詼諧也有嚴肅,一切都襟懷坦蕩,一切又都偽裝得很深。……它包含并激勵著一種有限與無限無法解決的沖突、一個完整的傳達既必要又不可實現的感覺。它是所有許可證最自由的一張,因為借助反諷,人們便自己超越自己;它還是最合法的一張,因為它是無論如何必不可少的。”[8]56解決有限與無限地沖突與隔膜,勢必要在兩者之中引入一個通道,使有限向無限自由生成,這個通道便是主體的超越性,主體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反過來對客體事物橫加干涉,這種超越性被施萊格爾發展到極致,便出現了黑格爾所擔心的自我精神的空乏以及客體價值的湮滅。黑格爾在《美學》中對主體這種玩世不恭、目下無塵的態度提出質疑:“一切事物都只是一種無實體的創造品,而自知不受一切事物拘束的創造者卻不受這創造品的約束,因為他能創造它,也能消滅它……對自在自為的普遍事物的關系,都看成虛幻的,他對這一切都抱著滑稽的態度。”[7]82并認為這種態度對藝術創作是極為不利的,它一方面消除了客體的價值,甚至那些神圣的具有真實意蘊的東西,也被毫不留情地拋棄了;另一方面,主體精神得不到實質性內容的支撐,便會如空中樓閣一般處于尷尬的境地,“感到一種渴望,想要找到一些堅實的,明確的,有實體性的旨趣”[7]83。這種因客體價值的缺失而導致的矛盾狀態,會使主體患上一種“精神上的饑渴病”。在黑格爾看來,僅僅從主體的絕對精神出發,是無法找到真理所在的,極致的純粹只會導致極致的空虛,而真理恰恰是包含有真實意蘊在內的客觀實體。黑格爾認為,反其道而行之,注定了浪漫反諷是不可行的,而這種理論也毫無可能付諸實踐。黑格爾對此的評價已經滲透了他自己的美學觀念,即“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但黑格爾同樣認為“美”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個矛盾統一的永恒的辯證運動過程:原本圓融一致的理念通過否定自身,達到自己的對立面,心靈雖然自分化和自否定了,卻同時把它的這種分化和否定作為由它自己所設立的東西“取消”了,它不是在這種分化和否定中碰到界限和局限,而是自己和自己的另一體在自由的普遍性里融合在一起。這種“矛盾沖突”實際上是二次否定的過程。而浪漫反諷所帶來的便是主體和客體的不相一致,也即處在沖突的最激烈階段,這其實是最終主客再次統一必不可少的步驟,“如果不經過空洞的主觀性階段,精神就無法達到自我認識,無法彌合任何裂縫”[9]76,不過在經過這一主體精神的迷惘階段,消除這種分裂就成了美的根本任務。浪漫反諷的存在有它的價值,按照黑格爾的理論,這反而是達到最高的理想美的必經之路。
但施萊格爾畢竟是生長在辯證法的時代,無論是他早期接觸的康德、樹立為榜樣的費希特,還是雖關系糟糕但早年有過師生之誼的青年黑格爾,都不可避免地為施萊格爾的藝術批評理論注入辯證法的啟蒙因子。但施萊格爾的辯證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反諷”的辯證特征主要體現在運動的化學屬性中,施萊格爾將“反諷”的運動性定義為“化學的”。所謂“化學的”,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或是機械的,而是生生不息的,內在蘊含無窮變化及矛盾的不斷轉化的運動。“矛盾”的概念,同樣可以運用于施萊格爾的理論中,但他否認黑格爾對于正反命題的綜合,認為通過“合題”來消除矛盾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這種矛盾始終沒有在主客統一中得到解決:“這種能達到反諷的‘完整性’,不是在對立面綜合意義上的絕對完整性,而是在對立的力量相互作用周而復始意義上的‘完整性’。”[9]84這種完整性始終處在無限地運動中,而這運動只能是主體精神的運動,而不是追求普遍性和綜合的運動。
浪漫反諷說不乏辯證因素,但它的辯證性并不徹底,落實到主體之后,施萊格爾的“反諷”說就此止步,再無向前的意愿,也即沒有達到主客統一的程度,這是不成熟的辯證法。黑格爾認為施萊格爾想通過反諷一步到位,創造出具有理想美和真理性的藝術作品,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黑格爾對“反諷”說理論內涵上的批判,主要是針對其片面性和未完成性。
四、結語
德國早期浪漫派面對現代文明對人性的沖擊,提出人向自然和自我心靈的復歸,是符合時代要求的。而“反諷”理論正是這種自由精神的體現,它反對自然科學對人的精神壓迫,高揚人的主體精神,通過建立“詩歌本體論”,追求詩化的人生境界,使人們能夠在現實世界中“詩意的棲居”。但“反諷”說始終沒有一個完整的、自洽的哲學體系作為支撐,導致其缺乏辯證性和客觀性,它的提出者施萊格爾的思想也是零零散散見諸于“斷片”的形式。這在建立了結構完整、體系宏大的藝術哲學的黑格爾看來,不免帶有片面性和極端性。而黑格爾也通過對“反諷”說的批判,進一步確立了以客觀唯心主義為內核的美學理論。
但施萊格爾倡導“反諷”的初衷是為把“詩”(文學)提升到哲學的位置,為此他以哲學為武裝,換言之,哲學僅是是他實現本體詩論的工具,而非其主觀目的。所以他只是選取德國古典哲學中適用于其理論的言論和觀點,而并非意圖建構一個詩的哲學體系。他在《哲學斷片集》和《雅典娜神殿》中反復將“詩”和“哲學”并舉,就是此意。但黑格爾恰恰抓住這一點,認為施萊格爾缺乏對理性、對哲學的敬畏,“詩”之所以能夠和“哲學”匯合,是施萊格爾對哲學以及道德、宗教等上層建筑進行褻瀆的緣故。從客觀的表現方式來說確實如此,但黑格爾又曲解了施萊格爾的意圖,因為施萊格爾對于改造社會道德等內容興趣不大,他關注的只有詩,或者說哲學的詩化,在他看來一切社會的都可以化作自然的、藝術的。所以,黑格爾對于“反諷”說的批判在主觀的針對性方面出現了偏差。基爾凱郭爾在《反諷的概念》一書中提到,其實黑格爾也不懂什么叫“反諷”,說他在批評“反諷”時,說法總是千篇一律,而且比較空泛。這大概是黑格爾沒有掌握“反諷”的核心內蘊,以及始終高度自信地從自己的學說體系內部入手來探討體系外部理論的緣故,從而導致一定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