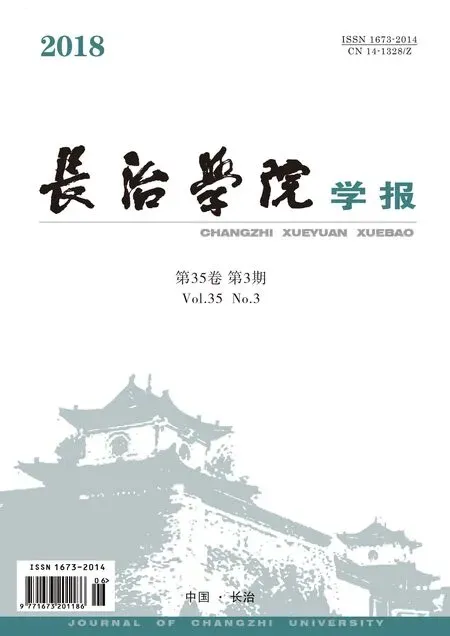自譯文學作品及其對文化外譯的啟示
趙韶麗
(長治醫學院,外語教學部,山西 長治 046000)
一、自譯研究背景
自譯(self-translation或 auto-translation)現象有著悠久的歷史,既可以指翻譯自己作品的行為,也可以指該行為產生的結果即自譯文本。20世紀之后,在西方國家,出現了產生自譯的各種客觀條件[1]。60年代,自譯研究在西方初露頭角。然而,自譯,作為一種翻譯現象到近30年才引起了學術關注。Grutman指出就大多數翻譯研究者而言,自譯更近似于一種雙語語言現象[2]。《翻譯研究詞典》中首次出現并將其定義為“經由作者本人將原作品變成另一種語言的翻譯”;科勒對自譯與“真正”的翻譯進行了比較,指出作者兼譯者會覺得是有理由對文本進行改動,而通常情況下的譯者或許不愿這么做[3]。自譯,作為翻譯的一種特殊現象,仍舊歸屬于雙語寫作的一種語言現象,但出于自譯者的雙重身份,這一特點使得翻譯者踟躕猶豫,但自譯者卻“會覺得有充分理由對目標語文本進行‘大膽’變更”[4];Faiq之所以將自譯者喻為“獨裁者”也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讓人“難以接受的自由”[5]。然而懷特提出了與之相反的觀點。他指出與翻譯者相比,自譯者沒有具備特別的“權威”。[6]Fitch在分析貝克特自譯作品之后,認為自譯與“翻譯”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為復制原文本,前者則是重復原文本的寫作過程[7]。也就是說,翻譯過程中,他譯文本必然涉及譯者的主觀介入,如此一來,翻譯的目標只能是追求與源語文本最大程度的相似;而自譯者的翻譯過程更貼合對源語文本寫作過程的重復。國內學者趙彥春認為自譯與翻譯無區別,由于翻譯本身不能排除差異或差錯,故同一內容的兩種語言的不同版本也就意味著翻譯[8]。陳吉榮認為,自譯作品與原文本之間構成復雜的互文關系,回旋著也在衍生著,忠實的同時也相互交錯著偏離。在文本和闡釋之間,自譯沒有被語言差異割裂[9]。
盡管,對于自譯現象的探討仍有很多局限,各家之言聚訟紛爭。而越來越多的作者具備雙語甚至多種語言的能力,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既可以是原作者,也具備了譯者潛質。文學作品自譯及其對文化外譯的啟示意義就有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二、自譯之得失
Gregory Rabassa曾說,能夠駕馭一種文字以上的作家如納波可夫和貝克特通常寧愿由別人英譯自己作品。而Philip E.Lewis說,“一個原作者把自己的文章譯成另一種文字時,可以隨心所欲、天馬行空。翻譯別人的作品,可就不能那么自由了。”[10]兩位學者一個否定了作家自譯,一個則因原作者自譯具有的高度自由而贊揚自譯。自譯在文學作品外譯中究竟存在怎樣的得失?
(一)字字對應:是水土不服還是消化不良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帶點凄涼。
Shanghai thirty years ago on a moonlit night......maybe we did not get to see the moon of thirty years ago.To young people the moon of thirty years ago should be a reddish-yellow wet stain the size of a copper coin,like a teardrop on letter paper by Toyun Hsuan,worn and blurred.In old people's memory the moon of thirty years ago was gay,larger,rounder,and whiter than the moon now.But seen after thirty years on a rough road,the best of moons is apt to be tinged with sadness.
例子出自張愛玲自譯的《金鎖記》(The Golden Cangue)。這樣的句子在該文本中比比皆是。她在翻譯中,使用最多的是字字對應的直譯,甚至沒有改動語序,此外有些地方還附加了英文注釋予以進一步說明。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Karen Mitchell談到此書的英譯時說張愛玲的英文不錯,只是故事中人對白,聽來有點不自然。那么這樣的譯作是應當歸結于譯者對二語的水土不服還是消化不良呢?倘若文中只是偶爾幾處,或許可將之歸咎于此。此處筆者認同陳吉榮的觀點,這是一種作者本位論的寫照[11]。從文本的角度來看,作者兼譯者張愛玲有著堅定不移的文化本位,即中華文化;從主體的角度來看,譯者的主體參與意識與創作意識對等;而作為女性,張愛玲始終堅持堅定的女性主義立場,這共同構成了張愛玲自譯作品的風格。其次,盡管她本人英文有很深的功底,她在翻譯中拒絕采用英美俚語習語,對文中的具有傳統中華文化特色的詞匯以及傳統小說的表現手法等,譯者近乎完全照搬至譯文文本中。采用這樣的譯法,其目的顯而易見,將中國文化換一種語言,僅限于語言的改變,原原本本的呈現給國外的讀者。這樣的譯法,是譯者有意為之,盡管張愛玲同時擔當作者和譯者,但是在其自譯作品中卻采取了歸隱的態度,因其大量使用直譯譯法,使譯者身份予以放大。
因此,在自譯中,譯者或許失去了順暢的二語表達,華麗的詞藻,但是收獲的是讀者面對文化差異的驚奇。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活動,也就達到了其目的。
(二)大篇幅省略:是譯者的自由不羈還是讀者接受空缺
《洋人看京劇及其它》
用洋人看京劇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味的事。頭上搭了竹竿,晾著小孩的開襠褲;柜臺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機里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無線電里賣著癩疥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
其英文版:Still Alive
Never before has the hardened city of Shanghai been moved so much by a play as by"Autumn Quince"("Chiu Hai Tang",《秋海棠》),a sentimental melodrama which has been running at the Carlton Theater since December 1942.
對比《洋人看京劇及其它》的中英文本,不但題目有異,內容上也大有出入。為什么要把自己的嘔心之作變得“面目全非”?張愛玲在寫作和翻譯時,思考方式也會因語言不同而隨之切換,因而至此。比如,用中文給中國讀者描述一些隱喻和典故,一點就明。但一旦受眾變成國外讀者,因為文化差異使然,他們并不能全然理解甚至無法理解其中意蘊。因而,在自譯過程中譯者與他譯者無異,都需考慮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能力。
英文文本中不遺余力的“贅述”,在中文中卻惜墨如金的例子,如《秧歌》中英文文本中對“鬧房”的進行了大篇幅細節性描述,以彌補讀者文化空缺,而其譯文卻只一句話:吃完了喜酒,照例鬧房。
可見,對于自譯文本中的大篇幅刪除省略,并不是自譯者的“特權”,翻譯在遇到自譯時也并沒有給譯者解除“枷鎖”,摘掉“鐐銬”。省略與否的決定權不是來自是作者的自譯者,而是預計讀者的接受能力。因此,在中國文學外譯的過程中,無論自譯還是他譯,首要考慮的都應當是目標語社會對其文化的接受環境以及目標語讀者的閱讀期待。
(三)當自譯遇上他譯
原文:(余光中)
雙人床
讓戰爭在雙人床外進行
躺在你長長的斜坡上
聽流彈,像一把呼嘯的螢火
在你的,我的頭頂竄過
竄過我的胡須和你的頭發
讓政變和革命在四周吶喊
至少愛情在我們的一邊
譯文1:(葉威廉譯)
Double Bed
Let war go on beyond the double bed,
Lying upon your long,long slope,
We listen to stray bullets,like roaming fireflies
Whiz over your head,my head,
Whiz over my moustache and your hair
Let coups d'etat,revolutions howl around us;
At least love is on our side...
譯文2:(余光中自譯)
The Double Bed
Let war rage on beyond the double bed
As I lie on the length of your slope
And hear the straying bullets,
Like a swarm of whistling will-o'-the-wisps
Whisk over your head and mine
And through your hair and through my beard.
On all sides let revolutions growl,
Love is at least on our side...
對比兩個文本,發現葉威廉的譯文更為中規中矩。比如,將第一句中“進行”譯作go on, 而自譯文本中,則更加自由。余光中既是原詩作者,也是譯者,在其譯文中可以讀到更多天馬行空。而葉威廉作為一個他譯者,則更為一板一眼。在處理“呼嘯的螢火”時,葉威廉采用了直譯, 余光中自己則似乎“不理會”原文,將螢火化為磷火,更彰顯戰場上的烽火漫天,但是由于意象的改變,缺了“螢火”帶有的浪漫意味。另外,從“胡須”的譯法,也可以看出自譯者與他譯者與文本之間的關系。葉威廉譯文中使用了moustache,該詞是胡須的全稱,是一個上義詞;余光中自譯中則使用了下義詞beard,更為具體和確切。這一點可以歸結于自譯與生俱來的優勢。倘若此時有讀者認為,身兼二者的自譯者余光中“欺負”了葉威廉,不妨再看看葉威廉在其自譯中的表現:
北風,我還能忍受這一年嗎?
冷街上,墻上,煩擾搖窗而至
帶來邊城的故事,呵氣無常的大地
草木的耐性,山巖的沉默,投下了
胡馬的長嘶
North wind,can I bear this one more year?
Street shivering along the walls
Romances in cold sorrows the frontiers
Remind me of these:
Patience of the mountains Erratic breath of outlands
Chronic neighing of Tartar horses...
從其譯文中也可以見到,自譯者的“優越”。然而,我們并不能因為自譯具有某些固有優勢,就認為,自譯優于他譯。自譯也好,他譯也罷,只是視角不同,因為既使是作者此時也是二度閱讀的讀者。此時,無論是自譯者還是他譯者都不可能踏進“同一條河流”。
三、啟示
究竟自譯是不是翻譯?這是困惑翻譯研究者的一個問題,甚至自譯者有時也會捫心自問。倘若譯者苦苦以求的是讓讀者通過自己對原作的“一斑”得以品味其伶仃魅力。那么設想,倘若譯者不僅僅是譯者,也是原作者,那么這樣的流失是不是就會減少一些。而他譯者以其譯者的專業角度,與之結合,翻譯會不會就是能夠滿足讀者閱讀期待的翻譯?然而,自譯“是不是”翻譯這樣的本體論問題已經不那么重要。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國文學正在逐步走出一度被邊緣化的桎梏。先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有劉慈欣獲得雨果獎,曹文軒又斬獲國際安徒生獎。這些榮譽并非一蹴而就,是我國文學事業長期發展沉淀積累使然,也從另一方面顯現出世界文學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真正顯示出了世界意義。然而我國文學的“走出去”并不能止步于此,作為世界文學的一個分支,如何在今后的文化交流中發出中國聲音,使中國文學真正走進外國讀者閱讀范圍?翻譯研究領域應時而新,出現了文化轉向。文化翻譯觀的觀點認為,文化翻譯過程中,譯者只是在原作被消解成的碎片中提取最為接近原作的成分進而進行重組整合,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東西,即“一個既接近原作又對之有所叛逆的‘第三者’”。[12]然而,自譯中由于譯者的特殊角色,總能挖掘到其他譯者難以挖掘之處。正如榮格所述自譯者能直接地獲得源語文本的寫作意圖,而在自譯過程中,源語言和目標語言所歸屬的兩種不同的文化語境會制約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自譯者具備的優勢就是他可以在解析源語文本結構之后徑直進入存儲原文寫作意圖的“記憶”。[13]換言之,自譯有著更為深廣的文本,原文本出自自譯者之手,因此必然其對原文本的理解更為深厚。他譯作品則或多或少有所局限,回歸文本回歸的是譯者作為讀者的二手文本。一般而言,人們普遍認可,譯者首先是讀者的觀點。那么在翻譯文本的過程中,他譯就遭遇了譯者的再度闡釋,從文本自身來看,或多或少的經歷了“變形記”,盡管從譯者角度來說,他們仍是“戴著枷鎖的舞者”。
綜上,自譯過程中有其與生俱來的優勢,也有先天性不足。但是在現在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自譯隨著越來越的雙語作者的出現,會成為譯界的一股力量,將自譯與他譯結合的產物,能夠更好地傳遞作品源語文本的文化內涵,從而高質量實現文化輸出,真正促進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