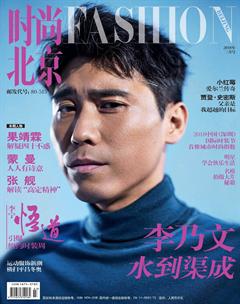金錢板 巴蜀的“討口”藝術
寒一一
乞丐,四川人又稱為游民、討口子、叫化子、要飯的。乞丐以四川方言說:我們“穿的千家衣,吃的萬家谷。蓋的肚囊皮,睡的背脊骨!”
“金錢板”屬韻誦類,半說半唱。演唱生動活潑、場地不限,一人一臺戲。最大特色就是使用的四川方言,最具巴蜀特色,更顯得生動、幽默、活潑、朗朗上口……方言唱詞為七字句或十字句,大多字數不限。唱詞通俗易懂、充滿四川方言中獨特的詼諧和智慧,段末一句略有拖腔。曲調隨語言及情緒而變化,但仍須在一定腔調上。否則就會怪聲怪氣“黃腔走調”。
金錢板演員上臺,先打鬧臺以吸引觀眾。演唱中,配合情節的需要竹片子有不同打法,如有平板(不快不慢)、快板(急打急唱)、慢板(慢打慢唱)……既可說長篇大書,也可短說民間故事、社會新聞。
與在中國北方流行的快板不同,瘦瘦長長的金錢板寬3.3厘米、長30厘米,三塊板子之間沒有用綢帶綁住,完全靠手指控制每塊竹板的活動。在表演時,表演者右手拿著竹板內嵌有銅錢的上板和下板,左手持沒有嵌著銅錢的一塊打板。三塊竹板一旦碰撞在一起,好戲就上演了。
在數百年的發展歷程中,“金錢板”的道具發生過幾次大的變化。最初使用由兩塊金屬板構成的“玉子板”,后改為由四塊串在一起的竹板和一塊橫插攔板構成的“連花板”,再后來發展為由兩塊竹板和一塊鋸齒狀竹板構成的“刮子板”。其間還有形似短劍的“金劍板”、形似朝笏的“金簽板”、代表天地人三才的“三才板”。為了增加金錢板的聲音效果,藝人們又把銅錢或金屬片嵌入竹板中,打擊和演唱時,既發出竹板聲又有隱隱約約的金屬聲,因此民間習稱這種說唱形式叫“金錢板”。金錢板大師鄒忠新所使用的三塊竹板,就是由兩塊平滑的竹板和一塊鋸齒狀竹板構成的“刮子板”。
四川金錢板在唱腔上充分汲取川劇高腔的部分曲牌和四川民歌、山歌、號子乃至昆曲、胡琴、燈戲、彈戲的優點,集眾家之長于一身,因此成為四川觀眾最喜愛的本土民間曲藝品種之一。
金錢板的流派又有“花派”、“雜派”和“清派”之分。花派講究板式的打法,要打得熱鬧,打得嫻熟,且打且耍,眉眼身法要靈活自如;雜派主要是講究唱詞,要求藝人對唱詞的長短運用自如,不受節奏的拘束和控制,唱一段說一段,說中帶唱;而清派則比較講究咬文嚼字,要求演員吐字時字正腔圓、細膩準確,行腔中不能出現“啦”、“哈”、“呀”等虛字尾音。
金錢板的唱詞又分為長篇唱段和短小的“書帽”兩種,像著名傳統唱段中的《武松》、《岳飛傳》、《乾隆下江南》等就屬長篇唱段,大多從歷史故事和章回小說改編而來。書帽則是短小精悍的唱段,常用于演出開場或結束時,起到畫龍點睛、出奇制勝的作用。著名書帽有《秀才過溝》、《疑人偷雞》、《小菜打仗》等。
說到金錢板,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鄒忠新。已經流傳了300多年的金錢板,在鄒忠新的手里打出了花樣,打出了名堂。
鄒忠新說:“金錢板在表演時,往往以說唱故事為主,因此它的唱詞需要極富敘事元素,詞中既有人物,又有情節,還有故事高潮,曲折生動,繪聲繪色,引人入勝。而在表演上,它要求表演者將打板、表演和唱功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目的是通過表演者對題材的理解和藝術加工,用或高亢激昂、或婉轉低徊的說唱方式,把故事形神兼備地傳達給觀眾,從而帶給觀眾強烈的藝術感染。”
鄒忠新吸收各派之長,終自成一派,被譽為金錢板“打、唱、演”三絕。竹板打得鏗鏗鏘鏘穿金裂石、唱腔行云流水……他鏗鏘演唱自己的身世的一段金錢板,充滿四川方言的“川味”魅力:“世居安岳龍臺鎮,自幼隨父逃災荒。乞討灌城把生父養,不幸半年苦逼亡。眼看孤兒無希望,來了新都小貨郎。恩父把我來收養,相依為命度時光。父子飄泊雙流縣,偶遇恩師收歌郎(歌郎即賣唱的叫花子)……從此三塊金錢板,嘀嘀噠噠走四方。饑寒交迫盼黎明,忍辱懷恨窮途長……紅旗漫卷烏云散,藝人翻身把家當……”
鄒忠新把原來在鄉場鬧市路口的金錢板帶進了茶館,成為茶客們品評的一門表演藝術。他更是心系這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在重病之際依然口傳唱段,生怕這門藝術在時代的洪流下被淹沒。
鄒忠新說,想當年推翻清王朝時,《殺趙爾豐》、《歌頌同志會》等段子為辛亥革命推波助瀾;抗日戰爭中,《不忘國恥》、《好男要當兵》等,讓多少四川人熱血沸騰……
三十年前,以四川方言為主的四川曲藝,曾有黃金歲月。總府街有實驗書場、鼓樓北街有芙蓉亭書場、東郊有如飛書場、人民商場有成都市曲藝場……電臺也天天播放這類節目:曾炳昆的相書、賈瞎子的竹琴、李月秋的清音、涂紹全的揚琴,還有鄒忠新,他的金錢板。
可如今,金錢板等曲藝的風光歲月,很快煙消云散。現在成都地區還常打金錢板演出的藝人,屈指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