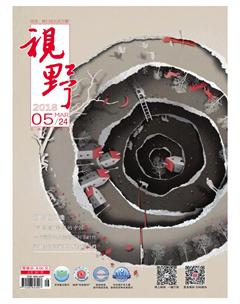恐懼與悲憫的進化
白先勇
大學求學期間,恐怕是一個人一生中對人生意義的探求,對精神生活的向往最強盛的時期。如果這期間有幸讀到一本好書,這本書可能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心路歷程。
我念大學的時候,在研讀過的西洋文學書籍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本小說給了我最大的沖擊與啟示。
我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的雪夜,我在宿舍里看完這本書,已是天明,從窗外望出去,只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陣奇異的感動。
我不是基督徒,也沒有其他任何宗教信仰,但那一刻我的確相信宇宙間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正在默默地垂憐著世上的蕓蕓眾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部驚心動魄的曠世杰作,激發了我那片刻幾近神秘的宗教情感,猛然間我好像聽到了悠悠一聲從中古教堂傳出來的格里歷圣歌,不禁一陣憫然。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扛鼎之作,享譽之高,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齊名,是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一雙瑰寶。陀氏與托翁同時代,處于俄國十九世紀新舊交替大變前夕,他在政治上、心理上、精神上屢遭困厄。年輕時,曾因參加激進黨政治活動被捕下監,險遭槍斃,放逐西伯利亞十年,恢復自由后,他反過來猛烈抨擊左翼虛無分子。陀氏相信只有希臘正教才可拯救俄羅斯民族,而左翼分子只能將俄國拖向萬劫不復。他一生執著于研討人與上帝的關系,經常擺蕩于天堂與地獄之間,穿梭于神性與魔性的兩極,直到他年屆六十,終于寫下《卡拉馬佐夫兄弟》,在人類精神領域中樹立了一座高峰。
這本小說是敘述卡拉馬佐夫一家四個同父異母兄弟的故事。四兄弟分別代表了情、理、圣、魔人性中的四種可能,四個手足相生相克,顯示了人性中生而俱來無法消弭的基本沖突。
陀氏在這本小說中說道:“這是一場上帝與魔鬼的戰爭,戰場就在人的心中。”陀氏是研究人類心靈中善惡沖突最深刻的小說家。在這部書中,陀氏對于人類善與惡的檢視,已經提高到了宗教的層面,他在另一本小說《罪與罰》中寫道:“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確,如果沒有代表道德力量的上帝存在,那么弒父也隨時可以發生。“弒父”這項最違反人倫的罪惡便是這本小說的主題。
西方文學從古希臘索福克利斯的悲劇《伊底帕斯王》到陀氏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許多杰作都在挖掘這個令人不寒而栗的人倫禁忌,證諸弗洛伊德學派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我們不能不凜然于人心惟危。在重重宗教、倫理、道德的壓束之下,人類那股最原始的嗜血亂倫的沖動仍舊蠢蠢伺機而發。西方文學的深刻處在于敢正視人類的罪惡,因而追根究底,鍥而不舍。看了《卡拉馬佐夫兄弟》,“恐懼與悲憫”不禁油然而生。
恐懼,因為我們看到人竟是如此的不完美,我們于是變得謙卑,因而興起相濡以沫的同情。文學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喚起人類常常處于休眠狀態中的惻隱之心吧。
(楚江南摘自《文苑·經典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