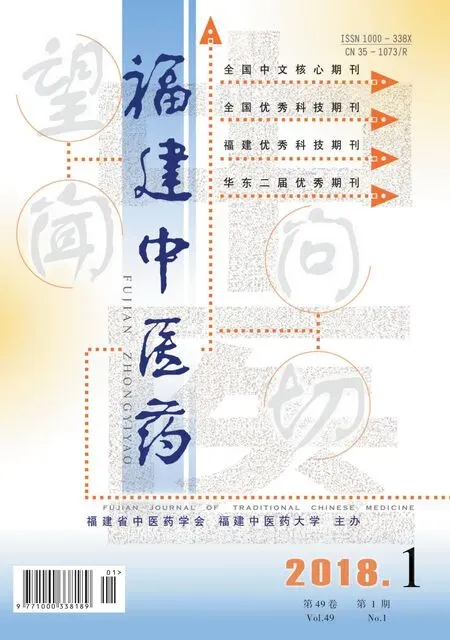張錫純論治瘡瘍病特色淺議
張云杰
(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東 濟南 250011)
張錫純,近代中西醫匯通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深研醫理,精于藥證,見解獨樹一幟,集畢生心血,著成《醫學衷中參西錄》。書中對瘡瘍病的論治較傳統多有創新,極具特色,頗能啟迪后學。
1 瘡瘍重癥,立論火毒,倡清透、清下之法,善用重劑
瘡瘍是各種致病因素侵襲人體后引起的體表化膿性疾病,是中醫外科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如癰、疽、癤、疔、流注、流痰、瘰疬、無頭疽、無名腫毒等。瘡瘍,特別是急性發生的,病機以“熱毒”“火毒”最為常見,《醫宗金鑒》概括為“癰疽原是火毒生”。走黃則是瘡瘍重癥,是因疔瘡火毒熾盛,早期失治,毒勢未能及時控制,或因擠壓等,使毒邪走散入血,內攻臟腑而引起的一種全身性危急疾病,火毒熾盛是發生走黃的關鍵之所在。
張錫純深究醫理,認為陽證瘡瘍:“撫之硬而且熱,色甚紅,純是一團火毒之氣”;而重癥瘡瘍則是“毒熱熾盛,盤踞陽明之府,若火之燎原”。因此,對于本證的治療張氏力主清透,一則宣散在外之邪,二則清解在里之熱。并創制清解湯、清盂湯等有效方劑,其具體用藥特點體現在對石膏、連翹、薄荷等藥物的配伍應用上。
張錫純對石膏的應用可謂出神入化,他認為石膏味辛性寒,質重氣浮,解肌膚邪熱,清氣分之實熱,實為“清陽明胃腑實熱之圣藥”。石膏的特點是清而能透,涼而不遏,既能使郁熱從里而清,又能透達肌表從外而解。
連翹具有清熱解毒、消腫散結之功,善治“鼠瘺,瘰疬,癰腫,惡瘡,癭瘤,結熱,蠱毒”。張氏認為“連翹,味淡微苦,性涼,具升浮宣散之力,流通氣血。治十二經血凝氣聚,為瘡家要藥。能透表解肌,清熱逐風,又為治風熱要藥”。張錫純用連翹,“欲其輕清之性,善走經絡,以解陽明在經之熱也。連翹“應秋金之令……能清肝家留滯之邪毒也”。所以,連翹既能清又能托,重在托毒外出。
薄荷,透發之力更強,《本草綱目》云:“薄荷入手太陰、足厥陰,辛能發散,涼能清利,專于消風散熱,故頭痛頭風,眼目、咽喉、口齒諸病,小兒驚熱及瘰疬、癘疥為要藥”。張錫純認為:“薄荷,味辛,氣清郁香竄,性平,少用則涼,多用則熱。其力能內透筋骨,外達肌表,宣通臟腑,貫穿經絡”。用薄荷關鍵在于其“涼宣”之功能,既能涼使熱而清解,又能宣使熱而透出。
石膏配連翹或者薄荷,意均取清熱之藥配以宣透之品,達到既解又清,清透、清宣并舉,內清外宣的功能,這樣可以使內外道路暢達,腠理疏通,熱毒、火毒可自里消解,自外透出。
瘡瘍中以疔毒為最緊要,被稱為瘡中之王,病情較為險峻,因其毒發于臟腑,非僅在于經絡,對此類疾病則必須采用清下之法,張氏特制定大黃掃毒湯,方中重用大黃以解毒清血,他認為大黃“善解瘡瘍熱毒,以治疔毒尤為特效之藥”“疔毒甚劇,他藥不效者,當重用大黃以通其大便自愈。可用之兩許或者更多”。其重用大黃,目的有二:大黃善清解熱邪,使毒邪從內而化;大黃善攻下而通大便,使毒邪隨便而出。
峻藥重用,這也是張氏治療瘡瘍重癥的特點之一,生石膏治療瘡毒實熱或實熱熾盛證時多重用,少則三兩,多則五六兩,甚則七八兩。但卻不是一味的蠻用、濫用,在長期的臨證過程中,張氏總結出石膏的禁忌主要是一個“瀉”字,其曰“至石膏之分量,亦宜因證加減,若大便不實者宜少用,若瀉者石膏可不用,待其瀉止便實仍有余熱者,石膏仍可再用”。對于煎服方法,也據情而變,石膏“必煎湯三、四匙,分四、五次徐徐溫飲下,熱退不必盡劑”,于無節制之中善用節制;在治療熱重證時,畏石膏量大而墜如下焦,不可頓服,而采用“連續服藥法”;研末服石膏,其用量更有明訓:“石膏末服,一錢之力,可抵串兩”,藥量當斟酌使用。由此可見,張氏運用石膏,并非一味重用,而是靈活處置。
大黃有將軍之稱,攻下破結,藥性峻猛,張錫純對大黃劑量之認識和應用也非同常人。其論治癲狂之實證用大黃2兩,疔毒更可以大劑治之,案載用生大黃治瘡毒以10斤水煎飲之而愈。
2 瘡瘍病中后期,顧護胃氣,大補氣血,補消結合
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胃氣的強弱與瘡瘍病的發生、發展、病理過程及轉歸預后有密切關系。瘡瘍病中后期,由于化膿潰破,大量膿液外泄,耗損氣血,或者瘡瘍日久不愈,此時的病機多為氣血虧虛,脾胃不健。張氏力主此時應顧護胃氣,大補氣血,輔以化腐生肌,補消并舉。蓋瘡瘍之作,由胃氣不調,瘡瘍之潰,由胃氣腐化,瘡瘍之斂,由胃氣榮養。張氏說:“夫人之后天,賴水谷以生氣血,賴氣血以生肌肉,此自然之理也”。胃氣強壯,瘡瘍氣血凝結者自散,膿已成者自潰,肌肉欲死者自生,肌肉已死者自腐、死肉已潰者自斂。治療瘡瘍,當助胃壯氣,使根本堅固,并創立內托生肌散(生黃芪、丹參、乳香、沒藥等)一方。在藥物選擇上,補氣養血首推黃芪,張氏盛贊“其補氣之功最優,故推為補藥之長,”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一書中大凡益氣養血活血之方必用。方中重用黃芪峻補氣分以生肌肉,“調其脾胃,使之多進飲食,以為生血之根本”“補正氣,即所以逐邪氣”。另外,治病服藥只有脾胃強壯,氣血生化之源充足,才能運化藥力以達病所。“必賴其人之正氣無傷,藥借正氣以運行之而后可以奏效”,扶正使“人之氣血壯旺,愈能駕馭藥力以勝病”。更配伍白芍、花粉滋陰養血,共奏益氣生血之功。
張氏用藥,注重靈動,其用黃芪,必生用者,認為黃芪生用補中而具有宣通之力,若炙之,則一于溫補,固于瘡家不宜也。
此外,方中又配以丹參、乳香、沒藥等活血生肌以開通之,使補而不滯,這充分說明張氏治療瘡瘍,不是一味濫補,而是注重氣血流通,消補兼施。
3 重視活血開瘀,將其貫穿于瘡瘍病的整個治療過程中
張氏認為,無論是瘡瘍病的早期,還是化膿和潰后期,以及一些慢性炎塊,諸如淋巴結腫大、淋巴結核、胸腹腔感染等,都有瘀血阻絡參與其中。因此,他認為瘀血阻絡是瘡瘍病發病最重要的機理,貫穿于瘡瘍病整個發病過程,這從他創立的一系列瘡瘍方劑中可以一窺端倪,在其大黃掃毒湯、消乳湯、內托生肌散、消瘰丸、活絡效靈丹、清金解毒湯、清涼華蓋飲,甚至外用藥化腐生肌散等方劑中,都配伍應用了活血開瘀之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藥物為:乳香、沒藥、三七、三棱、莪術等。
張氏采用乳香、沒藥治療瘡癰腫痛,取其解毒生肌、開瘀止痛之功。認為“乳香、沒藥同為瘡家之要藥,而消腫止痛之力,沒藥尤勝”,二藥可治“一切瘡瘍腫疼,或其瘡硬不疼”,能“解毒、消腫、生肌、止疼”。二藥又為“宣通臟腑流通經絡之要藥”“凡臟腑中,有氣血凝滯,二藥皆能流通之”,于“流通氣血之中,大具融化氣血之力”使“癰瘡可以內消”。此外,乳香、沒藥對于一切瘡瘍腫疼,亦可外用,為粉以外敷瘡瘍能解毒消腫,生肌止痛,多有奇效。
張氏在很多方劑中,都應用了具有化瘀之功的三七,他認為,“三七化瘀解毒之力最優,且化瘀而不傷新血,其解毒之力,更能佐生肌藥以速于生肌,故于痛劇者加之”。對于三七的解毒、化腐、生肌、托毒之功,前賢諸書皆未言及。張氏為三七的運用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后世采用三七研末內服、外敷,治療針眼結毒、肛癰、乳癰初起尚未化膿之證,多緣于此。
張錫純認為瘰疬之證是“肝膽之火上升,與痰涎凝結而成,初起多在少陽部位,或項側,或缺盆,久則漸入陽明部位”。在治療此病時,張錫純組方消瘰丸,在消痰軟堅藥中配伍三棱、莪術。三棱、莪術性較和平,其開瘀行氣之力“善開至堅之結”“善理肝膽之郁”,治“一切血凝氣滯之證”,更善“治瘀血,雖堅如鐵石亦能徐徐消除”。 三棱、莪術善開至堅之結,瘰疬自易消散。配伍黃芪還可以健脾強胃,脾胃健運,則痰濕自除,肝膽舒暢,相火自伏,痰火不得相交,不致凝結而形成瘰疬。這樣,可以做到標本并治。
雖然張氏善用活血開瘀之品,但卻很注意和其他藥相互配伍,取長補短。其曰“凡用藥開瘀,將藥服下必其臟腑之氣化能運行,其破藥之力始能奏效,若但知重用破藥以破瘀,恒有將其氣分破傷而瘀轉不開者,是以人之有瘀者,固忌服補氣之藥,而補氣之藥若與開破之藥同用,則補氣之藥轉能助開破之藥,俾所瘀者速消”。若“但知用破血通血之藥,往往病猶未去,而其人已先受其傷”,因此,常伍用黃芪、人參以護衛氣血,使“其補破之力皆可相敵,不但氣血不受傷損,瘀血之化亦較速”,故“消癥瘕諸藥不慮其因猛烈而傷人”。這與他一貫注重保護臟腑之氣的觀點是一致的。
張錫純治療此證,善用活血開瘀之品,卻少用理氣藥。曰“若論耗散氣血,香附猶甚于三棱、莪術,若論消磨癥瘕,十倍香附亦不及三棱、莪術也”。他強烈反對濫用理氣藥耗傷臟腑氣血的做法。“觀其臨證調方,漫不知病根于何處,惟是混開混破。恒集若香附、木香、陳皮、砂仁、枳殼、厚樸、延胡、五靈脂諸藥,或十余味或數十味為一方,服之令人臟腑之氣皆亂,常有本病可治,服此等藥數十劑而竟不治者。”
張氏治療瘡瘍,雖然立方不多,卻立法井然,用藥精煉,絲絲緊扣病之本質,為后學者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