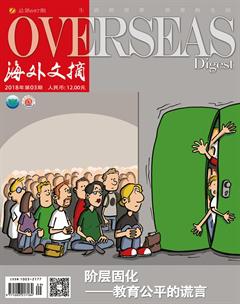信息時代易怒癥
長倉克枝 劉欣
日本美德的消失
東京的一位公司職員不禁嘆息:又有部下辭職了。導(dǎo)致部下接連辭職的是公司與大客戶的往來電子郵件,如果能面談溝通可能就不會這樣了。
到了業(yè)務(wù)繁忙期,大客戶會頻繁發(fā)來進(jìn)度確認(rèn)郵件,這些郵件是全員可讀的。每次都通過電話聯(lián)系的話很麻煩,電子郵件方便得多,但或許是因為對方也非常急躁,書面文字往往顯得粗魯而生硬:“那項目怎么樣了?”
由于看不到對方的表情,僅憑簡短的文字,似乎能感覺到客戶的指責(zé)之意。即便這些項目是客戶突然丟來的,也只能咬牙堅持做下去。他勸說年輕的項目負(fù)責(zé)人:“你就緩一緩吧。”

NTT開發(fā)的觸感電話,還能從屏幕直接看到對方的表情。
他的本意是讓部下不用那么快回復(fù)客戶,多花些時間處理,放慢節(jié)奏。可是不一會兒,他就收到了部下抄送全員的回信:“這個項目是前幾天才接的,日程方面有困難。”
他理解部下的心情。可是委托者與受委托者有時的確說不通道理。過去他也有類似的經(jīng)歷,只要在郵件中應(yīng)下要求,他立刻就會成為箭靶子,不斷收到催促郵件:“項目B進(jìn)展如何了?”“能按時完成嗎?”“報告里有錯別字。”郵件里滿是隱含責(zé)備的“當(dāng)初”“本來”等詞語。
“語言攻擊對執(zhí)行者來說是重創(chuàng)。客戶發(fā)來的郵件全員都能收到,部下會產(chǎn)生‘我丟人了的念頭。”他本人對回郵件也感到棘手,有時他直接給客戶打電話,或者去面談。他說:“如果覺得對方不講理,換成誰都會生氣。匯報郵件的語句往往很長,文字中的拉鋸很顯眼,客戶如果感到在意,事情就會向難以收拾的方向發(fā)展。”
有的領(lǐng)導(dǎo)會沖秘書怒吼“你做錯了!”有人會在網(wǎng)上公開發(fā)視頻責(zé)罵家人。謙讓和謙遜本是日本人的傳統(tǒng)美德,但現(xiàn)在似乎已成為過去式了。
失去伙伴的網(wǎng)絡(luò)時代
導(dǎo)致“易怒社會”出現(xiàn)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郵件、社交網(wǎng)站……人們交流的方式不斷進(jìn)化,與電話或面談相比,純文字溝通獲得的信息要少得多。
關(guān)西大學(xué)研究生院的社會心理學(xué)家三浦麻子說:“如果見面或電話溝通,聽見彼此的聲音,看見對方的表情,可以真切感受到對方傳達(dá)的明確信息。只憑文字交流,則需要在頭腦中重塑理解,不知不覺中就會過度解讀對方的意思。”
即便發(fā)信一方帶著感情,解讀者也可能產(chǎn)生誤解。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負(fù)面情緒越來越多。筑波大學(xué)準(zhǔn)教授、社會心理學(xué)者湯川進(jìn)太郎說:“舉個例子,遇到不開心的事,我們可以立刻將它發(fā)表在社交網(wǎng)站。如果當(dāng)事人感到憤怒,或受侵害的事情與大眾焦點吻合,就會引發(fā)大量共鳴,人類本身就傾向于給負(fù)面信息賦予更高的價值。而且因為對方不在面前,不必?fù)?dān)心會被毆打,人就更難自我控制,匿名發(fā)布信息更是如此。”
首都大學(xué)教授、社會學(xué)家宮臺真司認(rèn)為,二十幾年來社會的變化導(dǎo)致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爭執(zhí)增多。
過去,日本人的表達(dá)分為“真心話”和“場面話”。20世紀(jì)90年代,法治社會急速推進(jìn),鄰居家吵鬧也可以報警,針對陽臺抽煙現(xiàn)象也制定了相應(yīng)的細(xì)則,社會對違法者予以重?fù)簟Uf到底,鄰里也好,國民大眾也好,已經(jīng)不再是“同伴”,被害妄想向全社會蔓延。不安造成日本人容易陷入受眾人指責(zé)的局面。
宮臺真司說:“道德和法律替代了舊時代的共識,網(wǎng)上的‘引戰(zhàn)話題大多也與道德和法律相關(guān),‘鍵盤俠本人是否遵紀(jì)守法不重要,只要有人稍不遵守,他們就會群起攻之,創(chuàng)造虛擬的同伴和同盟。”
高須咨詢所的高須克彌院長曾多次在推特上遭受刷屏批評,即便如此,他的粉絲目前也超過了28萬人。他說:“對我來說,不管對方何等尊貴,都要說出當(dāng)下真實的想法,這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如果通過報紙或電視媒體發(fā)表意見,我的語言會被他人編輯整理,推特就不一樣了,這是可以即刻發(fā)信的寶貴空間。即便偶爾有混亂的爭吵,但在粉絲的指引下,我能漸漸將信息向正確的方向修整。我喜歡并享受社交網(wǎng)絡(luò)。”
不要評判他人
職業(yè)記者吉田豪說:“近十年,時代氛圍發(fā)生了改變。很多人不注意網(wǎng)絡(luò)禮儀,爭論不斷。網(wǎng)民們秉持各自的正義發(fā)生沖突,語言隨之變得強(qiáng)硬。假使站在客觀角度,還有可能分出勝負(fù),但讓當(dāng)事人認(rèn)輸或和解幾乎是不可能的。盡管如此,依然不斷有人試圖駁倒對方。即便你糾正了錯誤之處,想駁倒他人也是難以實現(xiàn)的,因為你無法改變一個成年人的思維。”
不少人把推特當(dāng)成無意識發(fā)牢騷的場所,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人性和感情好惡。吉田說: “良好使用社交網(wǎng)絡(luò)的秘訣是:第一,不要生氣;第二,使用敬語。不用敬語,別人會認(rèn)為你連最低限度的禮貌都不具備,留下不佳的印象。此外我個人的堅持是不去‘評判他人。”
一位27歲的女職員加了40多個Line聊天群,包括同事群、老同學(xué)群、家庭群等等。有事的時候如果有人不回復(fù),她會直接列出事務(wù)的期限和答案選項,并直接與似乎心懷不滿的成員進(jìn)行溝通安撫。
一位女性說,她的一個朋友曾經(jīng)以身體不適為理由推掉旅行邀約,卻轉(zhuǎn)天就在社交網(wǎng)絡(luò)發(fā)了一張去耶路撒冷的照片,感覺有點“人格分裂”。這種時候,表情包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它既可以讓氣氛輕松,又能為自己的主張增加幽默感。她說:“前幾天我和朋友約好吃飯,卻被放了鴿子。到下午對方才聯(lián)系我說:‘我記成下周了。我知道他忙得很,所以沒有真的生氣。”但她也不想平平淡淡地回復(fù)“沒關(guān)系”,于是發(fā)了一個暴怒狗熊的表情給朋友,朋友也就順勢說“對不起啦”。
使用表情其實是為對方考慮。她說:“如果真生氣了,我會不加標(biāo)點符號只發(fā)文字。‘知道了。和‘知道了給人的感覺不一樣。我的同齡人很少有人不用顏文字或標(biāo)點,如果對方發(fā)來的信息里只有字,我會懷疑他是不是生氣了。”

湯川進(jìn)太郎教授認(rèn)為:“文字適合用來說明概念,表達(dá)心情卻很難,一般的交流中人們可以通過表情、眼神、聲音推斷對方的心情,網(wǎng)上聊天時圖片反而能更好地傳達(dá)這些。”
“純文字”等于怒吼
NTT交流科學(xué)基礎(chǔ)研究所最近開發(fā)出一種“觸感電話”。當(dāng)一方按下按鈕,另一方腰部佩戴的“寬腰帶”就會隨之束緊。特別研究員渡邊淳司說:“我們在溝通交流的時候,重要的不是對方想說什么,而是對方怎么說、我們怎么回應(yīng)的‘身體反應(yīng)。僅憑文字難以完全表達(dá)人的內(nèi)心想法,所以我們嘗試做了觸感電話。”
觸感電話發(fā)揮著和表情包一樣的讓溝通更順暢的作用。渡邊說:“人是會發(fā)怒的生物。表情和音調(diào)容易傳達(dá)憤怒的征兆,而只用單薄的文字交流,更可能導(dǎo)致憤怒爆發(fā)、情緒失控。所以我們想到,能不能通過觸感讓對方了解‘我有點生氣了的情緒呢,此外也能提醒自己意識到當(dāng)前的情緒狀態(tài),適當(dāng)調(diào)整。”
麻省理工學(xué)院媒體實驗室研究員創(chuàng)建了Affectiva情感AI公司,開發(fā)出一款可識別人類情緒的APP,可通過表情分辨出悲傷、喜悅、憤怒、驚訝、恐懼、厭惡和輕蔑等7種真實的情緒。然后,軟件會將讀取的情緒用卡通表情表現(xiàn)出來。使用者用手機(jī)發(fā)信息時,APP就可以自動讀取情緒,發(fā)送示意表情,方便表達(dá)情緒。
那么情緒本身是可以被控制的嗎?人們的一般觀念是“因為快樂,所以笑”,但從心理學(xué)角度來說,身體有所反應(yīng)才能帶動情緒產(chǎn)生,也就是說事實是“先笑,才感到快樂”。利用這種機(jī)制,人或許就可以自如控制情緒。東京大學(xué)的吉田成朗助教著手開發(fā)電視會議系統(tǒng),通過處理畫面將對方表情自動轉(zhuǎn)換為笑臉。試驗表明,利用這一系統(tǒng)之后,與會者的創(chuàng)意增長至不使用狀態(tài)的1.5倍。
給人施加外部刺激改變其情緒和行為的試驗也在推廣,2014年,媒體稱臉書曾操縱68萬名用戶信息流,以進(jìn)行用戶情緒變化試驗,這一行為遭到了大眾的譴責(zé)。而實驗證明,通過過濾信息,就能對臉書用戶產(chǎn)生消極或積極的影響。
當(dāng)我們與人合作的時候,即便考慮了對方的心情,有時也會造成負(fù)面結(jié)果,無感情的機(jī)器人系統(tǒng)可以有效解決這種偏差。在美國耶魯大學(xué)攻讀博士學(xué)位的白土寬和通過實驗證明,在組合最佳色彩搭配的網(wǎng)絡(luò)游戲中,如果讓系統(tǒng)自行判定某些關(guān)卡的選擇,團(tuán)隊成績反而更高。“如果讓每位玩家選擇他認(rèn)為的最佳搭配,經(jīng)常會發(fā)生矛盾沖突,合作不佳。如果讓系統(tǒng)機(jī)器人對某些關(guān)卡做決定,雖然成員會產(chǎn)生‘這家伙為什么這么選的念頭,但最終結(jié)果并不差,全隊人都會感到滿意。”
容易過度在意情緒是人性本能,此時我們或許只能利用“不解風(fēng)情”的程序系統(tǒng)來防止情緒失控。
[譯自日本《AERA》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