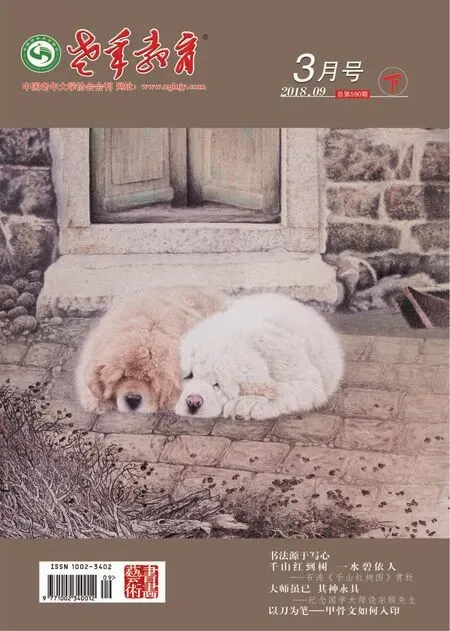清簡神逸 不墮家風
——文彭《草書滕王閣序》賞析
□ 劉 燕
中國古代詩文書畫講究家族傳承。據統計,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書畫世家是興起于明代中期的文氏家族。該家族以文征明為發端,從明代中期(約15世紀末)開始一直綿延到清代中后期(約18世紀中葉),前后歷經近三百年,在詩文書畫領域代不乏人,且被著錄的就有三十多人。文氏家族雖然才俊眾多,但是最有影響者當為文征明父子。文征明長子文彭、次子文嘉,皆善詩文書畫。如果選“雙璧”的話,無疑是文征明、文彭二人。文嘉主要在繪畫上用力,且未能跳出文征明的籠罩。文彭則在書法上有獨創之處。學書伊始,他便遵從父命,追源溯流,上學魏晉,下學唐人。明代許在《文國博墓志銘》中評價他說:“字學鐘、王,后效懷素,晚年全學孫過庭,而尤精篆隸。”縱觀文彭的各體書法,均帶有明顯的家族風范。詹景鳳在評價文彭書法時說道:“(彭)才似勝之,工力遠不及父。”或許,文彭先天氣質里就帶著一種“自我”因素,并有自知之明。其書法用力之處并不在法度工力,而是著意于性情的表達。
文彭所書《草書滕王閣序》,成熟老練,文雅從容。全篇61行,每行字數不一,共計717字。此作曾入清朝內府收藏,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這件作品明顯帶有祝允明、文征明等父輩的影子,不過也很自然地體現出文彭長期學習孫過庭的痕跡:在筆法上提按變化豐富,使轉圓轉流暢又勁健硬朗。在用鋒方面,文彭也有很大的突破。文征明作品主要使用中鋒,很少用側鋒,點畫比較細勁。但是文彭的用鋒則突破了中鋒為主而大量使用側鋒,這就使得點畫的形態變化多端。因為中鋒取凝練,能解決點畫的質感,側鋒取妍媚,能解決點畫的形態。以此作前半部分為例,許多鉤挑,尤其是向右上挑出的鉤法,如“廬()”“光”的末筆,以及大量的圓轉出鋒的處理,如“新”“興()”“而”“荊”“列”的末筆,在經過輕提筆右轉后迅速側按筆,增加點畫的厚度和輕重對比,再快速出鋒變為中鋒。還有“交”字后兩筆的側鋒轉中鋒的變化更明顯,這種筆法顯然是由孫過庭轉化而來。當然,若我們仔細看整幅作品的用筆,則不難發現,盡管文彭作品的線形對比明顯,側鋒運用很得體,但他的中鋒運筆還是弱了一些,點畫有些瑣碎感。

《草書滕王閣序》(局部)明·文彭 紙本 28.5cm×229cm(全卷)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通篇來看,文彭在字的體勢上改變了平正的家風而增加了欹側跳蕩,可以看出他或許借鑒了同輩陳淳的結體方法。陳淳是文征明的出藍高足,其祖上與文氏家族大有淵源,他的父親和文征明是好友。陳淳年少時遵父命受業于文征明,為其入室弟子。陳淳在父親去世后性情大變,崇尚玄虛,放蕩不羈,做派與老師漸漸不合,后來交往漸少了。但是陳淳與文彭、文嘉等仍然情誼深厚,且多有來往。陳淳在書畫上是個不落窠臼的人,繪畫自不必說,其書法亦是突破文征明的籠罩,廣學唐宋名家,書風率意奇縱,對后來的浪漫寫意書風很有影響。文彭在與陳淳的交往中,書法觀念受其影響是在情理之中的。陳淳的結體縱橫捭闔,以搖曳多變見長。文彭的《草書滕王閣序》,結體也有這種特點,但不是那么強烈。看“盡東南”“美都督”等字組的處理,皆體現出結體的左顧右盼,照應生情。
另外,從這件作品也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吳門書派”書風開始變化,已經從應規入矩轉向注重抒情。文彭書作中強調取勢,用筆略有狼藉感,并且一絲不安之氣也已露端倪。當然,這也是時代使然。明代中期,江南一帶出現了我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層興起,小說、戲劇、曲藝等市民文藝形式得到蓬勃發展,對個性的追求和抒發日益成為文藝創作的價值取向,這股風氣發展到晚明,浩然掀起了一股個性解放思潮。“吳門書派”也受到了影響,文彭的作品就是一個明證。總之,文彭在文氏家族中努力避開了父輩的某些影響,成為其家族書風傳承創新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