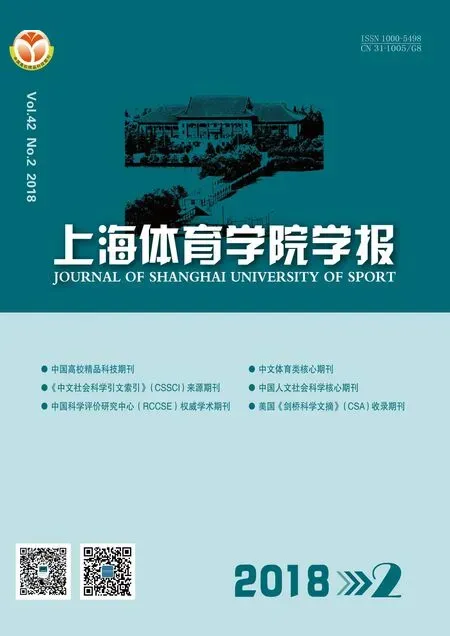體育自治的導向:體育自治權的屬性辨析
李 智, 喻艷艷
(福州大學 法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6)
近年來,國際足聯腐敗事件、俄羅斯田徑隊興奮劑事件等一系列國際體育事件的發生,不僅使國際體育組織的公信力受到廣泛質疑,而且導致外部司法力量的直接介入,嚴重動搖了體育組織的自治管理模式。這一系列事件表明:體育自治權出現權力化趨勢,引發濫權、瀆職、腐敗等各種問題,暴露了目前體育自治管理模式的缺陷以及規制能力的不足,這也是導致外部司法力量介入的直接原因。外部司法力量的介入影響了體育自治這一體育領域的基石。因此,厘清體育自治權的屬性,完善自治權行使的方式,協調與外部規制的關系,是實現善治的根本。
1 體育自治權的屬性之爭
“權利”與“權力”之爭是法理學領域的一個基礎性和歷史性辯題,同樣,對體育自治權在屬性上是“權利”還是“權力”的界定,也影響著體育自治權的范圍劃定、行使方法以及規制方式的確定。一直以來,雖存有爭議,但學界普遍將其視為一種行業自主治理權利。晚近以來,體育組織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權力化擴張趨勢。2015年,國際足聯爆發腐敗案件,國際足聯對世界足球運動所擁有的絕對治理的絕對權力[1],是導致自治體系失控的重要原因。體育組織的自治管理已擴張出較大的權力內容,并形成了公共權力之外的一種新的形態,進而引發了體育自治權的屬性之爭。
1.1體育自治權的產生與發展體育自治權產生于體育活動參與成員的權利讓渡和自愿認可,追溯體育自治的歷史脈絡,最值得一提的是阿諾德在拉格比公學進行的體育教育改革。他將學校內的運動競賽組織工作委托給最有威信的學生,讓他們管理運動場,按照自主原則組建運動隊和俱樂部,舉辦比賽。這種自主管理的方式迅速從校園走向社會,從國內走向國際。雖然在阿諾德的改革中,指定管理者的改革手段使體育自治權的產生略帶強權色彩,但在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演變成現今體育領域的以自愿為核心的自治模式。因此,體育自治權的產生和發展包含著濃重的“契約論”和“自生自發”的理論色彩。
依契約論,人生而自由,但為實現權利,需要通過權利讓渡的方式形成制度和規則,并自愿遵守[2]。哈耶克將社會秩序規則分為“自生自發”的秩序和“組織或者人造”的秩序。前者又稱為內部秩序,這種秩序不具有共同的目的等級序列,所具有的是每個人的目的,但這些不盡相同的目的因行動者遵循規則而得到彼此協調[3]。分析國際體育自治的產生,其依賴于私人契約,進而體系化發展,形成自治秩序,應屬“自生自發”的秩序。首先,體育運動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自然出現的一種行為方式,能促進身心健康,在產生之初與社會公共秩序并無牽涉。其次,人類自由地進行體育運動,而后產生了競技體育,并逐步發展出職業體育。這一發展進程與業余體育并行不悖,只是這個“磁場”越來越大,吸附物與日俱增,參與主體實現了廣泛性。為了更好地開展體育事務,需要有專門的人員、機構進行管理和組織,制訂專門的規則予以規制。于是,參與者們將管理權、規則的制訂權等基礎性權利讓渡出來。再次,在受讓主體的選擇上,基于業務熟悉程度的考慮,受讓主體顯然更愿意把權利交予了解并熱愛體育的人。由此,通過“個人契約”的方式,體育自治權的權利讓渡與交接順利完成。最后,20世紀以來,體育運動國際化極大推動了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運動聯合會、國家奧委會、國內單項體育運動聯合會等體育組織的發展,在成員自主參與的基礎上,體育自主治理權交由各體育組織行使,通過層層讓渡和授權,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國際體育自治權體系。
體系化的國際體育自治權的權屬內容可以概括為3大類:①組織管理權,這是體育自治權最基礎的內容。舉辦體育活動和組織體育賽事是體育事務的起點,包括內部建設管理權和外部組織管理權,即成員的接納和取消、內部組織框架的構建、內部管理機制的完善,以及舉辦體育賽事和管理其他相關的體育活動。②規則制訂權,這是體育自治權最重要的內容。體育組織通過制訂自治規則,將體育自治體系固定下來,以此規范競技體育,將體育參與者讓與權利的目的通過統一的賽事規則體現出來。根據效力層級,依體育自治權所制訂的規則可以分為自治章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根據內容,可以分為技術性規則和非技術性規則。其中,技術性規則主要指賽事規則,非技術性規則包括內部運作規則、紀律規則、糾紛解決規則等。③解決爭端權,這是體育自治權最具發展性和強制性的內容。體育自治權中的爭端解決權主要由2個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各個體育組織對內部糾紛的解決權,另一部分是國際體育仲裁院對國際體育糾紛的解決權。二者分別依托體育組織的內部糾紛解決體系和國際體育仲裁制度,自主處理體育糾紛。
可見,體育的娛樂性、健康性、發展性以及公益性等原初土壤,滋養了底蘊深厚、發展良好的自主治理文明,這也是體育愛好者和參與者智慧的結晶,人類智慧在自發的構建治理制度創舉中催生了體育自治權。即使晚近以來問題出現,但主流觀點仍是呼吁以完善自治為核心,追求體育的良好治理。而且,一貫以來,行政和司法等外部力量對體育自治秉持審慎的干預態度,從側面為體育自治權的發展提供了獨立自主的現實環境,使得“私人契約”的產生基礎和“自生自發”的發展秩序得以固化。
1.2體育自治權的屬性爭議與權力化趨勢如上所述,以契約為基礎,體育自治權自發成體系化,并得到了內部成員的高度認可和外部管制力量的尊重。以此為基礎,體育自治權的形成、發展及內容體現了以下3個主要特點:①權源上的契約性。無論是競技體育還是業余體育,無論是參加體育賽事還是參與其他體育事務,都體現了自愿性。通過自愿讓與產生了體育自治權,是意思自治原則的契約化過程,也是外部力量審慎干預體育自治權行使的原因所在。比起外部強制力,植根于內心意愿的契約精神更能確保治理的成效。②權利形式上的發展性。體育自治源于個人創造,最初也是交由體系內的個人行使的,這一階段的自治權可以歸結為代表權。在體育組織產生之后,轉由組織行使,發展成為團體自治權的一種。目前,尚無法斷定這是否是體育自治權發展的終點,未來是否可能探索出的新形式,值得期待。③權利內容上的綜合性。通常,可以根據某一權利或權力的內容對其進行類型化,例如管理權、審判權、處罰權、處分權等。體育自治權利的組織管理權、規則權以及爭端解決權,既有實體的內容,又有程序的內容,既有決策層面,又有管理層面,既有規制性,又有保障性。可以說,體育自治權既有明顯的權利發展軌跡,又具備權力的某些共性。因而,對其權屬特征的定位,存在以下3種主要觀點。
(1)社會權力說。該觀點從體育自治權的權力性出發,認為這是一種不同于國家權力的社會權力。這種社會權力是社會主體運用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對社會和國家的影響力、支配力,是全球公民社會中的治理權[4]。該觀點在邏輯上的建構是可行的,先進行基礎的定性,再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將其歸為社會權力,由此將其與國家權力、其他公共權力區分開來,充分考慮了自治的特殊性。但是這種觀點易將體育自治權與其他行業的自治權混淆,忽略了體育運動的娛樂至上性的本質以及其他特殊性。而且,“支配力”的闡述放大了體育自治權的效力,也與體育參與者讓渡權利的初衷相背離。尋求體育自治,其目的是讓“體育的歸體育”,并非是支配公共資源,甚至是公共權力,而是探索體育領域更好的治理方式和發展模式。
(2)權利說。依該觀點,體育自治權在本質上仍是一種權利。所以,持此觀點的學者常對體育組織所采取的某些強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提出質疑,例如禁賽、強制仲裁等[5]。誠然,權利說具有基于體育自治權權源上的契約性特點,體現了對體育精神和體育領域私人治理方式的尊重。然而,其對體育自治權內容的擴張性和影響范圍的延展性,未做出關注和解釋。一般情況下,類型化權利的內容指向往往較為明晰和單一,影響范圍也常以其他權利或公共權力為界限,有時還受地域性的制約。體育自治權在內容上具有綜合性,具體內容體系化,在影響范圍上則具有國際性。體育自治權的擴張性和延展性已經突破了權利的請求效力和抗辯效力,具備了一定的類似于權力的強制效力。
(3)綜合說。該觀點不對體育自治權進行定性,認為體育組織的權具有廣泛性,除了自治權之外,還有其他內容,強調自治權兼含權利和權力[6]。綜合說采取了一種折中的方式,兼容并包,試圖全面表述體育自治權的內容。但在基礎問題上模糊定性,會給體育自治權的行使方式、規制方式以及改革導向帶來搖擺不定的風險和困難,不利于體育自治權的結構化和法治化。
綜上,有關體育自治權的權屬爭議主要在于:相比依契約取得的類型化權利,其又具有權力的內容,尤其在外部管制力量對其高度尊重的情況下,在規則制訂、爭端解決等方面,權力化特征更加明顯。自治權利的權力化是晚近體育組織治理過程中最明顯的趨勢。
首先,體育自治權在性質上應該為“權利”,基于體育的特殊性,這種權利包含了部分權力的內容。例如:對運動員參賽權利的規定類似于行政權中的審批權;對運動員的禁賽處分、對管理者“禁止從事足球事務”處罰等紀律處分,則類似于行政處罰權,甚至可以類比為司法審判權對個人權利的限制。這些權屬內容在國際體育領域已經實現了普及化,并且得到體育領域內外的高度認可。以爭端解決權為例,它是體育自治權中最具發展性和強制性的內容,“權力化”趨勢也最為明顯。一方面,體育自治爭端解決在效力上具有內外的強制力。目前,國際體育爭端解決機制是遞進式的3層結構:①體育組織擁有對內部爭端解決的優先權,國際體育仲裁院及各國法院均對此予以尊重[7];②國際體育仲裁院通過各體育組織的章程及運動員協議,取得仲裁管轄權;③各國司法力量對體育爭端的自治解決予以尊重,審慎介入。體育爭端解決的實踐表明,國際體育爭端解決機制兼顧了效率和公正,不僅有效解決了各類體育爭端,且得到了內外部的尊重和認可,兼具極強的內部強制效力和一定的外部強制效力。另一方面,體育爭端的解決在形式上具有類司法權性。爭端解決體系的構建是國際體育秩序得以維護的命脈,在爭端解決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管轄權、規則適用、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等問題,使爭端解決權備受“準司法權”的質疑。
其次,“權力化”趨勢并未改變體育自治權的權利屬性。①私人意思自治的契約基礎所奠定的內在權利屬性未被改變。近代以來,權利本位思想占據主流,強調權力來源,并服務于權利,形成了“權力的權利性”的生成邏輯:權力的內在屬性中包含了權利的價值指向與功能,權力的起源、運行與發展過程會受到權利的價值與功能的指導和規制[8]。即:權利是權力的內在屬性,而非外在特點。體育自治權的發展軌跡恰恰相反,起點是權利,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若干被廣為接納的權力的內容與特點。然而,這種特點僅限于外部形式,其內在屬性仍然是權利。②以內部自愿遵循和外部審慎干預為原則的權利行使方式未被改變。換言之,如果突破了權利的性質,內部強制力將不再以自愿遵循為基礎,轉而以權力的強制性為基礎。根據權力的擴張本性,公共機關的介入隨之成為常態,審慎干預模式將被“以權力制衡權力”的模式替代。
雖然在內部認可與外部尊重的作用下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內外強制力,推動了體育自治權利的權力化,但這種“權力化”是一種“外在特點”,而非“內在屬性”。而且,這種“外在特點”仍給國際體育治理帶來了不小的沖擊,不容忽視。
1.3體育自治權權力化趨勢的影響“權力化”趨勢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體育自治權的內部強制效力日漸增強,并延伸出一定的外部強制效力,進而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體育自治權的權力化提高了體育組織的“自治能力”。比如,就爭端解決來看,國際體育領域已經逐漸形成了由國內單項體育協會仲裁機構、國際單項聯合會糾紛解決機構和國際體育仲裁院組成的具有層級結構的“類司法體系”。體育組織通過這一體系增強“體育王國”的自治能力[9]。自治能力提高后的國際體育組織順應體育商業化的潮流,通過電視營銷權、賽事舉辦權、商業贊助權以及媒體運營權等權利創造了巨大財富。以國際足聯為例,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杯足球賽的營銷利潤逐年遞增,收益已經占到國際足聯財政收入的90%[10]。財政獨立和自治能力的增強是一個雙向的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兩者之間是互促的。財政上不依附于政府等外部機構后,體育組織自治權利的行使就更加獨立;但這也容易使體育組織形成壟斷,拼命逐利。
另一方面,體育自治權的權力化也導致了權利濫用,滋生了不當和違法行為,最終導致司法的強勢介入,從而對體育自治權造成根本性沖擊。在國際足聯腐敗案中,國際足聯的數名高管遭到欺詐罪、洗錢罪、勒索罪等多項犯罪指控,嚴重損害了體育自治權最主要的行使主體——國際體育組織的公信力,還引發了民眾對體育自治體系的質疑與否定。以契約為基礎的體育自治權利在權力化趨勢的影響下,沾染了權力的若干不良屬性,在利益的誘導下成為錢權交易的溫床。在管理上,權利行使存在缺乏透明度、問責機制等弊端,使得規則制訂、組織管理以及爭端解決的公正性飽受質疑。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近年來外部司法力量對體育領域活動干預的不斷增長,從而使國際體育爭端解決出現了崇法主義傾向。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是德國慕尼黑地方法院于2015年1月15日對德國滑冰運動員Pechstein案作出的裁決,該裁決依托德國和歐盟的壟斷法和競爭法,對體育仲裁協議的自愿性、仲裁庭組成的獨立性以及裁決的公正性提出質疑,否定了國際體育仲裁院的裁決。雖然在上訴審理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撤銷了慕尼黑地方法院的裁決,維護了國際體育仲裁院的權威,但慕尼黑地方法院的裁決給體育爭端自治解決體系造成的沖擊堪稱“地震級”。
可見,體育自治權利的“權力化”趨勢對國際體育自治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在增強自治能力的同時也會造成權利濫用,引發外部干預,從而由內而外地削減自治成效。因此,分析體育自治權權力化發展的模式,厘清當下體育自治權的屬性,方能準確定位體育自治權的基本功能,提出適應體育活動的治理方式。
2 體育自治權的權利發展模式
體育自治權利的權力化趨勢是在體育的商業化、政治化以及社會化過程中,因內部認可和外部尊重程度日漸提高而促成的。因此,與公共權力、其他團體自治權以及體育活動參與主體的個人權利相比,體育自治權形成了一套頗具特色的權利發展模式。
2.1利與力:體育自治權與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是指在公共管理過程中,由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掌握并由其工作人員行使的,用以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的權力。基于權利與權力的本質差異,體育自治權與公共權力的區別顯而易見,但二者的共性也較易窺見,即都致力于實現維護良好秩序以及實現更好發展的價值。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建立了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平權式國際社會體系后,即代表對外獨立權和對內最高權的最大公共權力——國家主權,樹立了絕對權威,國際社會和絕大多數國家都維持了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人類社會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同樣,體育自治權產生伊始也是為尋求更好地開展體育活動的方式。而在其發展進程中,尤其是國際體育組織“遍地開花”之后,體育自治權內容得以豐富,權利得以充分行使,實現了國際競技體育的組織化、規則化和制度化,建立了較為穩定的國際體育秩序。然而,權利是利,權力是力,畢竟是不同的事物[11]。
(1)在權源上,二者雖然都可以運用“社會契約論”理論進行解釋,但是權利讓渡之后,所形成的公共權力本身就有了發展和修飾,創造出“國家強制力”和“暴力機關”,以確保公共權力的實現。受讓形成的體育自治權仍保持權利的狀態,維系運行的也是成員的尊重、認可以及自愿遵從,所以在起初并無外化的強制效力,也并未產生體育自治強制機關。
(2)在公共權力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從人民到法律的權力認證范式,在現代社會,法律捍衛權力并使之合法化。體育自治權并不存在這樣的論證模式,它不需要得到法律的認證,即得到承認,并維持良好的運作狀態。即“法無規定皆禁止”和“法無禁止皆自由”的分別適用,只要不違反法律的規定,自治權的行使在權利讓渡范圍內是自由的。同時這種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也不能凌駕于國家主權之上。因此,不難理解在國際足聯腐敗案件爆發后,馬上引發了公共權力干預體育自治的強烈沖動,并付諸實施,體育自治權并不能成為國際體育違法和犯罪行為的保護傘。
(3)公共權力,尤其是國家公權力,是公共產品的當然提供者,公共產品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例如國防和立法行為等。體育自治權卻并非體育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這也是體育自治權與體育行政權的最主要區別。體育自治權被權利來源方賦予了促進世界體育發展的使命,不同的體育組織的自治權內容和范圍不同,提供的產品具有競爭性。在本質上,體育自治組織的義務之一是使權利讓與主體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職業體育領域,為成員創造的利益量決定了職業聯盟或俱樂部的認可度,也直接決定了他們自治權利的大小。以轉會制度為例,轉會規則日趨復雜,考慮的因素不斷增多,正是在市場經濟供需杠桿的作用下,體育組織運用自治權完善規則以提高競爭力。再如體育贊助制度,它是體育自治權發揮調適作用,尋求體育運動與商業經濟并行發展和利益平衡的產物。
2.2公益與共益:體育自治權與其他團體自治權團體自治權是指社會組織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權利[12]。廣義的團體自治權還包括民族區域自治權等因地緣、血緣因素形成的公共自治權。狹義的團體自治權僅指社團自治權,較為典型的如各行業的自治權。這些團體的自治權(也稱行業自治權)在權源上都是產生于會員之間的契約[13],在利益追求上都是謀求行業成員的共同利益。體育自治權應歸屬狹義團體自治權的范疇,不過,憑借體育的特殊性,體育自治權較之其他團體自治權又具有以下3個明顯特征,并成為體育自治權突破權利“柵欄”,日漸延展出權力強制力特點的內因所在。
(1)體育自治權具有更徹底的自治性。以爭端解決為例,體育自治權的徹底性在國際體育強制仲裁制度上得到凸顯,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制度使國際體育仲裁院的仲裁管轄權和仲裁裁決權威得以確立。相比較而言,商事仲裁制度雖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認可,但國際商事仲裁的廣用性得益于仲裁解決商事糾紛的優越性,而國際體育仲裁體系的發展,除了延展了仲裁的優越性之外,也進一步推動了體育領域的自我治理。
(2)體育自治權具有更明確的公益性。體育是促進全人類身心健康的事業,競技體育產生伊始就被賦予“停戰”的和平使命,并產生了“奧運停戰協議”。近代以來,體育在國際政治交往中更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中美的“乒乓外交”,而“足球”等甚至成為某些民族和國家精神的象征。所以,即使受到商業化的沖擊,體育所倡導的和平、共贏的理念,仍然是其最終的內在追求。所以,在體育自治權價值理念上,公益性和共益性是并列的,這也是體育自治權得到極大尊重和信任的原因之一。相對而言,其他團體自治權更強調共益性。盡管也提及社會責任,但這種社會責任的實現往往也是為了通過樹立良好形象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這與體育治理的公益性訴求相去甚遠。
(3)體育自治權始終與公共權力保持距離。晚近,其他行業自治權與公共權力的關系出現趨同。公共權力通過委托或者授權等方式,將部分權力交予團體組織行使,將部分職能委托其履行,行業自治權和公共權力通過行使主體的趨同在某些領域實現了統一。反觀體育自治權與公共權力,則始終保持相互獨立的狀態,近年來還時有沖突,沖突的解決過程均是在堅持體育自治性的基礎上,不斷明晰著二者的邊界。哈耶克曾經指出:在一個傳統和慣例使人們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預期的社會中,國家的強制力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14]。以自治權行使為核心所建構的國際體育治理機制,憑借自治的優越性,弱化了國家強制力即公共權力的作用空間。
2.3集體與個體:體育自治權與其他體育參與方權利權利沖突是平等主體間法律糾紛最常見的原因,體育領域亦然。體育自治權來源于成員方的權利讓渡,但伴隨著體育利益和體育參與主體的不斷增多,體育自治權得以擴展,也導致它與其他體育參與方權利之間的沖突頻發。參賽資格糾紛、強制仲裁公平性爭議、贊助合同糾紛等事件逐漸成為體育爭端中的主要問題。明確二者的關系和邊界,是解決爭議的根本。
(1)自治權應遵從成員意志。體育自治權的唯一來源是體育參與方的個體權利,因而其權利邊界以成員權利讓與程度和范圍為限。以體育仲裁協議制度為例,在國際體育爭端解決體系中,通過3個環節確定了體育仲裁協議具有相當的強制性:一是仲裁協議的條款化;二是仲裁條款的格式化;三是格式化的仲裁條款在特定因素促成下,產生了強制效應[15]。分析此處的“特定因素”:當事人在選擇參與某一國際體育組織或國際體育賽事時,已行使了自主選擇權,自主將爭端解決方式的決定權讓與國際體育組織,國際體育組織行使受讓的權利,制訂了統一的“強制仲裁協議規則”,改規則適用于參與的成員。意思自治是啟動仲裁程序的起點因素,這種得到認可的強制仲裁協議制度形式上是強制的,在實質上仍是意思自治。因而,即使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選擇協議具有強制力,但其根本仍來源于成員意志。在上述德國速滑運動員Pechstein案中,國際體育仲裁院強制仲裁條款雖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裁決中遭到質疑,但最終在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中獲得了支持,說明權力化趨勢不應動搖契約性權利這一基礎。
(2)體育自治權應關注個體權利的實現。體育自治權是典型的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具有發生沖突的必然性。比如:近期頻發的運動隊(員)贊助合同沖突問題。職業聯盟對贊助商的選擇往往基于全體成員以及聯盟自身的考慮,但可能與某些個體運動員的利益產生沖突,尤其是一些商業價值較大的運動員。在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易建聯球鞋”風波中,易建聯以腳部不適為由,比賽中途更換球鞋,被認定違反聯賽規則,處以禁賽和罰款的處罰[16]。無獨有偶,林丹、孫楊等著名運動員的代言合同,也都與相應的國家隊集體代言品牌協議產生沖突。在體育商業化背景下,個體權利與體育自治權的沖突更加突出,也更需要體育自治權做出相應的調適,通過完善規則,考量個案,既維護自治體系,又關注個體權利的實現,充分體現公平,實現其“更好地管理體育”的初衷。體育自治權與個體權利同處一個利益鏈條,不管是權力間的關系,還是權利間的關系,亦或是權利與權力的關系,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利益的博弈。國際體育自治秩序的形成是以權利過渡為紐帶,依賴于體育參與者這一數量龐大的利益主體的團結一致。體育自治權與體育參與者的個人權利,正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這一理念上得以協調的。
總之,體育自治權既區別于公共權力,又區別于一般的團體自治權和其他個人權利,在利與力、公益與共益、集體與個體等差異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套頗具特色的權利發展模式。在價值追求上,其權利來源于成員的讓與,故而追求成員的共益。同時,體育自治權又依附于促進人類身心健康的體育活動而存在,因而又追求人類體育發展的公益。共益與公益同處于體育自治權所追求的同一價值鏈上,共益是基礎,公益是最終目標。正因為如此,即使體育自治權出現了“權力化”趨勢,仍被廣泛接納,并發展良好。在體育自治權行使方式上,體現為成熟徹底的私人自主治理模式。這一模式得以形成的現實基礎是內部認可和外部尊重,而以組織自治、規則自治以及爭端解決自治為核心的穩固的“三角架構”則是其制度保障。基于此,展望體育自治權的發展與完善:一方面,應在自治作用下與公共權力繼續保持分離態勢,依托“三角架構”,借助體育商業化、政治化和社會化的發展土壤,固化獨立自主的權利行使方式;另一方面,應探索“權力化”發展帶來的權利沖突、價值偏差等問題的解決之道,依托體育自治權的“權利”屬性,以之為導向,完善國際體育自治體系。
3 權利導向下的國際體育自治
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指出:體育改變世界,但并非憑借一己之力[17]。毋庸置疑,在國內和國際層面,體育的價值都出現了多元化趨勢。“良好的治理”是利益權衡的需要,也是體育發展的需要。厘清屬性,分析發展模式,進而確立完善國際體育自治的導向,實現國際體育的良好的自主治理。
3.1權利導向:引導而非限制“善治”中的“治”包括兩重含義:一是指一種治理的方式和模式;二是指一種秩序、狀態、結果[18]。概括地說,其就是使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19]。體育本身就具有公益性,體育自治權在產生之初就被賦予維護良好的世界體育發展秩序的使命。不僅為參與成員的共同利益服務,而且追求全人類的身心健康,這是公共利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體育自治權利的最終目標與良好治理的追求在價值上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從權利屬性出發,“良好的治理”關鍵在于以權利為導向,進行體育自治路徑的優化和制度的變革以及體系的完善。
具體而言,權利導向包括2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體育自治權的權利屬性必須被充分認識,同時該團體權利的行使應該服務于自愿讓渡的私人權利,而不能反過來憑借團體權利的力量聚合,侵蝕處于弱勢的私人權利。正如體育的商業化、政治化及社會化的發展不可逆轉一樣,體育自治權利的“權力化”趨勢不可避免也無法改變,而且還有可能進一步增強。所以,應該強調體育自治權的內在權利屬性,以此為基礎,追求良好的國際體育自主治理。另一方面,在進行制度改革與優化時,應該適用對權利而非權力的約束規則,即應該是引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具體包括對權利行使方式的優化、對權利行使過程的引導、對權利行使結果的監督,以實現權利行使效益的最大化。
3.2自下而上的內部調適遵循“由下而上”的原則進行內部調適,優化權利行使方式,是從體育自治權的權利行使主體的角度,追求成效良好的國際體育自治的重要方式。社會契約理論下的權力的形成是“由下而上”的,但權力的行使是憑借強制力和暴力機關“自上而下”的。相比較而言,私人契約理論下的國際體育自治權作為一項團體權利,其產生和行使應遵循“由下而上”的原則。
(1)通過豐富權利行使主體增強權利行使質效。目前體育自治權行使主體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國際體育組織,主要包括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國際體育仲裁院等;二是國內體育組織,如國家奧委會、國家單項體育協會、國家體育仲裁協會等。權利行使主體已經實現了從個體到集體的發展變化。在權利行使方式方面,各體育組織都在章程中規定了民主化原則,設立職能機關,分別行使規則性權利、組織性權利以及爭端解決權利,以形成分工明確、相互制衡的機制。隨著“自治權利”的膨脹,體育管理層權力不斷膨脹后,出現了脫離體育參與者的傾向,導致體育自治權利的行使偏離軌道,發生了腐敗、瀆職等不當行為。過于集中的權利行使方式削減了行使效果,修正的要義在于“私人自治并非個人自治”。所以,可以考慮管理機關權利的下放,效率價值的實現前提應該是公正價值,集體權利較之個人權利最大的特點在于團體性,這一特點應貫穿權利行使的始終。
(2)對爭端解決性權利這一出現“權力化”趨勢的權利,應該適當采納司法權的行使方式。在程序設置上,除了當前的正式裁決程序、上訴程序之外,還可以考慮增設其他申訴程序,通過豐富爭端當事人的參與形式促實體正義的良好實現。在規則適用上強調可適用規則的多樣性,在自治規則優先適用規則之下,考慮一般法律原則的替代適用和國內法的有條件適用,以彌補自治規則的缺陷[20]。在裁決過程中,要充分考慮體育事務的特殊性,但不能忽視當前國際體育的政治化、商業化及社會化發展趨勢,在權益保護和利益分配方面應適當傾向于弱勢方,尤其是運動員的基本權益保護。
3.3外部干預的適當引導引入適當的外部干預機制,引導權利的行使過程,監督權利的行使結果。這是從體育自主治理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角度追求成效良好的國際體育自治,是一種外部引導。體育是全人類的事業,參與主體在國籍、年齡、職業甚至生理等各方面都具有廣泛性,所以體育自主治理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有責任對國際體育自治權的權利行使加以引導和監督,以實現良好的治理。
(1)在規則性權利方面,強調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引導。必須明確一點:自治規則不得剝奪法院對這些規則進行解釋的權力[21]。通過保障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的規則解釋權,一方面尊重體育規則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在權益保護、制定技術以及價值取向方面引導體育規則更具公正性和規范性。此外,法院對規則的解釋權應包括技術性規則和非技術性規則等各類體育規則。技術性規則是國際體育規則中的基礎性規則,對運動員的影響最大,所以不應該以特殊性為由反對外部機關的解釋權。非技術性規則以管理規則為主,對這類規則的解釋會間接引導國際體育管理秩序的合理性。
(2)在組織性權利方面,強調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引導。體育組織作為一種社團法人,其成立和解除都需要經過特定的行政程序,行政權應該在準入、發展以及退出等方面進行引導和監督。這里還涉及“體育行政權”和“體育自治權”的沖突與協調。從屬性上來說,這是權力和權利的沖突在體育領域的反映,應該遵循“權利本位”的原則進行協調。體育行政權主要在宏觀層面協調國內體育事業的全面發展,而體育自治權則是在微觀層面促進體育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可能出現的交叉領域,例如賽事的開展上,體育行政權應該發揮引導作用,讓體育的歸于體育,違反公共秩序時再強勢介入。在組織性權利行使的監督上,行政權側重于對體育組織及其管理人員“體育不當行為”的監督、懲戒及糾正,而司法權則是對“體育違法行為”的矯正。
(3)在爭端解決性權利方面,由于這一權利的“權力化”趨勢最為明顯,應該通過構建完善的國際體育司法救濟機制以解決當前國際體育爭端自治解決體系中存在的顯失公正、違反公共秩序等問題。事實上,在堅持“審慎干預主義”原則的前提下,效力在上位司法救濟體系能夠反促國際體育爭端自治解決體系的發展。
可見,體育自治權的內在權利屬性決定了國際體育良好的自主治理應該以內部調適為重點,而外在特點上的“權力化”趨勢又使得能夠實現有效監督和制約的外部干預成為必要。而且在私人自治領域,適當的公共權力介入和良好的外部監督體系可以倒逼自治體系的內部改革,增強內部自制力,以消解“權力化”趨勢下自治能力增強后帶來的權利濫用風險,實現國際體育的良好自主治理成效。
4 結束語
體育之所以能形成一個完善的私人自治體系,并不間斷地發展到今天,源自于它在古代和現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經理比爾·尚克利曾言:足球不光是關于生與死的事情,它遠比生與死更重要。盡管如今的體育包含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豐富內涵,但在健康、熱情、平等、和平、公正等這些最初被寄予的理念上,仍然是體育所能體現的人類美好的共同追求,甚至可以說是人類的自然權利。同樣,根據私人契約形成的體育自治權發展程度的提高,不應該偏離“權利屬性”這個既定軌道。當前,公域治理已經由單純的國家壟斷轉變為國家與社會合作治理[22],但社會治理本質上還是一種公共治理,是權力導向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國際體育良好的自主治理的實現,應該是權利導向的。在權力和權利的關系上,以權利為本位,發揮權力的引導和監督作用,實現權利行使的效益最大化;在團體權利和個人權利的關系上,以私人契約理論為基礎,恪守團體權利的最終目標以促進個人權利的更好實現。
[1] HENK-ERIK M.Keeping private governance private:Is FIFA blackmailing national governments?[EB/OL].[2017-03-10].https://dspace.lboro.ac.uk/2134/12635
[2] 盧梭.社會契約論[M].科爾,譯.上海: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1-2
[3] 鄧正來.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哈耶克法律理論的研究[J].北大法律評論,1999,2(2):395-445
[4] 張文聞,吳義華.國際體育組織自治權的法理分析[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6,50(8):44-48
[5] PANAGIOTOPOULOS D.International sports rule’s implementation-decisions′ executability:The Bliamou case[J].Marquette Sports Law Review,2004,15(1):1-12
[6] 彭昕.我國體育自治建構的法理詮釋[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3,30(6):650-655
[7] 李智.體育爭端解決法律與仲裁實務[M].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出版社,2012:12
[8] 胡杰.論權力的權利性[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2):83-89
[9] 向會英.體育自治與國家法治的互動——兼評Pechstein案和FIFA受賄案對體育自治的影響[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16,40(4):42-49
[10] GUILLERMO J.Fixing FIFA: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ependent governance committee[J].Sou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4,21:165-174
[11] 漆多俊.論權力[J].法學研究,2001(1):18-32
[12] 李海平.論作為憲法權利的團體自治權[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51(6):141-146
[13] 汪莉.論行業協會自治權的權源及其性質[J].學術界,2010(7):75-82
[14]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3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1
[15] 張春良.強制性體育仲裁協議的合法性論證——CAS仲裁條款的效力考察兼及對中國的啟示[J].體育與科學,2011,31(1):19-28
[16] 搜狐體育.廣東:接受處罰盡力解決阿聯今后所穿球鞋問題[EB/OL].[2016-11-03].http://sports.sohu.com/20161103/n472209420.shtml
[17] Historic Milestone:United nations recognises autonomy of sport[EB/OL].[2017-03-10].http://www.olympic.prg/news/historic-milestone-united-nations-recognises-autonomy-of-sport
[18] 王利明.法治:良法與善治[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2):114-121
[19] 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0
[20] 喬一涓,李智.國際體育爭端解決中的規則適用[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5,49(10):34-39
[21] 貝洛夫,克爾,德米特里.體育法[M].郭樹理,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32
[22] 徐靖.論法律視域下社會公權力的內涵、構成及價值[J].中國法學,2014(1):7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