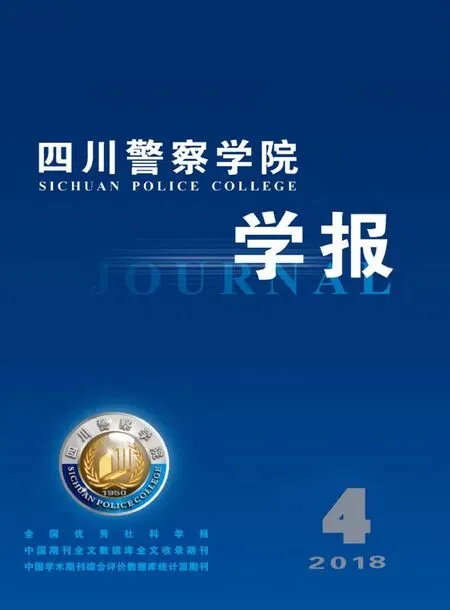論既遂標準的確立—構成要件說的重構
李佳波
(華東政法大學 上海 200042)
犯罪既遂這一概念,不論是在刑事立法還是司法實踐的發展過程中都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由于我國刑法分則并不是既遂模式,且只有關于未遂、預備等狀態的規定,關于犯罪既遂的標準認定一直存在重大爭論。而且對于刑事立法和司法中數目龐大的犯罪手段及方式,不同罪名之間的區別,特別是容易混淆的罪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犯罪既遂標準的區分,并且此罪的既遂與易混淆的彼罪的未遂、中止、預備之間都很可能存在競合抑或交叉,因此理清犯罪既遂的標準顯得尤為重要。
一、犯罪既遂標準主要學說概述
在我國刑法學界,雖然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是犯罪構成要件說,但是關于犯罪既遂標準的爭論一直存在,目前主要存在犯罪目的說、犯罪結果說。而且隨著對犯罪既遂標準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犯罪目的說和結果說在不斷改進中,而犯罪構成要件說被不斷質疑,通說地位動搖。
(一)犯罪目的說
目的說認為,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并發生一定的犯罪目的,是成立犯罪既遂的標志;如果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而沒有發生特定的犯罪目的,只能成立犯罪未遂。概言之,犯罪目的說就是“以是否實現犯罪目的作為既遂、未遂的區分標志”[1]。根據對目的的不同理解,目的說又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主要學說。1.犯罪目的說。犯罪既遂是通過犯罪,犯罪人在客觀上已實現犯罪目的的犯罪形態[2]。2.直接目的說。每一直接故意犯罪的行為都有其直接目的,也有其相應的結果,該直接目的的實現或相應結果的產生,就是犯罪既遂[3]。3.概然目的說。該說認為,在認定犯罪是否得逞時,所應當根據的就是法律觀念上的具有概然性的犯罪目的,而不是各具體主體在犯罪時的具體目的[4]。
從以上學說可以看出,目的具有層次性與多樣性,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犯罪目的”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爭議,何為目的,以何種目的作為標準都不具有確定性,是一個模糊的、難以客觀衡量的標準,我們不能以一個不確定的標準作為標準,因此,筆者不贊同犯罪目的說這一既遂標準。
(二)犯罪結果說
結果說認為,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并產生一定的犯罪結果,便成立犯罪既遂[5]。那么,什么是一定的犯罪結果呢,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觀點。1.法定的危害結果說。該說認為,犯罪人實施犯罪客觀要件的行為,在發生了法定的犯罪結構的情形下成立犯罪既遂[6]。2.追求的法定結果說。該學說認為成立犯罪既遂不但要求發生行為人追求的結果,而且這種結果還必須是法律規定的。3.犯罪完成結果說。該說認為,只有發生了標志犯罪完成的結果,才能成立犯罪既遂。4.希望或追求結果說。有學者認為,犯罪既遂的定義應當是:犯罪人實施完成的犯罪行為,并引起他所希望發生或追求的犯罪結果[7]。
結果說以一定的危害結果作為既遂標志,這就要求所有存在犯罪停止形態的犯罪要成立犯罪既遂,均需要發生特定的危害結果。但是,很多犯罪是不可能產生特定的危害結果的。例如危險駕駛罪,行為人在高速公路上危險駕駛,但是沒有導致車禍,沒有造成一定的危害結果。又比如,甲對單位有意見,于是在單位的食堂水缸投毒,在許多員工吃下毒物后,他又后悔并給中毒者服用解藥,員工身體健康沒有受到實質損害。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有對應的結果,因此犯罪結果說也不應當作為統一的犯罪既遂標準。
(三)犯罪構成要件說
犯罪構成要件說,該說認為犯罪既遂的標準就是犯罪行為具備犯罪構成要件。作為刑法的通說理論,不同學者對于犯罪構成全部要件齊備說的觀點本質上幾乎都相似,沒有重大分歧。但近年來,不斷有學者質疑構成要件說的存在合理性,為此構成要件說的支持者在原有的理論基礎上完善了構成要件說。
1.修正的構成要件齊備說。持該說的學者認為,犯罪既遂的認定,不能機械的認定齊備所有的構成要件,而應當同時結合從實質上界分既遂與未遂的觀點,從而使既遂標準更加全面準確。并主張不能超過犯罪構成要件齊備的限度來界定犯罪既遂標準,即首先必須從形式上齊備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但是在判斷是否齊備構成要件齊備時,又須對刑法規定進行實質解釋,符合刑事立法的原意,從而最終確定犯罪既遂的標準[8]。
2.客觀要素充足說。該說是指根據刑法分則規定的某種犯罪所需滿足的客觀方面,結合理論通說和司法實踐,確認該犯罪所屬的既遂類型,判斷其是屬于行為犯、結果犯還是危險犯,然后根據行為犯、結果犯、危險犯的不同既遂標準進行第二層次的評價,看行為的客觀方面是否滿足所屬類型的既遂標準所需要的客觀要素,比如,結果犯的既遂標準是產生法定犯罪結果作為[9]。簡而言之,就是結合司法實踐,根據刑法分則規定的某種犯罪客觀方面,先確定犯罪所屬的既遂類型,再判斷行為符不符合該既遂類型所需要的客觀要素。
綜上所述,犯罪目的說和犯罪結果說由于目的和結果本身的不確定性,不能作為衡量標準,因此,本文只探討如何使犯罪構成要件說成為更加完善的既遂標準。
二、犯罪構成要件說的借鑒與批判
(一)構成要件說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構成要件說規避了目的說和結果說存在的弊端,將刑法中各種各樣犯罪的既遂形態與未遂形態區分情況進行了全面而科學的概括。其次,每個罪都只有一個確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并且都是由法律規定,或者學界的通說確定,因此犯罪構成要件這一標準是唯一確定的。最后,因為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的標準,所以脫離犯罪構成后,就不能對犯罪停止形態加以準確的認定,行為要成立犯罪,都必須符合犯罪構成。而犯罪停止形態是指在行為成立犯罪即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后所表現出的不同狀態[10]。
犯罪構成要件說克服了結果說和目的說所存在的多樣性、復雜性之不足,使得犯罪既遂標準變得更為確定、一致。畢竟對所有犯罪而言,齊備犯罪構成全部要件基本上都是唯一的,不存在所謂的要件不同造成的認定標準不一的問題。但是犯罪構成要件說在理論基礎上和具體適用時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改進。
(二)對構成要件說質疑之思考
1.與停止狀態范圍相矛盾。按照犯罪構成要件說的觀點,犯罪既遂就是符合刑法分則的規定構成要件,那么按照這種邏輯,刑法分則也規定了過失犯罪的構成要件和刑事責任,所以過失犯罪也存在犯罪既遂[11]。然而根據通說,討論犯罪的既遂、未遂、預備的前提是行為人故意犯罪,既遂、未遂的區分不存在于過失犯罪中,只有故意犯罪有犯罪停止形態。這就導致了理論上的矛盾。
這種觀點實際上沒有明確既遂討論的前提,既遂只有在直接故意犯罪中才會談論,過失犯罪和間接過失犯罪中并沒有既遂和未遂的區分,這種批判意見本身就將既遂置于全部犯罪中討論,然后批判既遂標準沒有在既遂存在的范圍內討論,這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犯罪構成要件說原本就只適用于直接故意犯罪。
2.引起既遂標準混亂。有學者認為,關于犯罪既遂的觀點,如果適用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那么同一種犯罪有兩個不同的既遂標準,比如破壞交通設施罪,未導致火車、輪船等交通工具傾覆、毀壞的是既遂,導致交通工具傾覆、毀壞的也是既遂,又如爆炸罪,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是既遂,造成嚴重后果的也是既遂。這從理論上來講是邏輯不通的,也不符合犯罪分子的主觀心理狀態。
這一觀點本身并不成立,放火罪,其既遂標志是被燃物能夠獨立燃燒,未造成嚴重后果和造成嚴重后果只是量刑輕重的依據,或者說造成嚴重后果是結果加重犯的既遂標志,既遂標準并不混亂。
3.前提不真實。犯罪構成要件說源于英美法系國家,而就美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刑法分則立法模式都是犯罪既遂模式。因此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形態模式為犯罪既遂模式是犯罪構成全部要件齊備說賴以成立的前提條件。然而這個前提是不真實的。既遂模式的前提起碼在我國現行立法的條件下是不存在的,在故意犯罪中,許多條文在對罪狀的描述中并不規定犯罪結果的內容,若堅持分則規定既遂模式的前提,就會得出殺人罪是行為犯的結論,這顯然并不符合我國司法與理論界的通論觀點[12]。而且我國刑法總則明文規定了犯罪未遂及其刑事責任,這就說明犯罪未遂不是負刑事責任的例外,而是確立了犯罪未遂要負刑事責任的原則。
雖然我國對于刑法分則是成立模式還是既遂模式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犯罪既遂模式的理論地位并不穩定,將犯罪既遂標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一個不確定的既遂模式理論上,犯罪構成要件說這一標準也將有所動搖,因此,要確立犯罪既遂模式的標準,必須擯棄刑法分則是既遂模式這一理論基礎。
4.與犯罪成立相混淆。有學者認為,犯罪構成要件是只針對具體罪名,而不存在于犯罪形態中;故意殺人罪、搶劫罪等有自己的犯罪構成要件,有主客觀方面等,但預備犯、中止犯等本身并沒有自己的犯罪構成要件。犯罪預備、犯罪中止、犯罪未遂與犯罪既遂的區別在于組成犯罪構成要件的具體案件事實不同,而在犯罪構成要件方面并沒有不同。具體犯罪與犯罪形態的關系,混淆了法律規定的犯罪構成與具體案件事實的關系,也有違罪行法定原則[13]。犯罪既遂是犯罪成立后的一種停止形態,犯罪成立后還可能存在未遂、中止等形態,一個犯罪行為齊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并不能說明就是犯罪既遂,只是說明該行為構成了這個罪名。
確實,客觀的說,我國很多學者在闡述犯罪構成要件說確實混淆了犯罪構成成立標準和既遂標準,直接將犯罪構成要件作為既遂標準。但犯罪行為是否具備某種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并不是區分既遂、未遂界限的根據。或者說是學者在表述時沒有詳細闡述犯罪構成全部要件的概念,導致將該全部要件等同于成立犯罪所需要的全部要件。
5.涉嫌循環論證。在立法上,刑法并沒有明確區分“危險犯”“結果犯”“舉動犯”“行為犯”,這些既遂類型的劃分是來源于理論和司法實踐。“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先確定不同的既遂模式,將某種犯罪歸到某一既遂模式中,然后再來研究這種犯罪的既遂標準,如以結果達成與否作為既遂標準,即以已知的各種犯罪的既遂模式來確定標準,而不是先確定統一的標準再來認定各種犯罪的既遂與未遂形態[14]。確定犯罪既遂與未遂的劃分標準本身正是為了正確地區分兩者,那么既然已知每一犯罪的既遂與未遂模式,再去研究犯罪既遂標準就是多此一舉。在這個論證過程中,“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以一個已知的真實論題,來論證論據的真實性的論證方法,是典型的“循環論證”。
確實,目前的犯罪構成要件說基本上都有一個分類,那就是結果犯、行為犯和危險犯,但是事實上,這種分類就是在確定了將某一結果或者行為作為既遂的標志,然后再用犯罪構成的既遂標準論證結果犯、行為犯的既遂標準,顯然是一種循環論證,因此,在重構犯罪構成要件說時必須放棄結果犯、行為犯和危險犯這一分類。
總的來說,很多犯罪構成要件說的反對意見都有些強詞奪理,但是有些觀點確實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比如如何明確區分犯罪成立與犯罪既遂標準,如何在沒有既遂模式的前提下適用構成要件說,如何避免循環論證等。
(三)既有重構犯罪構成要件說的不足
針對前文所述的犯罪構成要件說的質疑意見,很多學者對犯罪構成要件說進行了完善和重構,但是這些重構還是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在修正的犯罪構成要件說中,區分了犯罪成立的“犯罪構成”與犯罪既遂的“犯罪構成”,認為包含四要件的“犯罪構成要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而修正的犯罪構成中的“犯罪構成”,是指在犯罪成立之后,即符合四要件的犯罪構成基礎上,影響故意犯罪停止形態的各犯罪構成要素的總稱,是量刑的標準。換句話說,討論行為的停止形態是在行為成立犯罪的基礎上,二者不是同時進行評價,而是一個前后銜接的過程。修正的犯罪構成的內容明顯超出了犯罪成立的犯罪構成所包含的四要件。以盜竊罪為例,該罪的既遂就不僅包括著犯罪成立的四要件,如乘人不備,秘密竊取等,還必須符合“取得財物”這一結果性構成要素[15]。在客觀要素充足說中,符合基本構成要件只是犯罪成立的標準;而每一構成要件,如主觀方面中,又包含多種要素,將原來的四要件的內容進行豐富,只有構成要件的每一要素都充分了才能構成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既遂;這種學說是同時評價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和是否構成既遂,如未遂犯只是成立犯罪但不具備充分的構成要件要素[16]。
這兩種學說都沒有具體說明哪一要素才是成立犯罪既遂的標志,具體各罪的要素還需要具體鑒定,而且構成要件本身就內含了要件內部的各要素,比如說客觀要件中的行為和結果,不需要再明確指出。如果以修正的構成要件作為既遂標準,容易導致與成立犯罪的構成要件概念混淆,指代不明,并且也沒能明確區分何為基本的犯罪構成,何為修正的犯罪構成。因此這兩種學說都沒有確立一個明確可執行的犯罪既遂標準。
綜上所述,雖然犯罪構成要件說存在一些缺陷,但瑕不掩瑜,其通說地位不可動搖,而對于其中的缺陷,雖然很多學者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完善和重構,但是都沒能有力反駁犯罪構成要件說最大的缺陷,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犯罪構成要件說的完善之路。
三、構成要件說的完善
(一)劃分構成要件的成立和既遂標準
犯罪成立是犯罪既遂成立的前提,因此犯罪既遂的要件滿足必然包含犯罪成立的要件滿足。而犯罪成立是需要滿足構成要件的全部要件,那么如何犯罪成立需要的全部要件和犯罪既遂需要的全部要件呢?以故意殺人罪為例,刑法條文中只規定“故意殺人”,要成立故意殺人罪,行為人只要符合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要素,主體要件中的責任能力要素,侵害或威脅他人的生命權的這一客體,并且客觀上實施了殺人行為并可能導致被害人死亡,就成立了故意殺人罪,簡而言之,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有殺死被害人的可能性,不論可能性大小。而要成立故意殺人罪的既遂,需要達到實際殺死被害人的程度。所以犯罪既遂與未遂、預備形態的最大區別在于,未遂與預備形態只具有滿足構成要件全部要件的可能性,未遂與預備形態的可能性大小的區分依賴于刑法中關于犯罪停止形態的規定,而既遂形態是最大程度滿足全部構成要件,只要構成要件中任一要件只具有可能性,即使是這個可能性無限接近于構成要件的最大程度,都不成立既遂。
概括來說,犯罪成立標準就是構成要件的全部滿足,犯罪既遂的標準就是全部構成要件的最大程度滿足,如果沒有最大程度滿足,只具有滿足的可能性時,就是犯罪未遂或者預備。這一區分能夠有效避免犯罪成立要件和犯罪既遂要件的混淆。而何為全部構成要件的最大程度滿足需要進一步確定。
(二)確定構成要件的既遂標準
犯罪既遂的標準就是在犯罪構成要件達到最大程度的滿足,而這一最大程度的確定可以通過無線放大未完成形態的要件滿足的可能性,當可能性趨近于無窮大直至成為現實,即研究處在相對于未完成形態的延長線上的某一個臨界點,這一臨界點即為犯罪既遂的標準。
如何確定這一臨界點,或者說什么要件影響著可能性的程度。顯而易見,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體和客體并不會成為判斷可能性程度的標準,在區分犯罪的既遂和未完成形態起著作用的主要是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所以這兩個方面的內容應該被包含在相對于未完成形態延長線上的臨界點中。
先從主觀方面來看,主觀方面主要是指行為人的故意和過失心態,而過失犯罪沒有既遂、未遂之分,所以僅考慮行為人的故意,故意的內容包括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兩方面。認識因素是行為人明確知道自己的行為并且打算實施,即“明知”,行為人一旦具備了認識因素,就完成了犯罪的第一步,即產生了犯意,但是意志因素不同,它具體表現為行為人預備完成的犯罪目的,從犯意的產生到犯罪目的的完成有一段過程,在這個完成過程中,行為人可以將其放棄或終止。所以從主觀上講,犯罪中止是將犯罪目的放棄了或者終結了犯罪目的的持續狀態,犯罪既遂相對于犯罪中止而言,是犯罪目的一直處于延續的狀態。
再討論客觀方面,許多刑法著作中認為犯罪中止只要在犯罪結果發生之前,或者是在某種狀態形成之前,刑法明文規定犯罪中止是發生在“犯罪過程中”,而未遂犯也有實行終了與未實行終了的未遂之分,終了也是犯罪中的某一狀態,從這些例子來看,可以說明犯罪既遂處在未完成形態延長線上的點,在這個點之后犯罪處于怎樣的狀態就不必再進行評價,也即犯罪既遂的標志就是某種狀態的出現。而綜合犯罪主觀方面,可以把這種狀態稱為是彰顯犯罪目的的狀態,而且彰顯的程度必須是達到足以與其他罪相區別[17]。而且與犯罪目的實現說不同的是,這種狀態并非要有完成某種特定的目的,不論是預期目的還是刑法規定的目的,只要行為實施達到彰顯犯罪目的,能夠讓一般理性人在觀察后,綜合客觀條件,能夠清楚行為人所意欲達到的犯罪目的的狀態即可。如果這種狀態出現之后還能繼續,并且是承繼了先前的結果,那所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害結果不應當認定為既遂或者其他停止狀態,而應當認為是結果加重犯。
舉例來說,比如綁架罪,行為人雖然已經著手禁錮了被害人,但是行為人沒有向被害人家屬勒索財物時,不可能在外部讓人了解行為人所意欲的是綁架還是一般的非法拘禁,所以只有行為人勒索財物時才能將行為人的犯罪目的彰顯出來,將人殺死這種狀態就能區分出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這兩罪,因而要求現實結果的出現才能確定犯罪既遂。再比如盜竊罪,行為人入室盜竊,在沒盜取財物前,此時犯罪目的只存在于行為人的意向中,一般人從客觀角度觀察可能無法分辨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是什么,可能是入室搶劫,可能是意欲強奸,也可能是意圖盜竊,還可能只是非法入侵住宅,但當行為人使財物脫離其所有人的控制時,盜竊的犯罪目的就已經完全彰顯,財物的取得就是盜竊罪的既遂狀態,所以可以認定犯罪既遂。再例如破壞交通設施罪,行為人破壞了火車軌道,此時行為人的犯罪目的似乎已經彰顯了,但其實不然,如果不能產生具體的危險,比如這條軌道實際上已經報廢,雖然還沒有被拆除,但不能彰顯行為人意圖破壞交通設施造成危險的目的,就只能是不能犯,因而,要出現具體的危險狀態才能彰顯犯罪目的。
通過彰顯犯罪目的狀態,且彰顯程度是足以區別于其他罪這一認定犯罪既遂的標準,我們可以避免犯罪構成要件說現有的缺陷:1.不需要以犯罪刑法分則的既遂模式為前提,刑法分則的規定可以同時作為未完成形態與完成形態的構成要件;2.避免預設各類犯罪的既遂的標準,即行為犯、結果犯和危險犯的分類,避免陷入循環論證。比如就刑法所規定的第119條第1款,不需要危害結果的出現,而只要達到第116條規定的狀態,犯罪目的就已經彰顯出來,而第119條第1款的內容可以認定為結果加重犯,這樣就確定了一個唯一的犯罪既遂標準。而且這一標準是明確的、可執行的,在司法實踐中,面對查清的案件事實,在已知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之后,再追溯案件發生時,行為人所展現出來的客觀狀態是是否能完全彰顯其犯罪目的,如果說已經完全將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彰顯了出來,也就是行為人本身的行為已經足夠認定其罪名,司法機關所查證的其他情節和證據其實只起到了佐證作用,不需要再進行推測其犯罪目的,比如小偷入室盜竊完成后,剛到小區門口就被財物所有人給抓住了,這就是盜竊既遂。
綜上所述,重構的犯罪構成要件說的基本內容是:最大程度滿足犯罪構成全部要件,最大程度是指達到彰顯犯罪目的并且足以與其他罪相區別的臨界點,未達到臨界點的是屬于犯罪未完成形態,具體是犯罪未遂還是預備需要通過犯罪停止的內容確定,在臨界點之后的是屬于結果加重犯或者是加重的量刑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