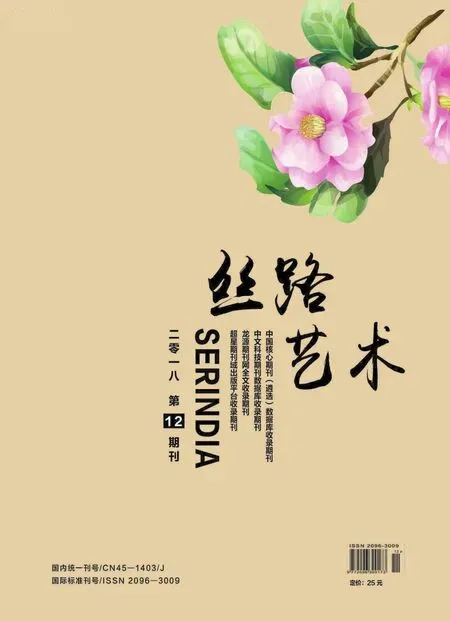英雄的葬禮,靈魂的哀鳴—論肖邦第二鋼琴奏鳴曲
吳貝妮(長沙市青少年宮,湖南 長沙 410000)
“死亡不在遠處,而是在眼前,就在當下,我們的心執著的就是記憶。”
—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
肖邦第二鋼琴奏鳴曲,為悼念華沙起義的英雄同胞們而作,夾雜在伴有喪鐘哀鳴的送葬行列之中的是平和優美的行情樂段,似回憶般溫存動人。肖二奏鳴曲中深切的痛楚以及苦痛化成的歌,撥動世人的心弦,展現了作曲家關于生與死的音樂哲學觀以及肖邦音樂特有的詩性空間。全曲點睛之處莫過于第三樂章“葬禮進行曲”,肖邦的這首葬禮進行曲深刻寫實,具有哲學思辨的高度。這個樂章刻畫的景象,如同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在《生與死的冥想》詩篇中的敘述。“死亡不在遠處,而是在眼前,就在當下”,這便是最好的注腳。
肖邦《第二鋼琴奏鳴曲》,作于1839年,其中第三樂章為著名的送葬進行曲,先作于1837年。當時肖邦在馬略卡島療養,住在喬治·桑的故鄉諾昂。1838年秋,肖邦、喬治·桑同她的兩個孩子,分別來到馬略卡島修養。“肖邦自己另走一路,很可能是為了掩人耳目”",那時,他與桑的戀情并未公開。馬略卡島多雨潮濕的氣候,當地人對肖邦肺病的厭棄以及謠傳,瓦勒德莫薩的夏爾特爾修道院,廢棄、荒涼、甚至是恐怖,肖邦肺病的加重,直至咳血不止,這一切,都成為肖邦療養時的丑陋印象。《葬禮進行曲》也正是在那里,有了雛形。1839年,二月,肖邦和桑離開馬略卡島,在馬塞短暫停留之后,于五月回到了喬治·桑的故鄉諾昂。怡人的鄉村景色,溫和舒暢的空氣,使肖邦倍感安慰,此時的他,音樂創作步入成熟期,技巧嫻熟而且頗為多產。1839年,夏,肖邦在瓦勒德莫薩草稿的基礎上,創作了這首降b 小調第二鋼琴奏鳴曲。因為包含了先前創作的葬禮進行曲樂章,而得名《葬禮奏鳴曲》。
喬治·桑曾精到描述肖邦創作此作品的歷程。“他能連著幾天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流著淚來回踱步,折斷他的羽毛筆,重復或一百次地變動一個小節,一次次寫出來再抹去,第二天在一種堅忍不拔和絕望相混雜的執著中重新來過。”
一、灼熱的愛國激情與抑郁苦楚的情懷
第一樂章,極慢板,在嚴謹歸整的結構內融入真誠的愛國熱情,賦予奏鳴曲形式浪漫的靈魂。莊嚴的引子,音響籠罩著壓抑悲憤的氣息。用呻吟般的極慢板做引子,接著用加倍的速度奏出第一主題展開部則以長氣息和小分句結合的復線條手法,將悲傷、孤寂、憤怒、執著與頑強的情感在逐層遞增的推進中一一呈現。隨后的第二主題再現與尾聲仍舊是音樂性格的截然對比,增添悲傷與抗爭的心理色彩。結束部和尾聲在增長的強力度內,將音樂中倔強與堅決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騰越突進的諧謔曲
第二樂章以陰郁開始,猶如烏云密布,狂風呼嘯的意境,慢慢的云開霧散一縷陽光照射著大地,有此樂曲慢慢轉向慢板,有如天籟般的琴聲甜美悠揚,仿佛經過復雜的思緒,憧憬美好的未來。這個奏鳴曲套曲的間奏型樂章,在音樂表現出沖動感的同時,給予音響“時間上的方向和興奮”,引導聽眾隨著音樂的展開,建立對聲音、內容、行進方向和情緒爆發的預期。中間舒緩的樂段,有著搖籃曲的歌調,不禁讓人聯想起肖邦第一諧墟曲(Op.20)中段舒緩的搖籃曲。
三、英雄的葬禮,靈魂的哀鳴
整部奏鳴曲套曲音樂氣氛和形象性格的核心,具備鮮活的描繪性與戲劇性。均衡對稱三部曲式,以其節奏、色彩和織體形式的切換,產生強烈的心理印象。而樂章中段唯美至及、溫柔貼慰的行情片段,是肖邦對頭尾兩次持續壓抑的葬禮行進片段作出的心理補償。
柱狀和弦的橫向傳導,象征著步履為艱的沉痛心情。左手為降b 小調主音到中音的小三度搖擺,象征著喪鐘低鳴。接著主音到中音的下行連接為主要輪廓,象征著絕望中的悲嘆。而連續附點節奏的上行推進,仿佛向人們展現這樣的場景:送葬人群突然躁動了起來,人民加急了腳步,抽泣著、哽咽著,被訣別的悲痛與不舍吞噬。中段的音樂整體上色彩柔和,情緒親切感人。此外,中段左右手的上行趨勢,使音樂流動悠揚,夢幻而富有希望,不同于第一部分持續的哀傷下行。中段之后是葬例進行樂段的原形再現。強烈的畫面感再一次席卷而至,聽眾在第一次呈現的基礎上,增加了熟悉感,更易于融入音樂的戲劇進程,從而獲得更強烈的音樂影像和心理感動。本樂章的結束句,聲音消散的過程沒有出現漸慢的標注,而只出現最后主音和弦音的加重和延長。肖邦并未像第二樂章的尾聲那樣,回憶起中段如歌的夢幻場景,卻誓將痛苦與絕望銘刻于心。
麻木與輕盈,僵硬與酥軟,冰冷與溫暖,絕望與尋求,停滯與流暢,掙扎與順服……肖邦細膩地刻畫了葬禮行列行進的場景,鮮活地展現了絕別時刻人們的心碎、麻木、哀慟、絕望的心理狀態。
四、悲情的深化
這個如風飄逝的第四樂章,似點精之筆,深刻了全曲的悲情效果。開始部分六連音動機中的三連音上行和三連音回轉下行,成為該樂章的運動內核。它們的并置與分裂,展開與聯結,配以淡淡的朦朧音色,呈現出特別的音樂情境。墓旁的陰風,漂泊的靈魂,瘋狂的找尋,以及無法抗拒的墜跌。音調上無穩定的中心感,音樂進行飄忽不定,難以捕捉的方向感和伸縮的力度布局,似即興的音詩,色調迷離。本樂章無窮動式的上行展現出對平安、希望和歸屬的不懈追尋,而下行則是通向絕望深淵的無奈墜跌。
舒曼評述:“這是非旋律,沒有歡樂的樂章,像是強有力的手壓抑了叛逆的靈魂,使那特別恐怖的幽靈與我們對話。”結尾像是帶著被獅身人面像愚弄過的微笑終了。”肖邦要求這個樂章要“左手與右手七七八八地齊奏同音。”尼克斯對這個樂章的評價是“葬儀之后,那邊有三位鄰居在議論已故者的為人,沒有惡意的批評,只有善意的贊揚。”而克拉拉則認為“像是秋風吹散落葉,飄落在新墓上。”
偉大的鋼琴家李斯特,在《肖邦的生活》(《Life of CHOPIN》)一書中,描述肖邦為身心細膩之人。對于此曲,李斯特這樣寫道。“我們感受到我們不只是為一個勇士的逝去而哀悼,而是一代人中所有勇士的永久消逝,把裒歌存留給哭嚎的婦人,流淚的孩童和無助的教士。”
李斯特最后說道,“最純凈、最圣潔、最值得信賴,在孩子、女人和牧師們的心中點燃無限的希望。以其不可抗拒的樂音振動,回響、震動和顫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