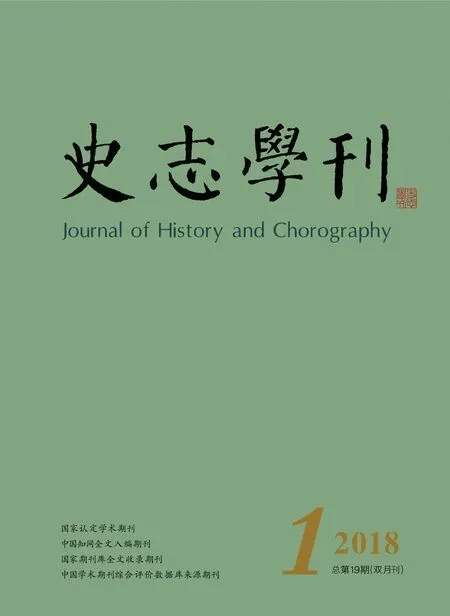“修志問道”與方志編纂思維更新
吉 祥
(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南京210004)
2017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地方志第一次被正式列入國家重大文化國策之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年也先后對地方志作了兩次重要批示,在2014年第五次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的批示中,稱“地方志是傳承中華文明、發掘歷史智慧的重要載體”,提出“修志問道,以啟未來”。2015年在對全國地方志系統先進模范座談會的批示中,提出了“直筆著信史,彰善引風氣,為當代提供資政輔治之參考,為后世留下堪存堪鑒之記述”的要求。這兩次重要批示傳遞了很多重要的新理念,“發掘歷史智慧”“修志問道”“彰善引風氣”“堪存堪鑒”等提法,較之以往地方志功能“資政、教化、存史”的表述有明顯的不同,更加強調了地方志“文以載道”,掌握社會的發展規律,總結歷史經驗智慧,引領社會風氣的作用。與這樣的理念對照,現有的地方志存在明顯的差距。30多年來,在“橫排豎寫”“述而不作”等體例規范下所形成的志書,更多的是外在體例形式上像志書,注重科學分類,而在內容上則顯得相對平庸,沒有體現出足夠的獨到價值;志書貫徹了“述而不作”的資料性文獻要求,表象事實羅列有余,深度歷史分析缺乏,只看到表象性的“是什么”,看不到歷史發生的“為什么”,無法給人以真正的思想啟迪;志書記載了組織機構及工作開展和制度的變化,而很少看到人的創造、人的思想、人的價值,基本看不出志書直接傳遞的歷史智慧;“生不立傳”帶來創造當代歷史的當代人在志書中很難見到蹤影,而已故人物的活動以及傳遞的精神與當代精神風尚形成一定脫節;很多志書真正用心探尋和反映地方發展之道明顯不足。
目前,地方志系統所開展的地方志資源開發利用,是對已出版的地方志(志書、年鑒)進行二次資源化開發利用。這種事后的以功能開發為首位的資源開發利用固然重要,但也提醒我們,為什么不能將“問道”的意識和方志利用的觀念直接前置植入地方志的編纂過程中?因此,地方志編纂有必要隨著新理念而作相應的改變。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書寫方式并不是單一的,有什么樣的編纂思維就會有什么樣的書寫方式,也就會呈現什么樣的功能價值。“述而不作”是志書的一種編纂模式,“問道”式的地方志同樣也會是一種新的編纂思維形式。這一切取決于我們自身對地方志書新的功用定位和體例規定,新的范式就有可能從理念變為現實。
一、“修志問道”需要以地情研究為前提
過去的地方志工作把編修一部省、市、縣三級志書作為主體。2015年9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頒發《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中最新提出了六個基本原則(堅持正確方向、堅持依法治志、堅持全面發展、堅持改革創新、堅持質量第一、堅持修志為用)和11項主要任務,首次提出地方志工作要修用并舉,并在“提高地方志資源開發利用水平”中還專門提出要“培育地方歷史記憶”,進行地域研究(或地情研究、地方發展研究)的內容。過去一直只是把地方志看作為資政決策、社科研究、新聞寫作、文學影視創作等提供基本資料素材,而沒有意識到地方志工作者自身所直接進行的“問道”式的地方發展研究或地情研究。
從各地的編修實踐尤其是二輪修志實踐來看,由于地方志編修走的是通過政府行政手段眾手成志而不是專家修志的方式,資料征集和初稿工作基本是在承編志書的基層和各職能部門進行,地方志專業部門并沒有直接參與第一手資料的征集,所以方志部門所掌握的基本是經過基層承編單位非專業處理后的二手資料,專業地方志工作者所做的基本是體例和行文規范方面的技術性生產,而不是內容生產。地方志專業工作部門擔負的是編輯角色,而沒有承擔第一手資料征集和研究的職能,這導致了專業方志工作者對地情研究的弱化。
地方志的編修過程本質上是“現實(地方發展或地情)—文本(方志編纂)—現實(方志利用和服務于現實)”或“地方(發展)—地方志—地方(發展)”的過程。地方志其實是對地方發展的文本記錄和投射,是記錄歷史的人對創造歷史的人的記錄。地方志要強化“問道”功能,就必須從“地方志”研究回到“地方”研究的本體上去。地方志應該是建立在地方如何發展的地情研究基礎上的自然產物,而不是相反。恰恰是由于目前地方志系統把重心停留在“編輯”上的定位問題,導致了地方志部門對“問道”地方發展的功能較差。所以,地方志要加強對地方發展決策咨詢作用,必須要把工作重心從基于他人二手資料基礎上的“編輯”,向前延伸到對地方發展基礎資料的把握和地方發展路徑的研究上來,應當要把志書看作是整個地方志工作的中端而不是終端。
目前,地方志部門強調的地方志理論研究,更多的是方志界業內關于編纂記述的技術性研究,而不是社會層面對地方志所期待的地方研究。方志工作者相當多的是將自己定位為方志行業內的“編修者”而不是社會角色意義上的地情研究者或使用者。相對于地方研究,地方志編纂研究在社會看來實在是微不足道和缺乏意義的。
方志界有人提出,地方志不僅要成為“知庫”還要成為“智庫”[1]洪民榮.地方志:既是“知庫”,也應成為“智庫”.解放日報,2017-07-18.。這個愿景很美好,但客觀地說,很多方志工作者由于沒有對地情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自身缺乏提出現實發展對策的能力,自然也就談不上貢獻什么“智”。在這方面,淮安市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荀德麟,對地情是有深入研究的,同樣他從地情研究中生發出淮安地方發展的戰略,先后提出了“三淮一體”和“運河之都”名片打造地方發展的戰略,像他這樣打鐵還須自身硬的人,在地方志系統其實是不多的。如果我們用放大一些的社會眼光來看大方志,其實每個地方都應該有一批研究地情、參與地方志編纂并能提出地方發展之道的智者(智囊)。
二、地方志“問道”的重心是揭示地方發展之道
地方是一個相對于國家和中央而言的概念范疇。地方志不是國志、國史,而是地方的歷史文獻記錄。而從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很多探索是從地方發起的,地方志要把從本地實際出發所進行的新發展、新創造、新探索、新路徑重點進行記述,尤其是地方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更是與地方發展之道息息相關。這樣編纂的志書,才真正對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有啟發借鑒意義。
我們以對應二輪修志斷限的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為例,以往的表述基本上是一場由執政黨和中央政府所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什么、如何改由中央政府說了算,任何下級政府及企業、個人如果沒有獲得上級政府的授權,是不能自發進行制度創新的[1]楊瑞龍.昆山帶給我們的啟示.中國改革,2002,(7).。由于原先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是權力高度集中于上層,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則意味著自我革命,事實上要突破自我的局限性往往是很困難的,因此,改革開放的最初歷史發生路徑往往并不是自上而下式的,而恰恰是呈現為從體制外部沖擊體制內部(或是以對外開放拉動對內改革)、體制內部地方和民間底層的“以下犯上”和“自下而上”的制度突破。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就是一個改革開放“自下而上”成功突破的典型案例[2]吉祥,徐秋明.書寫可理解的歷史:歷史發生與指數編纂的理念——以昆山經濟開發區及指數為樣本的案例分析.第二屆中國地方志學術年會“第二輪市縣志編纂及其理論問題”會議材料,2012.。1984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三個特區,國務院增設特區辦公室,全國出現第一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央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為昆山的決策者們打開了思路。昆山人大著膽子仿照沿海開放城市創辦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做法,自費開發建立工業新區(1988年6月更名為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在自費開發過程中,他們突破開發區一沒上級批準、二沒資金來源、三沒有任何優惠政策,白手起家的重重困難,發揚率先創業、率先開放、率先改革、率先發展的精神,大膽闖、大膽試、大膽干,勇于實踐、敢為人先,在全國、全省創造了眾多第一,昆山開發區的綜合經濟實力位居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前列。昆山建設自費開發區是改革開放中一個比較突出的自下而上實現制度突破的案例,成為向全國推廣建立開發區的一個重要模式,對全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之路提供了一個樣本。
再以《中國名鎮志文化工程》為例,這套叢書的定位不應該只是各名鎮的名片性質的社會普及性宣傳書,還應當承擔這些名鎮在中國農村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的示范啟迪作用。以這套叢書中的《周莊鎮志》[3]中國名鎮志文化工程·周莊鎮志.方志出版社,2016.為例,我們反復思索周莊鎮在全國歷史文化名鎮以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何在,為此在《周莊鎮志》中設置了周莊古鎮保護模式、周莊旅游開發模式,把周莊放在江南水鄉的地域背景下橫向考察,揭示周莊模式的發生路徑、特點特征以及所產生的全國性、全球性的示范推廣意義及其價值所在。再以這套叢書的《巴城鎮志》為例,我們同樣設置了專題調研報告《巴城:現代農業模式的新型城鎮化樣本》,我在該報告中,總結了該鎮農村空間布局中的新型社區化、農村經濟管理模式中的新型集體化、產業化經營的現代都市農業模式等特征,將巴城鎮放在昆山市基本現代化的整體布局中,揭示巴城鎮融生態、生活、生產的現代化“三生農業”在基本現代化中的位置,指出其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的結合對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路徑所具有的重要啟發意義。志書中這種對地方發展之道的探索,就是典型和直接的“修志問道”。
三、從“述而不作”到分析性記述
要發揮志書“問道”的功用,必須要改變“述而不作”的歷史編纂書寫方式,加強深層化“分析性記述”的方法運用。所謂分析性記述,并不是空發議論,而是基于歷史事實、歷史數據,對事實發生的源頭起因、動因做客觀的記述,對社會現象作結構性的分析,并將產生的后續影響作關聯性的記述。對歷史記述要賦予歷史的洞察力、思辨力,客觀合理地分析。這樣書寫的歷史才是可理解的歷史。
從首輪新方志編修開始,“述而不作”就是地方志編修的一條基本原則。“述而不作”出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言說,其本義是遵循圣人之道而不改創,這種著述理念源于古人原道、征圣、宗經思想[1]郭明浩,萬敥.“述而不作”與中國闡述學建構.云南社會科學,2012,(6).。清代章學誠對“述而不作”思想進行闡發時曾經說道:“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唯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也。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為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于后也。”[2]章學誠.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聯系到章學誠的“志乃信史”“文人不可與修志”的言論,可以看出,章學誠對“述而不作”的理解主要表現在學術撰著與文學創作的區別上,史志撰著中的“述”必須都應該有歷史依據而不能憑空改創。與撰史相反,文學創作則不能守舊僵化,蹈襲前人,而應提倡創新。作為方志學的鼻祖,章學誠的這種理論并沒有錯,但是“述而不作”的學術原則到了新方志編纂過程中則被廣泛解釋為志書只需要客觀記述而不加以分析評論。這種對“述而不作”的闡釋相當程度上已經背離了這句話的本初意義。
歷史事實是不可以憑空杜撰的,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一直都有以敘述事實為主的史書范式和風格。從文化觀念史的角度考察,“述而不作”的傳統在中國社會有著特定的背景。中國的傳統政治生態環境是一種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專制制度,它所生成的是維護統治者的專制文化思想,專制思想對社會個體獨立精神的扼殺,使整個社會的思想精神出現萎頓狀態。因此獨立精神人格的史家在記載歷史真相時需要冒著生命風險。早期的史家出現了司馬遷受宮刑及史官被殺的情形,后來進而演化出大多數文人的精神自宮,這種狀況在清代文字獄發生后尤為明顯。由于志書記述內容的當代性,加上修志是一項政府行為,需要體現政府的意志,保持與統治者的思想精神的一致性,這些局限性導致了志書對當代的隱諱,社會的潛規則很多時候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說,或者是需要婉轉、隱晦地說而不能直截了當、開門見山地說,凡是“當代”性質的史書只寫事實不作分析評論的比比皆是,因此“述而不作”其實并不只是修志的一個準則或文化現象,而是整個傳統史學的一個共同文化現象。
與中國的考據史學傳統相近,西方近代史上也曾經存在德國蘭克學派。蘭克學派的史學基本思想是追求純粹客觀的歷史,認為史學寫作的目的在于復原歷史,要達此目的,最重要的是找到原始資料,用史料說話,不偏不倚、如實客觀地再現歷史的真實性,因此這個學派極其重視原始資料的利用和考辨。但是這種史學思想由于過分注重對事實的描述,排斥了概括、解釋和理論,忽視歷史學家主體意識的作用,后來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現代史學的批判和拋棄,新的史學不再是純粹的客觀敘述,而是出現了分析性的史學范式,歷史學要求必須體現對歷史的闡釋能力。
而在中國,史書也從來就不只是“述而不作”的客觀事實敘述,同時也存在著對歷史的認知。翻檢中國歷史上的舊方志,也從來就不是只有記“是什么”和“不作”的單一記述模式,同樣也有分析評論的志書,很多方志學著司馬遷《史記》“太史公曰”的筆法書寫對歷史的見解。
回過頭來看首輪修志的實踐,我們可以觀察到,由于“述而不作”編纂思想所賦予的秉性,志書呈現了兩種特征,一個特征是“述”的淺層化、表象化,只寫了“是什么”,根本看不出“為什么”,人們所看到的志書幾乎是沒有思想生氣的,只有“冷冰冰”的板著面孔書寫的機械的事實,而看不到地方志豐富“正史”所應該具有的豐富表情和值得回味的歷史細節,看不到編纂者在記載地方發展時所應具有的思考和價值判斷,無法給人以直接的啟迪。有人指稱“述而不作”至少有“是非不明”“因果不彰”“規律不見”“真假難辨”等四大弊病[1]諸葛計.新方志五十年史(稿).在方志思想和理論方面的若干探討.。地方志要贏得社會關注和共鳴,迫切需要解決這一記事原則的禁錮。另外一個特征是對“述”和“作”的片面理解,認為志書要加強著述性,但只可以在概述和無題序中作分析議論,在這種思想片面理解下,志書強調整體性的記述風格,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在這種風格下編纂的方志漸漸失去了更加實在具體的資料存史意義。
針對志書“述而不作”的弊端,一些方志人提出了“述而有作”“述而精作”“述而略作、作必合道”等理論,并基于方志是資料性著述的理解,提出了“如果說真實性、資料性是新方志的生命,那么著述性則是方志力量和價值、是新方志活化的生命”的見解[2]胡嘉楣.加強方志著述 提高志書質量.黑龍江史志,1989,(4).。但是真正將這些理論付諸志書編修實踐的極少。
2006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省《龍巖市志》(1988—2002)其中運用了不少分析性的記述。如該志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運行”[3]龍巖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龍巖市志(第二十編財政稅務第一章財政第二節財政體制).方志出版社,2006.(P871-872)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范例,該記述不是停留在過去的只寫“是什么”的事實表象層面,而是既寫了事實,也對新的體制運行出現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結果效應及其社會運行中的矛盾、困難、問題作分析,其中所蘊含的為龍巖的困境鼓與呼的政策憂患色彩表露無遺。從方志編纂的角度而言,《龍巖市志》中的這一段分析性記述就是觸及本質的“修志問道”之作。這種分析性記述的意義在于,展示了深度的歷史,觸及了地情與歷史中本質性的內核。
地方志總體來說是一種記述性文體,不提倡空發議論,但采用記述體并不表明只能寫“是什么”,而不能寫“為什么”。恰恰是那些寫為什么式的分析性記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發展的動因和歷史的走向,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讓歷史變得可以被理解。地方志要發揮更大的人文意義和歷史借鑒價值,寫出“為什么”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第二輪修志記述的時段是中國社會結構發生大轉型的時代,社會運行中的矛盾以及社會價值觀念非常復雜,準確地把握這個時代就要求我們的方志編纂者必須要有基本的分析判斷。分析性記述的志書寫作,其意義不是單純宏觀層面的“資政”作用,而是對每個社會個體都具有普遍的啟迪意義[4]吉祥.突破“述而不作”的禁錮:分析性記述范式的運用——《龍巖市志》文本分析及二輪修志理論創新的思索.江蘇地方志,2008,(1).。
地方志中分析式記述方法,除了在正文中運用外,還可以通過創新體例用新的形式加以呈現,如“匯考”
“專記”“調研報告”以及鏈接。
四、發掘歷史智慧要重視人的思想精神入志
李克強總理指出地方志要“傳承中華文明,發掘歷史智慧”,什么是歷史智慧?智慧是升華到精神層面的東西,這種智慧有些是經驗之談,有些是獨到的思想。精神層面的東西是否需要入志?如何入志?
中國古代對歷史文獻的記載有多種形式,早期的史官有記言和記事的分工,即《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尚書》和《春秋》,一為記言,一為記事,言事分記。后代的史書和地方志均偏重于記事,而對記言有所弱化。在新編地方志中,普遍重視記載歷史活動和物的一面,而對精神的一面除了藝文和民俗有所收錄外,其余對人的精神世界很少記及。由于現代社會結構的變遷,地方志從舊志普遍重視人物傳到新志普遍重視組織機構而弱化個體人物的記載,且對人物的記載多限于其業績方面,對其主觀精神世界的言論、思想主張很少記及。
在歷史上,發揮歷史借鑒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史學著作當首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里面收錄了不少治世經典之語,如“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是之謂大丈夫。”“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這些經典言論充滿歷史的智慧,清人王鳴盛評價《資治通鑒》:“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歷史上的很多統治者都是從中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這種人的思想精神和智慧在志書中不是要不要記,而是怎么記。古代的史志中,一般都是針對人物,將“言”“事”結合。浙東學派的史家強調“即器以言道”,提出道器合一,反對空言義理[1]林勤藝.章學誠之經世致用.環球人文地理(評論版),2016,(9).。在人物傳中,杰出的人物可以結合其活動將其富有見解的主張言論“以事系言”“以人系言”。首輪新方志中浙江《紹興市志》專門設置“名家學術思想卷”[2]紹興市志(卷32名家學術思想).http://killusoftly.bokee.com/6826592.html.,每一名家介紹其主要理論觀點,以一斑窺全豹,從中了解紹興歷史上學術研究的主要成果,這些名家的學術思想產生于現實生活,又直接為現實的需要服務,在中國歷史上閃耀著光芒。
在我主編的《中國名鎮志文化工程·灣頭鎮志》中,針對該鎮玉器特色產業設置了“玉器濫觴”,其中又針對若干玉器工藝大師設置了“玉工匠心”,每個大師都介紹他們的業績、創作榮譽外,還收錄了他們對治玉的理解,如鑒玉大師劉月朗下有他的一段話:
人們都說“黃金有價玉無價”,但我以為玉也是有價格的,無論是每公斤數十萬還是數百萬,都始終有談定的價格。真正做到無價的是工藝。就像是一幅名畫一樣,作畫的紙墨都可以價格量化,但這些廉價的工具一經大師之手,凝聚了大師的藝術結晶后,就可能成為無價之寶。張大千的畫為什么能夠拍賣到數千萬乃至上億的價格?不是他用的紙墨多名貴,而是他的藝術價值珍貴。同樣的,玉雕就材質本身,現在也已經可以稱得上名貴了,但這還不夠,一塊上乘的玉石只有經過大師的工藝塑造,達到藝術上的升華,才可能會真正做到流芳百世,長存不朽。所以我說應該是“金玉有價藝無價”才對。
除了人物和學術思想外,地方志中的思想智慧還可以表現在家譜家訓的記載中,那些優秀的家訓家風恰恰是今天社會需要弘揚光大的。
五、“問道”要重視“細節之道”
劉延東副總理在第五次全國地方志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志書“還要精益求精,不放過每一件小事,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細節里可能蘊含有一些重大的突破。當然我們還要重點突出整個歷史脈絡,但歷史發展過程中一些細節的東西,看起來是小的東西,也不要把他遺漏。”
仍以昆山經濟開發區為例,昆山開發區的見證人宣炳龍曾對采訪他的研究者這樣說過:“目前研究改革開放30年的東西蠻多的,但是缺少對于艱辛歷程的展示。開發區的幾次重要的決策,無論是決策者、操作者、建設者,都面臨不同的困境和抉擇。研究中國的開發區,不研究昆山開發區肯定是個缺憾,研究昆山開發區不寫出昆山開發區的特殊性也是一個缺憾。有些記者、專家來昆山采訪、調查后寫文章,成績和原則好寫,但缺少可資借鑒與操作的過程和細節。……今天成績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總結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幾條經驗、幾個原則就能說清楚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大家都做,為什么昆山行?因為昆山市經過千辛萬苦的過程和千頭萬緒的細節做出來的。這些不講清楚,人家當然無法學。”[1]鐘永一,張樹成編著.宣炳龍印象.見證中國第一個自費開發區.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P104-105)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歷史發展有必然性規律,但是就歷史的具體發生而言,則是由很多小事件和歷史細節觸發的。在某種意義上,細節決定了歷史最初發生的走向,引爆了大歷史。同時也正是那些歷史的瞬間、故事、細節,使歷史變得生動起來,觸發我們的情緒,產生歷史的情緒共鳴。由于缺少對歷史細節的記載,以往的志書顯得枯燥乏味。《昆山經濟開發區志》的編纂特色之一是在主體章節后附了不少歷史細節特寫的資料鏈接,如第二章自費開發中鏈接“一碗面做活三篇文章”“費老的關懷”“宣炳龍的三個小故事”,第五章親商服務中鏈接了“親商更要富商 富商引來萬商”“優惠政策不如優質服務”“親商實錄”,第六章招商引資中鏈接“第一家臺資企業的來歷”,第十一章黨群工作一體化中鏈接“陳慧芬和她的‘融和工作法’”。此外在若干正文中也重視細節的記載,如1992年李鵬總理在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發展規劃座談會上講話細節,江蘇縣級興辦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昆山中國蘇旺你有限公司的艱辛過程,江蘇省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成立的真實背景,全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是如何從概念的提出到花了三年跑國家8個部委突破重重困難把不可能的事辦成的艱辛過程。在這些細節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昆山人在發展中踏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歷經千難萬險謀發展的“四千四萬精神”。正是這些歷史細節告訴我們:昆山開發區何以能夠成功。與這些細節的歷史書寫相關,該志還有一點值得稱道的是重視口述史資料的運用,其中不少資料來自于主持開發區實際工作二十余年的開發區負責人宣炳龍的口述史資料[2]宣炳龍印象(第二編).見證中國第一個自費開發區.宣炳龍的口述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昆山經濟開發區志》對昆山開發區從自費開發到創新發展的歷史發展路徑、發展理念以及實踐的細節處理,其意義在于揭示了昆山之路是可感、可學、可借鑒、可引發思考的發展樣本。
現在很多人說要“講好中國故事”,但是很多地方志編修者長期受體例規范的影響,只知道往“里”收,用中觀的筆法泛泛地記述或概述,而不知道對微觀的敘事描述,不會講故事,細節中的微妙之處揭示不出。目前,一些地方志機構開始拓展口述史影像志,而口述和影像恰恰需要若干細節和故事構建。“道”不是抽象的,地方之道就是細節之道。這種歷史的細節可能恰恰是地方發展之道的獨到之處。李克強總理批示中提到了歷史智慧,這種歷史智慧很多是人物個體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所展現的。
結語
《地方志工作條例》將志書的本質界定為“資料性文獻”,筆者認為,志書的功能不僅在于分門別類地保存地方資料文獻的存史功用上,還應該有更高的追求,追尋歷史發生的時代精神和思想理念。
長期以來,地方志受固有的編纂理念的束縛,自我局限于編輯層面的體例規范,而沒有著眼于地方發展和地情的研究,沒有積極地體現出史志者的歷史認知。對于地方志來說,“存史”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著就不可以“問道”。這種基于地情研究的“問道”,體現的是對歷史發展的洞察力和編纂者的價值判斷,考量的是對時代和地方發展的“史識”。從某種意義上,志書最重要的編纂思想就是揭示時代和歷史本身是如何思想的,時代的精神靈魂同樣是志書的編纂思想靈魂。對時代和地方發展的認知體現的就是“問道”。笛卡爾曾說“我思故我在”,將這種哲學思維投射到修志過程中,同樣也是修志者思考所在、問道所在及志書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