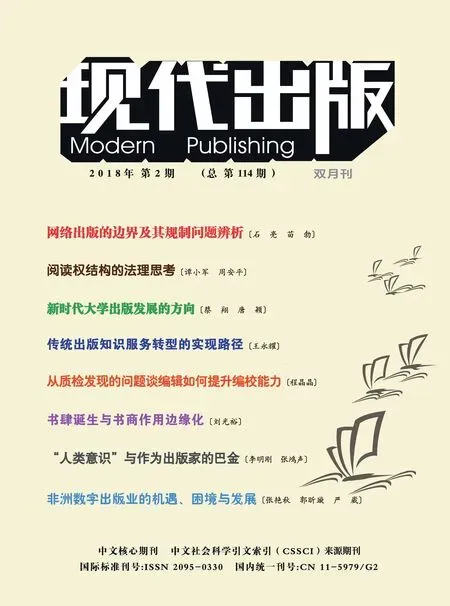書肆誕生與書商作用邊緣化
◎ 劉光裕

中國古代書肆誕生于西漢后期,與書肆同時誕生的還有書商。事實說明書肆誕生后,人們獲得書籍最普通、最常見的方法仍舊是自己“寫書”。漢代所說“寫書”意為復制作品,一般代表制作書籍(寫本)。讀者自己“寫書”,就是讀者制作自己所需書籍。書商在漢代誕生后,他們做什么,怎么做,首先不取決于書商自己,而取決于客觀存在的社會環境。早在書商誕生以前,隨著以重農抑商為國策,特別是推行壓制商人的“市籍”制,全國職業商人早已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成為名副其實的邊緣群體。與此同時,社會上自給自足經濟不斷發展,不斷完善,根深蒂固。因此,書商自誕生那天起,就與其他商人一樣成為處于邊緣地位的、身負“市籍”的賤民群體與“下等公民”。身處社會最底層的書商,失去了與士大夫平等相處或交往的起碼資格。在“市籍”制的重壓之下,書商的社會權利與人身自由被剝奪殆盡,他們沒有條件與能力自己建立作坊從事書籍生產,也沒有條件與能力從事新書發行。擁有作坊從事書籍生產的不是書商,而是士人。士人所辦作坊生產的書籍都以自給自足為目的,不以商品交換為目的,不可能交給書商去牟利。因此,書商不掌握也不可能掌握作坊生產的任何新書資源,由此決定他們不可能從事有關新書購買、倉儲、銷售等現代書商所做的發行業務。而且,不只漢代書商如此,到唐代還是如此。對漢唐書商來說,現代書商那種發行業務,他們上千年一無所知,聞所未聞,既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他們的書肆業務主要是買賣舊書,為社會上冗余之書調劑余缺,互通有無。這就是本文所謂“書商作用邊緣化”。在自漢至唐的書籍出版活動中,書商作用邊緣化與讀者傳寫成為書籍流通的主渠道是相互關聯的兩件大事,也是影響最為深廣、最具代表性的兩件大事。
一、書肆與書商產生于西漢后期
在我國歷史上,西周商業都是官府經營的,商人都是官奴。東周以來,主要是戰國至秦漢年間,私營商業蓬勃興起,涌現出許多著名商人,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商品經濟繁榮時期。在這次商品經濟繁榮中,書籍并未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也沒有產生書肆。我國最早書籍是官府典籍,如誥命文書、典章文獻、國家史籍、諸侯史志等,此外還有術數等具有神秘性的宗教書籍。這些書籍稱為官書。凡官書,一概由官府典藏,不準公之于眾,不準公開流通,由此決定官書不可能成為商品。迄今為止,我們找不到先秦存在書肆或書籍買賣的任何資料。有關秦始皇焚書的資料中,未有一語涉及書肆,說明秦代社會還沒有書肆這類事物存在。若有書肆,秦火豈有不焚之理?
先秦官府對市場的管制非常嚴厲。《禮記·王制》列出禁止進入市場的兩大類物品。一類是質量不可靠者,如“五谷不時”“果實未熟”等。另一類是代表貴族與官員享有等級特權的器物,如“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戎器”等。孔穎達疏曰:“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王制》在此沒有提及書籍。擁有官書,在西周是天子的特權,在春秋戰國是諸侯的特權,連貴族私家都不準隨便擁有。官書若進入市場,至少也是“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這樣形成了書籍不能買賣的觀念。不只官書不買賣,連后起的子書也不買賣。這或許是書肆遲遲不能產生的主要原因。
至西漢,一方面是惠帝年間“除挾書律”,國家鼓勵私家藏書,鼓勵書籍自由流通,古今書籍紛紛在社會上流布;另一方面是文化教育大發展,公眾對書籍的需求迅速增長。這樣,將書籍用于商品交換的客觀條件逐漸成熟起來。
河間獻王劉德,“從民得善書,必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加金帛賜以招之”的“賜”,是劉德居高臨下的賜予,與市場上的商品交換不是一回事。可是,通過“賜”的名義,曲折地表現了書籍具有可以用“金帛”交換的一種價值。
據《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注:識,記也。),具作其事。后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張安世是西漢名臣張湯之子,事武帝、昭帝、宣帝數十年,卒于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張安世“購求得書”之事,聯系他生平考察大概在武帝晚年,即公元前二世紀末或公元前一世紀初。《說文·六下》:“購,以財有所求也。”張安世如何“購求”不得而知,不過他與劉德“賜”金帛已有不同。既為“購求得書”,必定是用財物通過某種途徑交換得來的,已屬于商品交換范疇的行為。
從上面兩例,尚不能完全斷定武帝或昭帝年間已有書肆或書籍市場,然而可以認為書籍商品交換的社會條件已趨成熟。
我國最早的書肆資料見于揚雄《法言·吾子》。《吾子》的主旨是崇本抑末,崇本就是尊儒。其中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軌注: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李軌注: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這句話的意思是,愛好讀書而不折中于孔子,就像賣書于市肆而不懂書中意思的書商;好發議論而不折中于孔子,猶如敲出小聲的鈴鐺而不合乎大雅之音。如今許多人把揚雄這句話理解為書商博學。這樣的理解,與作者原意南轅北轍,肯定沒有讀《吾子》原文和李軌的注。揚雄,字子云,西漢著名學者,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據陸侃如教授考證,《法言》大約作于西漢平帝二年,即公元2年。在《法言·吾子》中,“書肆”是用于修辭的比喻。既為比喻,可知這時候長安士人都已知道市場上有賣書于市而不能釋義的書商。由此看來,長安書肆必定產生在《法言》之前。再聯系張安世“購求得書”是在公元前二世紀末或公元前一世紀初,可以推斷長安書肆誕生在公元前一世紀后半葉,具體年代難考。西漢京城長安是當年中國最大城市,有八萬余戶,人口二十四萬多。長安又是全國文化中心,元帝年間長安有太學生上千人,成帝年間增至三千人,另有大批文人學者聚居于此,故而長安最早出現書肆并不奇怪。
中國書肆誕生于長安市場,那么漢代的長安市場究竟是怎樣的?
西漢長安有兩個市場,即東西市,此外再無別的市場。長安商販都集中在這兩個市場營業,白天開市,晚間閉市。長安市場的四周筑有圍墻,以將市場與居民區、行政區隔離。圍墻上有數道門與外界相通,開市才開門,閉市就關門。管理市場的行政機構稱“令署”,設于懸掛醒目旌旗的市樓上,對商販進行晝夜嚴格監管。班固《西都賦》描述長安市場說:“九市開場,貨別隧分。”長安的西市由六市組成,東市由三市組成,故稱“九市”。“貨別隧分”的“隧”,《文選》李善注引薛綜曰:“隧,列肆道也。”可知市場內道路,稱“隧”。班固這話意思是東市、西市開場營業,不同的貨物由一條條街道(隧)區分開來。在長安市場上,經營同類貨物的商賈聚集在相鄰街道上。店肆是商賈居住與營業的場所,如《三輔黃圖》說“周環列肆,商賈居之”。“肆”本是陳列的意思。店肆排立在“隧”的兩旁,故稱“肆”或“列肆”。孤立的一家商店,一般不可稱肆。
由此可知,長安市場是與四周居民完全區隔,由“令署”晝夜嚴格監管的封閉市場或非自由市場。長安“書肆”就在這長安市場(東市或西市)內。除此之外,長安其他地方并無市場,也無書肆。此其一。其二,既稱“肆”,書商就不能是一家,必定有數家或多家,如班固所說“貨別隧分”。因此,這“書肆”是書籍市場,即書市。兩漢書肆,或在長安,或在洛陽,基本情況都是如此。一直到唐代,書肆的基本情況仍是如此。古代商人有行商、坐賈之別。“書肆”為書商中坐賈。漢代書商是否另有行商,尚無資料可證。
二、商人階層成為重農抑商的犧牲品
書商最初誕生于長安市場,時間是西漢后期。要了解書商誕生之后可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必須知道在書商誕生以前,漢代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早已成為重農抑商政策的犧牲品,淪為社會生活中的邊緣群體。
西漢推行重農抑商,客觀說來并非偶然,它是我國古代輕商傳統與西漢初年社會情況相結合的產物。西周商人都是官奴,我國社會上一直存在輕商觀念。先秦諸子在思想觀點上各有不同,然而輕商賤商是他們共同的看法。儒家講仁政民本,重視人數最多的農民,也不忽視手工業者,可是儒者視商業為賤業,不屑與商人為伍。法家講耕戰,重視農業與農民,敵視商業與商人,一向主張殘酷打擊商人,以利于富國強兵。先秦子書很多,重商者唯《管子》一家。秦漢年間出現了比戰國時期更大的商業繁榮。可是在西漢初年,全國自耕農數量銳減。自耕農是賦稅的主要來源,也是士兵的主要來源。自耕農數量銳減,削弱國家統治的基礎,造成社會不穩定,不能不引起政治家與士人的憂慮與不安,結果朝野輿論都將自耕農銳減的原因歸之于商業繁榮。在人們的思考中,竟沒有找到商業繁榮與社會穩定的兩全之策。戰國末年以來,社會上重農抑商的呼聲不斷高漲。秦代法家掌權,故而打擊商人最堅決,無情壓制商人的“市籍”就產生在秦代。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而困辱之”;惠帝年間又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與秦代相比,西漢對商人與商業的打擊更苛嚴,制度上更完備。
漢代推行重農抑商,主要始于西漢武帝年間,大致有以下三方面措施。其一,通過鹽鐵專賣、國家干預等措施,嚴格限制商品經濟的活動范圍。其二,通過“算緍”“告緍”將商人財產剝奪殆盡,結果全國中等以上商人大都破產(《史記·平準書》:“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其三,繼承秦代“市籍”并加以完善,成為無情壓制與歧視商人的一種社會制度。當局規定凡職業商人都有“市籍”,稱“入籍”;凡“入籍”的商人,子孫皆有“市籍”,不得更改。在政治方面,惠帝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之后,景帝再次明確“有市籍不得宦”,東漢光武帝重申“商賈不得宦為吏”。從西漢到東漢,嚴禁商人入仕,嚴禁商人子弟進官學讀書與參加選官。在經濟方面,規定“有市籍者”及其家屬不得占有田產,違反者“沒入田僮”,田產沒收。人身方面,漢高祖劉邦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到后來,發展到令商人穿歧視性服裝,如《晉令》:“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命令商人穿這種奇異服飾,目的是賤商卑商,視商人為另類。
當重農抑商成為國策之后,必然要演變成為社會制度,“市籍”就是旨在壓制商人以實現重農抑商的制度性規定。與抑商的其他措施相比,“市籍”制對職業商人的打擊是最致命的,也是最持久的。它公開剝奪商人的政治權利、教育權利、置田產權利,從而將職業商人完全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成為社會成員中名副其實的賤民或另類。只要“市籍”存在,商人就成為不享有社會權利、沒有人格尊嚴的“下等公民”;而且“市籍”是子孫世襲,所以商人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市籍”制自漢經唐到北宋年間才廢除,在社會生活中留下了卑商賤商的深刻烙印。
在古代經濟史上,西漢重農抑商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經濟史學者評論說:“它使初興的職業商人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其打擊面之廣,程度之深,通中國歷史大概無出其右者。它對商人與市場的影響,也絕不只是一時的挫折而已。這次打擊,使商人的力量驟然衰落,長時期內一蹶不振,并且在以后數百多年內一直未能恢復此前之盛況。它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標志著中國市場史上第一個高漲期至此畫上了一個句號。”漢代政治家在處理文化問題時,特別是處理尊儒后與儒家對立的諸子異端時,顯示了政治家非同尋常的胸懷氣度與遠見卓識,表現了運用政治藝術的沉著、老練與靈活。可是,漢代政治家面對生機勃勃的商品經濟與市場時,毫無駕馭能力,個個驚慌失措,處處顯示自己的偏見與短視,束手無策與感情用事,最終將蓬勃興起的商品經濟完全扼殺。士大夫無不是扼殺商品經濟的倡導者與支持者,像司馬遷《平準書》那樣對商品經濟厄運兼有同情之心者實乃鳳毛麟角。
書商誕生以前,職業商人早已在社會生活中邊緣化,淪為另類與賤民。書商誕生后,他們與其他商人一樣也有“市籍”,同屬不享有社會權利、沒有人格尊嚴的賤民與另類。在書籍領域,作者與讀者都是士人;在社會上,士人是地位最高的精英群體。書商身受“市籍”重壓,他們與士人之間,地位相差過于懸殊,故而連與士人平等相處或交往的起碼資格都沒有。書商根本不可能像現代書商(出版者)那樣成為溝通作者與讀者的橋梁與中介,也根本不可能像現代書商(出版者)那樣處于書籍出版活動的中心地位或核心地位。從重農抑商的嚴酷環境看,出現“書商作用邊緣化”是不可抗拒的,是命中注定的。
三、士商對立與自給自足書籍經濟
一般說,有重農抑商,有“市籍”制,就有書商作用邊緣化。除此之外,社會上還存在兩個造成書商作用邊緣化的因素:一是士商對立,另一是自給自足書籍經濟。這兩個因素,歸根結蒂也源于重農抑商。
漢代社會的階層結構,大致是按“士農工商”這個次序建立的。在這樣的階層結構中,商人處于最底層,士人處于最上層。重農抑商特別是“市籍”制,迫使職業商人淪為世襲的賤民與另類,成為不享有社會權利、沒有人格尊嚴的“下等公民”。在此同時,士人的社會地位在尊儒中又得到進一步提升,成為既掌握知識又掌握權力的社會精英。在重農抑商與獨尊儒術的共同作用下,士人與商人牢固處于階層結構的兩極:士人作為精英群體居于最上層,商人作為賤民群體處于最底層。
當年積極鼓吹并支持重農抑商的恰恰就是士大夫。先秦諸子早已將商品經濟與保護農民、穩定農業對立起來。西漢初年,朝野討論農與商的關系時,多數人認為發展商品經濟必然引起農業破產與社會不穩定,于是士大夫紛紛充當聲討商人與商業的急先鋒。像賈誼、晁錯那樣頭腦清醒的政治家,都以嚴厲言辭歷數商業繁榮的罪過,大聲疾呼重農抑商。政治上尊儒的結果,不是削弱而是強化了士人頭腦里的重農抑商觀念。漢代以來,中國士人崇尚文化,倡導中和,為民請命,代民立言;可是在商人與商業問題上,他們皆為賤商主義者,鮮有例外。在古代,重農抑商之所以成為長期實行的一項國策,“市籍”制之所以延續上千年而不改,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士階層的全力支持。
在士人看來,商人沒有文化和道德,乃藏污納垢之徒,歧視與壓制商人是理所當然。如此在士人與商人之間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隔閡與對立。士與商對立,首先源于重農抑商的治國理論,在觀念上則表現為士人瞧不起商人。揚雄在《法言》中偶爾提到一次“書肆”,就用了賣書于市而不懂書中意思這樣的輕蔑口吻;這種輕蔑口吻,說明揚雄心里瞧不起書商。這并非是他個人特有的觀念,而是士人的共同觀念。士人秉持賤商主義,瞧不起包括書商在內的所有商人,所以士商對立是一個階層與另一個階層的對立。這在今天看來與情理不合,也難以理解,可是在古代是千百年存在的客觀現實。
從漢代開始,書籍領域成為士人的世襲領地。在書籍生產與流通中,士人都居于主導地位或主宰地位。士人從事書籍生產,無論辦作坊還是個體作業都很自由,也很容易,至少并非難事。可是在士商對立的社會上,身負“市籍”的書商要自辦作坊從事書籍生產,一是書商自身不具備這種能力,二是社會客觀條件不允許,所以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古代書商自辦作坊從事書籍生產之事,不可能出現在漢代,晚唐的書商作坊尚是不成氣候的零星現象,最早要到北宋年間廢除“市籍”之后才出現。士商對立因為根植于重農抑商與獨尊儒術,根深蒂固,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不可完全消解的一個死結,故而書商邊緣化也成為中國古代書籍領域不可完全消解的一個死結。“市籍”制廢除以后,書商作用邊緣化有所緩解,然而并沒有完全消除。
再看自給自足經濟對書商作用邊緣化的影響。經重農抑商的重拳打擊之后,戰國至秦漢年間出現的第一次商品經濟繁榮,到西漢初年就宣告結束了。我國商品經濟由衰轉盛的第二次繁榮要等上千年之后,直至北宋年間才出現。重農抑商完全扼殺了我國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進一步鞏固并發展了自給自足經濟。從此,農業是小農經濟,手工業是個體經濟,連世家大族的莊園也是莊園經濟,自給自足經濟堅如磐石,穩如泰山。
書肆誕生以前,重農抑商早已獲得成功,我國社會上早已成為自給自足經濟的汪洋大海。在書籍領域,為適應文化教育大發展的需要,書籍生產與書籍流通不斷發展,于是造成漢代書籍經濟持續繁榮的景象。可是漢代的書籍經濟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經濟,不是也不可能是商品經濟。
經濟學所說自給自足,指生產不以商品交換為目的,而以滿足生產者自己需要為目的。考察漢代書籍經濟是否是自給自足經濟,不能從書籍流通入手,只能從書籍生產入手,考察書籍生產的目的是怎樣的。
漢代書籍生產有兩種方式:一為作坊生產,一為個體作業。官府藏書機構與民間藏書家都擁有自己的書籍作坊。西漢武帝年間既“建藏書之策”,又“置寫書之官”。前者是建立藏書機構,后者是建立書籍作坊。兩者同時并舉的原因在于,朝廷藏書機構所藏之書都是朝廷作坊生產的。自漢至唐上千年,朝廷藏書機構所藏之書皆由朝廷作坊生產,此等書籍都不用于商品交換,只供朝廷藏書之用(我國朝廷作坊生產的書籍第一次向公眾出售是馮道刊刻《九經》,時間是唐以后的五代),這樣的書籍生產以滿足生產者自己需要為目的,是典型的自給自足書籍經濟。民間藏書家作坊中生產之書,同樣不以商品交換為目的,只供自己藏書之用。漢代書籍生產的另一種方式是太學生從師“寫書”這類個體作業。學生所“寫書”也僅供學生自己使用。無論以哪種方式從事書籍生產,都不以商品交換為目的,只供生產者自己使用,所以都是自給自足書籍經濟。
這里需說明,漢代書籍生產并不與市場完全隔離,它存在與市場關聯的事項。在書籍生產三要素(作品、書籍材料、作品復制)中有兩項,即書籍材料與作品復制,都可以從市場獲得解決。書籍材料以簡策為主。《居延漢簡》(五五·五):“出錢六十,買槧二百。”槧,是用于書寫文字的三尺長木板。這表明邊遠地區集市上有簡牘買賣。由此推知內地文化發達地區的集市上,也有簡策或簡牘買賣,或許數量更多。關于作品復制,就是所謂“寫書”。當人們自己“寫書”有困難時,可以雇請“傭書”代勞,班超與闞澤的“傭書”可證。漢代以來的“傭書”者,多為中下層士人或沒落貴族。“傭書”的“傭”,繁體為“傭”。《正字通》:“傭,雇役于人,受其直(值)也。”古代凡稱傭如傭工、傭夫、傭耕等,也包括“傭書”在內,都是雇傭勞動。現代經濟學早已將雇傭勞動視為勞動力市場的組成部分。可是在我國古代,因為未有勞動力市場觀念的緣故,不將雇傭勞動視為出售勞動力的市場行為。古人認為,在傭工、傭耕等雇傭勞動中不存在與買賣等同的市場關系,只存在雇與被雇的雇傭關系;這種雇傭關系不能改變雇主與被雇者的原有社會身份。同樣的道理,“傭書”者原來的士人身份也不會因為“傭書”而有所改變。在集市出售簡策的人,一般是個體勞動者(手工業者或農民);究其性質是個體勞動者的自產自銷。漢代的抑商政策在嚴厲打擊職業商人的同時,對個體勞動者的自產自銷則網開一面。在古代,自產自銷的個體勞動者與商人兩者存在明確的區別,政策上總是區別對待。總之,出售簡策者與“傭書”者因為都不是“入籍”的商人,他們不受“市籍”限制,是很自由的。因此,人們可以比較容易地雇得“傭書”,或購得簡策。從今天經濟學的觀點看,簡策可以買賣,是將書籍材料商品化;而“傭書”,是將復制作品的勞動商品化。那么這兩項商品化,究竟是為商品經濟服務,還是為自給自足經濟服務呢?首先,“傭書”者復制什么作品,一律聽命于雇主;而“傭書”的雇主是士人、官員等,其中沒有書商。其次,“傭書”的最終產品——書,沒有成為商品,都供雇主自己使用。根據這兩點,可以確認書籍材料與復制勞動這兩項商品化,歸根結蒂是為讀者傳寫服務,其目的是使人們自己“寫書”變得更方便、更簡單、更靈活。可見這個市場是為自給自足書籍經濟服務的,無非對其做了必要補充。
所謂自給自足書籍經濟,其實就是讀者傳寫。哪里有讀者傳寫,哪里就有自給自足書籍經濟。書商自誕生那天起,就已處于讀者傳寫的汪洋大海之中。隨著書籍材料特別是復制勞動的商品化,人們自己“寫書”變得更方便、更簡單、更靈活。人們所需書籍,一般都能通過傳寫這種方式獲得解決,一般無需仰賴書商。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書商做的事情,或書商可能做的事情,實際上已經不多,或者很少了。我們再說明書商根本無法自建作坊后,就知書商究竟能做什么事情。
四、書肆業務以經營舊書為主
漢代士人只要擁有書籍資源與資金,他們辦作坊從事書籍生產,一般是比較容易的。那么,書商為何不能自辦作坊從事書籍生產呢?
對書商來說,若要從事書籍生產,個體作業無法滿足商業需要,必須自己建立作坊。書商若要自建作坊,必須雇人到作坊來傭書與校書,在此必然面臨“市籍”制與士商對立這兩大障礙。“市籍”制迫使書商淪為不享有社會權利、沒有人格尊嚴的“下等公民”。可是,傭書者的社會身份都是士大夫,他們或為中下層士人,或為家道衰落的貴族子弟。傭書者因為是士人,觀念上都持賤商主義,視商人為沒有文化道德的卑賤之輩,瞧不起書商。他們從維護自己士人身份與尊嚴出發,恥于與商人為伍,不愿意也不可能為書商傭書。迄今所見自漢至唐的數十條傭書資料中,找不到一個以書商為雇主的傭書事例,這就是士人不肯為書商傭書的證據。辦作坊,必須有一批人為書商傭書。單就士人拒絕一項就把書商自辦書籍作坊這條路完全堵死。此外,書籍作坊為保證產品質量,不能沒有校書;從事校書,需是水平較高的學者。即便是在“市籍”廢除后的宋代,多數學者仍不愿為書商校書。只要“市籍”制仍在,士人就不能為書商傭書和校書。在“市籍”廢除以前,我國書商根本沒有條件也沒有能力自辦書籍作坊。
漢代書肆在京城的東市與西市,書商與其他商人都集中居住在這里。需知這個漢代市場,與《東京夢華錄》所記北宋開封的市場,存在不小的區別。北宋開封這個市場,是廢除了“市籍”并取消了宵禁以后的市場,所以是開放的與相當自由的市場。漢代京城的市場,是用高墻與四周完全隔離的,由“令署”晝夜嚴格管理的封閉市場與非自由市場。而且,北宋以前的我國市場,從來不是人們休閑娛樂的場所。東漢鄭玄注《周禮·司市》有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人們為何不到市場“游觀”?因為古代市場除了從事買賣交易,還是犯人殺頭的刑場。唐代劉禹錫《觀市》開頭就說:“有命士以上不入于市,《周禮》有焉。”在唐代,仍規定五品以上官員禁止入市。所以漢代市場并不是人們休閑娛樂的場所,高官禁入,有地位的士人不愿進入。市場實行宵禁,交易活動有時間限制。從事交易的商人身有“市籍”,經營不能獨立自主,也沒有一般人享有的自由與權利。總之,這是政治上受壓制、觀念上受歧視、人員流動受限制的封閉市場。如觀點以為,身有“市籍”的書商可以在這種封閉市場自建作坊從事書籍生產,又以為士人愿意到這封閉市場去為“入籍”的書商傭書,蓋不明古今市場與古今書商之區別。
從漢代開始一直到唐代,我國書商一直不具有自建書籍作坊的條件與能力。書商自己可能建立作坊,并從事“前店后坊”的經營模式,最早要到北宋廢除“市籍”與宵禁之后。中唐以來,不斷出現書商私刻作家詩集或日歷等種種例外現象,其意義主要是昭示舊制度即將變革,并不說明舊制度已經變革。漢唐書商不能自建作坊的根本原因不在書商自身,而是因為以重農抑商為國策,特別是無情壓制商人的“市籍”制。鑒于書商無法從事書籍生產,作者的新作出版之事宜就不可能交給書商辦理;書商不辦理新作問世,等于不掌握新的出版資源。在社會上,士人辦的書籍作坊越來越多。這些作坊生產的新書,都以自給自足為目的,不以商品交換為目的;況且,士人也不可能將自己生產的新書交給書商去牟利。社會上作坊生產的新書盡管很多,但它們都不可能成為書商掌握的新書資源。再加上書商無法自建作坊,所以自漢至唐上千年,書商始終不掌握也不可能掌握作坊生產的任何新書資源。不掌握任何新書資源,足以決定書商根本不可能從事新書購買、倉儲、銷售這些今天書商兼顧的發行業務。如今漢唐書商研究出現的種種錯誤,都是離開了社會環境與真實歷史,將古今書商混為一談,進而以今例古,認為只要有書商,必有發行存在。如今出版史著作幾乎都認為,書商在東漢就建立發行業,到唐代更有發達的發行業。可是,誰也拿不出書商自建書籍作坊和書商掌握新書資源的證據。實際上,自漢至唐的書商,他們與宋代書商已不一樣,與今天書商更是大不相同。對漢唐書商來說,新書的購買、倉儲、銷售以及新書銷售中批發、零售、分銷這類發行業務,他們一無所知,聞所未聞;既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說過。所以有書商必有發行的推理不能成立,那種認為漢唐書商從事新書發行并擁有發行業的觀點值得商榷。
書商無法自建作坊,也無法從事新書發行,那么他們究竟能做些什么呢?有一件事非靠書商不可,就是買賣舊書。書是古代士人的最愛。士人熱衷于“寫書”,也熱衷于藏書。可是,士人不愿與商人為伍,以從商為可恥,不肯從事書籍買賣。隨著文化教育大發展,凡讀書者家家“寫書”,人人“寫書”。這“寫書”就是制作書籍。社會上書籍數量與日俱增,其中總有一些書,因為個人或家庭的種種原因而成為冗余之書。冗余之書是使用過的舊書。可是,這一家的冗余之書可能是另一家急需之書,所以具有重新利用的價值。舊書品種不一,重新利用舊書的最好方法是通過市場交換自由選擇,實現物有所用。鑒于士人以從商為恥,不肯從事書籍買賣,通過市場交換實現重新利用舊書這件事,除了交給商人,沒有別的好辦法。商人買賣舊書,符合我國古代商業之道:互通有無,調劑余缺。而且,買賣舊衣服家具等舊物件也是古代市場上的一種通例。漢代的書肆與書商,就是適應了這樣的客觀需要必然產生并不斷發展的。自漢至唐的書商,偶爾可能私自“寫書”,暗自售賣。然而書商文化水平低,他們“寫書”質量差,數量少,可以忽略不計。書肆經營的書,都源于社會上的冗余之書,也就是舊書。書籍事業日益繁榮,冗余之書不斷增多,買賣舊書遂成為書商大有可為的事業,進而成為我國古代書籍市場一大特色。自漢至唐的書肆,其實是舊書店或舊書市場。它與宋代書籍市場有所不同,與現代書籍市場更是大不一樣。
五、書肆與書籍市場
漢代書肆大約誕生于公元前一世紀的后半世紀,已如前述。書肆經營之書,不是也不可能是作坊生產的新書,而是傳寫中產生的冗余之書,亦即舊書。書肆所在的市場是政治上受壓制、觀念上受歧視、人員流動受限制的封閉市場,所以漢代書商的經營環境遠不如宋代書商那樣寬松,書肆經營的品種與數量也十分有限。
從揚雄《法言》稱“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推斷,西漢書肆所賣主要是儒家之書。公元前28年,東平王劉宇請求成帝賜諸子與《史記》,這時候長安可能已有書肆。從成帝拒絕東平王賜書之請看,長安即使有書肆,也尚未售賣諸子及《史記》這類書。班固《漢書·敘傳》記西漢末年桓譚向班嗣借書之事:“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老嚴之術”指老子、莊子。這次,桓譚借“老嚴之術”遭班嗣婉拒,原因或許是受成帝拒賜東平王書的影響。不過,這時候長安肯定已有書肆,如果書肆有《老子》《莊子》,桓譚就能到書肆去買,不必向班嗣借書。從桓譚借書這件事可以推測,西漢末年的長安書肆以售賣儒家之書為主。不過,書肆所售是冗余之書,所以書肆沒有桓譚所需《老子》《莊子》,不等于社會上也沒有。像成帝召而不見的安丘先生一生在民間講《老子》,可見民間肯定有《老子》其書,只是數量很少,像桓譚那樣好學的長安青年也難以覓得。
東漢洛陽書肆經營的品種,比西漢有所增加。東漢初年,王充從家鄉會稽到京都洛陽,“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王充是太學生,他可以自由出入市場,到“市肆閱所賣書”。從“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看,王充在洛陽書肆所讀書中,理應包括子書。東漢對文化的管制比西漢寬松。西漢因尊儒而隱退的諸子特別是道家,到東漢又重新活躍起來,所以洛陽書肆有子書是完全可能的。不過,王充“師事扶風班彪”,他在洛陽所讀書,除書肆外,還可以讀班家的藏書。班家藏書中因有西漢成帝的賜書,其珍貴與豐富遠高于京城一般藏書家,更不是書肆可以并比的。王充“通眾流百家之言”所讀書,不必盡歸于書肆,班家藏書的作用肯定更重要。
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荀悅“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此見《太平御覽》卷614引。另外,《后漢書·荀悅傳》說:“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這兩則資料都說荀悅讀書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其中一則,是說荀悅“至市間閱篇牘”,意為在書肆讀書。荀悅生于洛陽,洛陽有書肆,他年幼時“至市間閱篇牘”是可能的。荀悅一生學術以儒家經史為主,再從他著《申鑒》看,作者涉獵“《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可知荀悅讀書很廣泛。荀悅生于名門望族。祖父荀淑是一代名儒,他八個兒子皆為才子,時稱“八龍”。叔父荀爽,是與鄭玄同時的著名經學家。荀悅因父親早喪而“貧無書”,幼年時不得已到書肆讀書。然而,他的親友多為富于藏書的學者或官宦,他一生所讀書不可能僅限于書肆。
王充或荀悅到書肆讀書,都是年幼時因“家貧無書”而迫不得已的行為。漢代市場是政治上受壓制、觀念上受歧視、人員流動受限制的封閉市場。王充、荀悅作為未有功名的年輕人,雖可以出入市場,但與今天人們輕松“逛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王充、荀悅去書肆讀書,可以說明書肆為貧寒子弟提供讀書的方便,也說明東漢書肆的書籍品種與數量與西漢相比有所增加。不過,書肆所售是傳寫中產生的冗余之書,其中大多數是普通常見之書,可能滿足人們年幼時的讀書需求,但難以滿足更高的讀書需求。這一點,我們可從曹操不得不請蔡文姬憑“誦憶”“繕書”“四百余篇”獲得證明。
漢代的書籍市場,除了書商經營的書肆,還有“槐市”這類民間集市。
據《藝文類聚》引《三輔黃圖》:“王莽作宰衡”時,擴建太學。“去城七里,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為隊(隧),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予買賣,雍容揖讓;或議論槐下。其東,為太學宮門寺。”可見,這槐市不在長安市場(東市或西市),它靠近太學,因“列槐樹數百行為隊(隧)”而得名。隧,是市場內的街道。槐市出現的時間是王莽作宰衡之后。據《漢書·平帝紀》,王莽作宰衡在平帝四年,公元4年;此后不久,就天下大亂。公元23年,長安陷落,西漢亡。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長安槐市存在的時間,至多二十來年。
槐市,是從事商品交換的民間集市,要注意它與長安或洛陽的書肆有何區別。槐市作為市場,特點有四:其一,以太學生為主體的文化集市。槐市上從事交易的是太學生,即“諸生朔望會此市”的“諸生”。所謂“經傳書記、笙磬樂器”,說明槐市以交換文化用品為主,其中包括書籍。槐市也交換“其郡所出貨物”,大概是各地土特產。其二,不以牟利為目的。從“相予買賣,雍容揖讓”看,槐市不以牟利為目的,旨在太學生之間互通有無,調濟余缺。其三,定期的文化集市。“諸生朔望會此市”,就是太學生每逢初一與十五在此交易;半月一次,一月兩次。其四,槐市也是太學生自由發表議論的場所,這就是頗受后代文人贊揚的“或議論槐下”。從這四點可知,槐市的市場主體是太學生,槐市沒有書商參與,這是槐市與書肆的最大不同處。在士人眼里,市場是藏污納垢的場所。太學生不是高官,可以到書肆讀書或買書。可是,太學生若在市場(東市或西市)從事文化用品的交換,就是甘愿與商人為伍,這是士人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太學生的文化集市,必須離開長安市場(東市或西市)另找地方,這樣才產生了地處太學之旁的槐市。
與槐市類似,還有公元二世紀前期的弘農“公超市”。張楷,字公超,生于公元86年,卒于公元149年。其父張霸是著名春秋學家。《后漢書·張楷傳》稱,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后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在文化界,張楷是頗具個人魅力的著名學者,當他隱居弘農山中,追隨者紛紛慕名而來。所謂“學者隨之,所居成市”,于是弘農山中出現了所謂“公超市”。弘農離東漢京都洛陽不遠,接近全國文化中心,文化人來往尚稱方便。“公超市”以滿足文化人的需求為主,它的市場性質與西漢長安的槐市相似。
我國古代書籍的商品交換,就是書的所有權通過交換從一方轉移給另一方,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市場內通過書商進行的,另一種是在市場外由士人直接進行的。前者如書肆,后者如“槐市”“公超市”。
最后,談談東漢劉梁“賣書于市“說明什么。
《后漢書·劉梁傳》載,劉梁“少孤貧,賣書于市以自資”。劉梁本人以文章聞名于順帝、桓帝時,《后漢書》列于“文苑傳”,并錄《辯和同之論》全文。劉梁本是西漢文帝之子梁孝王后裔,漢宗室成員。他后來通過薦舉入仕,官至尚書郎。劉梁之孫劉楨,仍以詩文名世,與王粲、陳琳等人同為“建安七子”。劉梁“賣書于市以自資”,“自資”是借以維持生計。他“賣書于市”僅限于“少孤貧”時,時間不長。再從他不久入仕,官至尚書郎,說明劉梁根本不想做書商,當時人也不把他視為書商。劉梁若做書商,就不能以文章名世,不能入仕做官,這是當時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史書記劉梁“賣書于市以自資”,旨在說明這位后來成為文化名人的宗室后裔,幼年孤貧時不避恥辱(士人以從商為恥)、曲折求生、艱苦奮斗的一種自強精神。現在人們把劉梁“賣書于市”與書商相提并論,似乎劉梁也是書商,可謂不倫不類。
不過,劉梁“賣書于市”的資料在書籍史上有其特殊意義。劉梁是東平寧陽人,即今天山東省寧陽縣人。寧陽雖然離洛陽很遠,然而受齊魯文化浸潤很深,是文化發達地區。劉梁在寧陽集市上“賣書”可以說明,東漢文化發達地區的縣境集市上,可能已有某種類型的書籍市場。
(劉光裕,原《文史哲》編輯部主任,教授)
注釋:
① 參見劉光裕輯《抄本時期書籍流通資料》,載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② 《漢書》卷5 3《景十三王傳》。按:《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隋志》所說“購以千金不得”,漢代文獻中不見,不知何據。
③ 晉李軌注《法言》,諸子集成本。
④ 陸侃.中古文學系年[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26.
⑤ 此據《漢書·地理志》。
⑥ 《廣韻》:“肆,陳也。”《廣雅·釋詁》:“肆,置也。”
⑦ 《史記·平準書》。
⑧ 見《漢書》卷5《景帝紀》。
⑨ 《史記·平準書》:“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
⑩ 《太平御覽》卷828引。
? 龍登高.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7-68.
? 《后漢書》卷49《王充傳》。
? 見王鏊《申鑒·序》,《諸子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