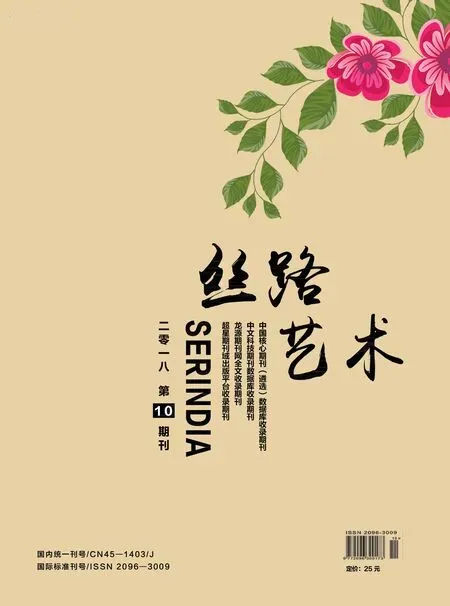淺談舞劇《絲路花雨》中所展現的敦煌舞臺服飾
張靜(甘肅省歌舞劇院,甘肅 蘭州 730000)
前言:
無論是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藝術,還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均是我國五千年人發展歷程中的文化瑰寶,而《絲路花雨》正是容壁畫藝術與絲綢文化為一體的舞藝術諸多,在我國文化傳承與藝術發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與價值。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當屬《絲路花雨》中為廣大觀眾展現出來的服飾風格,不僅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傳承,更是對當代受眾審美意識的一種升華與提煉。
一、《絲路花雨》的舞臺藝術特征在服飾方面的表現
燦爛輝煌的敦煌藝術,一直以來都是讓藝術家們流連忘返的寶庫。《絲路花雨》的主創們在多次進窟的觀摩探索中被敦煌壁畫中極具特色的服飾造型所吸引,在專家們的指導下對壁畫中服飾造型進行了臨摹,創作人員在一千多張服飾資料中吸取精華,群策群力。為舞劇《絲路花雨》的服飾造型奠定了雄厚的設計創作基礎。
在《絲路花雨》整部舞劇中,各類型服飾共有兩百多套、三千多件。根據人物身份、場景的不同,沒一件服飾的色調都要與劇中情境和諧統一(,即要有不同旳特征,又要突出主人公的形象個性。在設計上不能對敦煌壁畫中的服飾造型進行全部的生搬硬套,而是要集取唐代服飾的精華之處,再反復的推敲與加工提煉,設計出舞劇中人物的服飾造型既有唐代歷史特征的共性,又能突顯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如在序幕中出現的飛天仙子,在借助于鋼絲繩的幫助下,使舞者在空中優美地飛舞起來。飛天仙子在空中腰肢輕盈扭動,動勢含蓄嬌柔,其體態嫻娜多姿。妙曼的長裙隨著飛天仙子的身體飄動起伏,線條疏密有序,在優雅的旋律和徐緩輕盈的節奏中,再配以飄帶、鮮花、彩云等,使飛天仙子的形象飄逸柔曼,真實的營造出了“飛動”的芙感。可以想象,如果我們去除服飾,那么舞蹈本身就不會那么有吸引力。
二、《絲路花雨》的舞臺服裝設計形態
《絲路花雨》劇中的服裝靚麗多彩,聚西融中,具有鮮明的盛唐和地域特色。為當時籠統陳舊的新中國舞臺服飾打開了新的局面。復活了沉睡在壁畫中千年的服飾。全劇共近兩百多套、三千多件的舞臺服裝,讓觀眾感受到了唐代服裝的魅力。
郝漢義是《絲路花雨》劇的服裝設計師,他與助手焦艷芳、杜成蘭,在設計《絲》劇服裝時,遇見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無法從古代歷史的文獻文字中得到具體的古代服裝的形制、樣式、顏色等內容。
在敦煌現存四百九十二個石窟,四萬五千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畫中,人物繁多,服飾多樣,有些人物的服飾細致入微、華麗精美,而有些人物的服飾則寥寥幾筆、一掠而過。因此《絲路花雨》劇的服裝從多方面取材,曾受到沈從文和諸多敦煌服裝研究著的共同修改與建議,從一千多張敦煌壁畫臨摹服飾圖以及浩瀚的古代服飾文獻中進行深入研究,創作出既符合歷史真實又具有創造性的舞臺服裝,獲得了觀眾的認可與稱贊。對于《絲路花雨》劇服裝成功原因分析如下:首先,從大量的歷史圖片與資料中獲取充實可靠的理論支撐。其次,在尊重歷史真實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壁畫的原型進行再創作。最后,根據舞劇劇情人物,考慮角色身份以及舞臺服飾的可用性,為舞蹈本身服務,突出人物身份、性格。
(一)英娘與“喇叭褲”
英娘是《絲路花雨》中的主人公,無論是在服飾設計方面,還是在角色搭配方面,英娘的舞臺服飾不僅隨場景的變化而變化,還隨英娘在故事中所擔當的角色發生一定的變化,與此同時,英娘這一主角服飾與群眾服飾之間不僅能夠主次分明,還能夠達到協調統一的視覺效果。英娘的舞臺服飾是壁畫中世俗服飾同宗教服飾的結合產物,其服飾并沒有完全運用唐朝女性的服飾特征,以上身短裝、下身喇叭褲的形式呈現出來,而服裝的紋飾隨劇情的變化而變化。英娘獨具特色的“喇叭褲”對后期敦煌舞蹈服飾的設計具有深遠影響。
(二)古代勞動者的服飾
英娘的父親神筆張在《絲路花雨》中以普通勞動者的形象呈現出來,編導力求在神筆張身上塑造出一個擁有高超繪畫技藝同時身份低賤的普通勞動者的形象。在《隋書》中層記載,“庶人服白”。古代對腐蝕的穿著具有嚴格的規定與限制,身份低賤的農民、手工藝人等勞動生產者均不允許穿紅著綠,僅能穿粗布麻衣。因此,在《絲路花雨》中《彌勒下生經變》這一場景中,神筆張身著半袖粗布缺骻袍,衣服的顏色偏黃褐色,圍著綠色或者是藍色的圍巾,佩戴褐色腰帶,腳穿布鞋或者是草鞋,頭戴草帽,一只手拿鐮刀,另一只手揮著牛鞭,呈現一幅收割勞作的畫面。神筆張的這一生衣著與當時統治者對庶人服飾的要求相吻合。神筆張這樣的穿著在敦煌莫高窟壁畫中同樣有所體現,不僅為我國歷史文化考究提供重要素材,還為我國藝術設計提供思想創作源泉。
總結:
綜述《絲路花雨》劇的服裝設計,即盡力的還原與唐代服飾的歷史真實,又不拘泥與刻板的壁畫形象,并進行了大膽且嚴謹的創作,在統一劇情人物、主角、群眾、背景、色彩等關系的情況下,創作出來兩百多套,三千多件的服裝,成功的將觀眾帶回到唐代。在后來的演出中受到廣大觀眾以及專家的好評,同時影響了后來有關于唐代的以及敦煌舞的舞臺服裝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