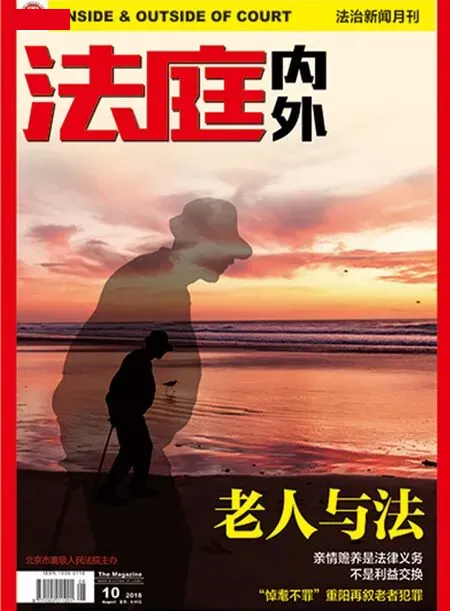好心幫人自殺小心構成犯罪
張颯
2017年6月15號晚上,江蘇某地發生了一起離奇的交通事故。肇事司機徐某在事故發生后撥打電話報警,當交警趕至現場后發現被撞女子吳某受傷嚴重,但奇怪的是吳某及其家屬都拒絕救治,而司機徐某更是神情淡定,仿若無事,這些異常的舉動引起了警方的懷疑。而在警方查看徐某行車記錄儀內容時發現,在吳某被徐某駕駛的車輛撞倒后,徐某竟倒車將吳某再一次碾壓。經過調查后發現,原來司機徐某與被害人吳某早已相識,吳某因患有癌癥,無法忍受病痛,意欲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其得知徐某駕駛的車輛在保險公司投保了保額為100萬的商業三者險后,吳某及其丈夫王某便游說徐某將吳某撞死,并提出除喪葬費外其余的保險公司賠償款都歸由徐某所有,徐某沒經得起金錢的誘惑便答應了吳某及其丈夫王某的請求,于是有了這起離奇的交通事故。隨后,當地公訴機關認為徐某主觀上有殺人的故意,肇事后再次碾壓,屬于殺人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對徐某提起公訴。于此同時,公訴機關指控吳某的丈夫王某為此次故意殺人案的從犯。
那么,為什么肇事司機徐某受被害人吳某及其丈夫的“委托”,將吳某撞死的行為會構成犯罪?為什么公訴機關指控吳某構成故意殺人罪而非交通肇事罪?本文將為大家一一解答。
幫人自殺構成犯罪
在我國,公民的人身權利受到刑法的保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任何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除非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否則都是犯罪行為。生命權作為一項重要的人身權利,除審判機關依法剝奪外,任何主體都不能對他人的生命權予以侵害。徐某對吳某實施的侵害行為,雖然是基于被害人吳某本人自愿,但生命權并非個人可以自由支配和處分的權利,不屬于被害人可以承諾的對象,也就是說被害人的自愿承諾并不能阻卻加害人侵害他人生命權這一行為的違法性。在本案中,徐某對吳某實施的侵害行為違反刑法規定,構成犯罪,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另外,幫人自殺的行為還可能出現在相約自殺的情形中。相約自殺即約定共同自愿自殺的行為,包括各自分別完成自殺行為,還包括一方受托將對方先殺死再完成自殺行為這一方式,后者即是幫人自殺的行為。實踐中出現過這樣的案例,即相約自殺中的受托方在幫助對方完成自殺行為后,因害怕恐懼等情緒而放棄自殺,那么在這種情形下,幫人自殺的行為也是違反刑法規定,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交通肇事罪還是故意殺人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體是交通運輸安全,其客觀方面在于在交通運輸活動中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司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在主觀方面為過失,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及過于自信的過失,同時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年齡為16周歲。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該罪名在主觀上為故意。對比交通肇事罪可知,兩罪在主觀方面有著重要的區別,交通肇事罪為過失犯罪,即行為人在主觀上只能為過失,而不能是故意。
在本案中,徐某駕駛機動車將吳某撞倒,之后還存在再次碾壓的行為,其對吳某的傷害行為主觀上是基于故意而非過失,故徐某的行為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論處而非交通肇事罪。
在量刑方面,眾所周知,故意殺人是一種極其嚴重犯罪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他人已有自殺意圖的情況下,幫助他人實施自殺的行為,雖然應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但與因憤怒、報復等心態而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情形相比,其主觀惡性程度較輕,在量刑時會考慮對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從寬處罰。
還可能構成保險詐騙罪
本案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由于徐某的車輛在保險公司投保了保額為100萬元的商業第三者責任保險,在吳某及其丈夫王某游說司機徐某將吳某撞死時便提出,除喪葬費外其余的保險公司賠償款都歸由徐某所有。商業第三者責任保險是指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員在使用保險車輛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財產直接損毀,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的險種。也就是說,保險公司理賠的前提必須是意外事故,而不能是故意犯罪。在本案中,司機徐某、被害人吳某及其丈夫王某系合謀,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意圖騙取保險金,對此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同時該行為可能構成保險詐騙罪。
雖然少部分人可能因為身體疾病、心理壓力等多方面原因承受巨大的身體痛苦及精神痛苦,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目前在世界范圍內,除了荷蘭、日本等少數國家外,多數國家包括我國在內,“安樂死”以及其他幫助自殺行為都是犯罪,在此提醒大家要知法守法,否則將付出巨大代價。
延伸閱讀
2009年在廣東深圳發生了震驚一時的“拔管殺妻案”,被告人文某的妻子胡某在家中昏倒后被送至醫院緊急救治,但一直處于昏迷狀態,雖然有心跳、血壓但需要靠呼吸機維持生命。被告人文某利用進入重癥監護室探視胡某的機會,以不想再讓妻子受罪為由,強行將胡某的呼吸管以及監測設備拔掉,并阻攔醫生及護士對胡某進行救治,最終胡某死亡。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文某強行拔掉其妻子胡某的救護設備,并阻攔醫護人員對胡某進行救治,導致胡某死亡,其行為應當按故意殺人罪論處,但情節較輕,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深圳市人民檢察院認為一審結果對文某量刑畸低,提起抗訴,最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判決結果。
那么,對于身體機能已經處于嚴重衰竭狀態,目前的醫療技術水平無法治愈,需要依靠維持生命的醫療手段來延續生命的患者而言,究竟能否采取停止救治的手段?可以明確的是,如果患者本人意識尚處清醒狀態,對于是否繼續接受救治,應當尊重患者本人意見,患者本人選擇放棄治療的,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家屬對于患者之后的死亡結果都不承擔法律責任。如果患者本人已經喪失自主意識,一般情況下,在醫生對患者病情作出醫學判斷后,認為無繼續救治必要的,在患者家屬同意的前提下,由醫生實施“拔管”這一停止維持患者生命措施的行為,并不觸犯刑法規定,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但是,目前我國法律對于作出停止救治的主體資格以及相關程序、標準等內容并無明文規定,這一法律空白還有待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