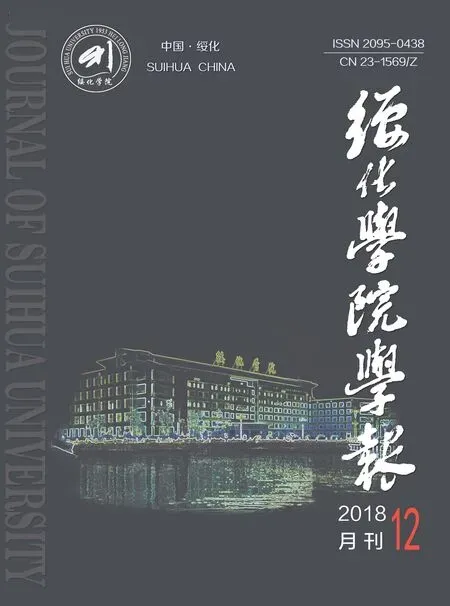論《動物園/第三工廠》的翻譯藝術
張國俠
(綏化學院外國語學院 黑龍江綏化 152061)
什克洛夫斯基以高標獨舉的形式主義文論躋身20世紀世界文藝理論大師之列,而他的散文創作自出機杼,開創了現代敘事學的新風,其鮮明化的詩意行文風格澤被深遠。什克洛夫斯基的自傳三部曲《感傷的旅行》《動物園》《第三工廠》,呈現了他早年發表的《散文理論》的文藝精髓,他厭倦老實陳述和笨拙抒情,必用新奇的藝術形式提升藝術感知度和審美欣賞的高度。書信體、日記體、傳記體、回憶體、札記體等形式均在他的筆下熠熠生輝,正如什克洛夫斯基自言的“俄國知識分子已被毀掉,我們靠手藝茍且偷生”那樣,他睥睨俄羅斯厚重深邃的寫作傳統,憑理論與實踐的雙重驅策實現了文學的革新意圖。他以理論為骨、創作為肌,突出了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陌生化理論建樹與文體實驗。
什克洛夫斯基的中國傳播與接受,多集中在《作為手法的藝術》《散文理論》《詞的復活》《漢堡記事》等文藝理論名篇上,他的文學作品逐漸被中國翻譯界重視,趙曉彬、鄭艷紅翻譯出版的《動物園/第三工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使什克洛夫斯基的自傳三部曲得以完整,更在翻譯實踐上實現了藝術探索。
文學翻譯是選擇的藝術,更是藝術的再創造。運用之妙,存乎于心,要實現兩種語言翻譯的準確、鮮明、生動、流暢,翻譯者在語言習得、文化素養上要比一般的語言學習者浸淫更深,在處理翻譯細節時形成了匠心獨創。趙曉彬、鄭艷紅翻譯出版的《動物園/第三工廠》,讓人想到嚴復強調的“信、達、雅”,傅雷宣稱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瞿秋白的“等同概念”,美國翻譯理論家E.A.Nida的主張“功能對等”或“動態對等”,無非是要突出的中心是“譯文要忠實準確地表達原文的意義,保持原作風格,忠實反映是非曲直和原作原貌。”達到魯迅對文章語言的要求——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更進一步的是,《動物園/第三工廠》,深得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論要義,即在譯文的形式上運思巧妙,以期“使對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這樣的譯本從語言、敘述方式、情節構造出發,在轉譯的過程中刷新了人們的審美感知。當然,她們的翻譯的新奇性不是為了單純的雜耍,而是譯者作為審美主體,對源語文本中異質成分的發現,用新奇性來達成翻譯的“陌生化”。
當代著名作家畢飛宇說:“一個好作家遇上一個好翻譯,幾乎就是一場艷遇。”藝術完成兩種不同語言的轉譯者,幾乎獲得了上帝的神諭。作為印歐語系之一的俄語,屬屈折語,詞根、詞干、詞尾的變化較多,它凸顯著俄羅斯人的個體發散思維,其形似乎比意更為重要。而屬于孤立語的漢語尚美崇簡,極具漢藏語系的特點,重意不重形,強調直觀和形聲會意,理解上突出曲折婉轉、含藏豐富的特質。如何銜接,趙曉彬、鄭艷紅的翻譯進行了多種的藝術探索,在精準的表達基礎上,文字細膩鮮活,轉譯效果到位而不越位。
什克洛夫斯基的這兩部作品涉及了隱喻、位移、階梯型構造、穿插敘事等陌生化手法。什克洛夫斯基的這些手法看似無心,實則匠心,使原本連貫嚴整的敘述節奏重新組合,拓寬了小說的疆域,豐富了內容的廣度。趙曉彬、鄭艷紅的翻譯充分呈現了這一特征,在藝術的再創造過程中做到了“眉目清楚,層次分明,重點突出,語氣連貫,前后呼應”。《動物園》是以書信體構成的小說,混雜了文評、政論、回憶,哲思、抒情替代了談情說愛。為此,鄭艷紅的翻譯更像是預設了一個“敘述接收者”,正好呼應了原文中主人公的多維傾訴。在什克洛夫斯基與俄裔法國作家艾莉薩·特里奧里亞的34封通信中,真實人物與虛擬編輯的雙重身份自由切換。主人公負責敘事事件、推進故事、表情達意;編輯負責挖掘內涵,理順思路。作為書信體,作者的書信體故意略去呼語和落款。作者去信30封,收到的情人回信4封。譯者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借用中國人書信體的特點,盡得原文神韻。“在女人的生活中,句法根本不存在。(Синтаксиса в жизни женщины почти нет.)”這句翻譯深得原文神髓,符合寫信人機智幽默博學的身份。在《第八封信》中,譯者忽有神助,“我不是不幸的女人,我是艾麗雅,面色紅潤,體態豐盈。”惟妙惟肖刻畫了作家臆想中的“美人”形象,唯其譯筆才能讓中國讀者領略什克洛夫斯基的藝術之美。
為呈現什克洛夫斯基隱喻型文本的藝術之妙,譯者將作品中的俗語、諺語、俚語、成語,換轉為恰切漢語的語匯,多擇用意譯、換譯。過分拘泥直譯,會傷害原文的表意效果,而離開原文較遠的意譯,更是粗暴的做法。“在遇到原文出現文字游戲之類的變異下,要采取以變應變的策略,舍棄表層意義,傳達深層意蘊,也就是說,譯出精神,譯出風格,一句話,譯出原文的妙處。”3譯者選擇哪一種譯法,是根由表情達意的迫切需要。如地名和人名、作品名、器物名,多用音譯。如《第七封信》中譯句,“肖像畫上的臉很肉,或者說更像是裝滿食物的腸衣”,將臉部肥胖譯為“肉”,運用的是意譯,而“腸衣”之喻則選擇了直譯。
翻譯在兩種文字形象轉換上運用了如下方法:留形、換形、整形、分形、顯形。在翻譯時,充分考慮了目標讀者的實際感受、原著的藝術質素、文化差異等情況,減少了讀者的閱讀障礙與陌生感。譯者大幅度調整語序,變換句式。首先,恰切地運用了加詞、減詞的方式,來處理語言間的不完全的對應關系。為達到神似和意似的目標,加詞或減詞是翻譯的主動選擇,而非空穴來風地隨意妄為。什克洛夫斯基原文多類音節重音詩體,即在每個詩行中不僅要有一定數量的音節,而且要有一定數量的重音,并且重音的分布有一定的規律。在翻譯時,譯者在確切理解原文的基礎上,有時刪繁就簡,去掉一些不必要的語氣詞等。如《第十五封信》中譯筆為,“孕育他們時愉快,就覺得難為情,懷著艱難,生時就痛苦,然后孩子們活得也痛苦。(Их зачинают весело,весело и не постыдно,носят трудно,рожают больно,а живут они потомгорько.)”將原俄文的抑揚,變換為中國行文的鋪排,在音步、韻腳、押韻方式等方面將差異降到了最低要求。
翻譯是文學的歷險,正如陸谷孫所說:“翻譯過程中內心掠過一絲得意的時候少,更多的是‘詞窮’時的惶惑和渺小感。”[1]要擺脫這種“惶惑和渺小感,” 譯者要堅持樸則近本,更要掙脫形式的緊身衣。翻譯的難度不在于認識多少異邦語詞,而在于溫故知新,熟知二個國家的語言文化,恰切找出對等策略。“對于任何人希望表達的思維,都僅有一個詞是合適的,唯一一個表達這一思維的詞,唯一一個動詞使這思想栩栩如生,唯一一個形容詞來說明這一思維,因此我們必須去尋找并最終發現這個詞,這個動詞和這個形容詞。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滿足于類似的表達。”[2]翻譯無疑是戴著鐐銬跳舞,多次琢磨只為了詞語恰切轉譯,要處理好歸化、異化的問題。
翻譯是一門雜學,首要的是消除語境隔閡,增加可讀性。張澤乾在其《翻譯經緯》中指出:“翻譯不僅要跨過語言的障礙,更要逾越文化的鴻溝”,“語言的翻譯就是文化的翻譯。”《動物園/第三工廠》更具隱喻和諷擬色彩。這是一部理論探討與傳記抒寫融合的文學回憶錄。在翻譯時,趙曉彬老師特別注意到俄羅斯民族善思考,常常對現實生活提出疑問,故而在漢譯時要多選擇用疑問詞、疑問句、感嘆詞、感嘆句來突出這一特征。如在《畢業考試》里,“春色攀援到了大衣上,春風掠進懷里。”譯文行文流暢,極顯俄羅斯人面對春天的喜悅感,中國讀者讀來也倍感親切。“可讀性是指譯文對于作者來說的易解性,即期本省的通順程度,所以原作的可譯性越強,譯文的可讀性就越大。”[3]譯文時時增加文本的陌生化,極大提升了閱讀的快感。
“由于漢語表達多用短句,而俄語容易形成較長的的句子,因此,在俄譯漢翻譯過程中,更要利用拆句的方法,以使譯文變得更加簡潔明了。”[4]要完成什克洛夫斯基各種隱喻的換譯,譯者還經常使用拆句法、并句法。“要知道,審美的作品不是享樂的組織,而是作品的組織。”(《關于藝術的自由》)此處使用的是并句法。
“從譯語中選擇與原語相似或類似的形象來替換原語中的對應形象”。此種譯法多適用于中俄文化差異引發的翻譯問題。“村莊患上了自閉癥。”(《接下來》)在什克洛夫斯基那個時代,尚無自閉癥這個詞匯,但譯者接通了歷史與當下,讓“自閉癥”這個詞匯穿越到了前代。譯者經常要涉及文化差異處理。“戰爭漫不經心地咀嚼著我,我就像從吃飽的馬嘴里掉下的麥秸。”(《戰爭》)譯者將被動句,譯為漢語的主動句。
趙曉彬、鄭艷紅翻譯的《動物園/第三工廠》成功探索了多種陌生化藝術手法,達到了英國作家毛姆所說的效果:“詞有其力、其音、其形;唯有考慮這些,方能寫出醒目入耳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