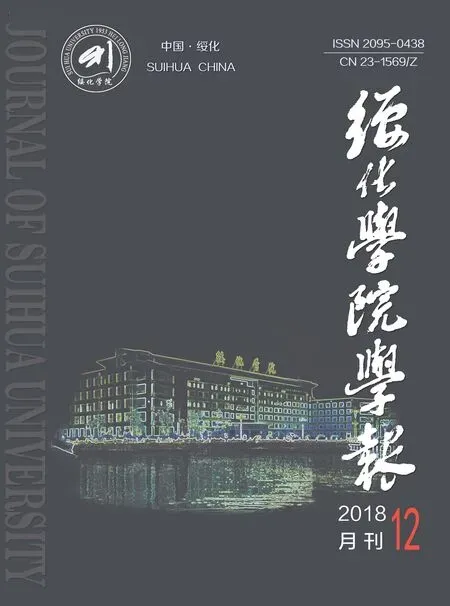漢代禮法結合統治模式的確立與演變
李東澤
(山東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 山東濟南 250358)
一、漢初統治思想轉型中的禮與法
漢朝建立之初,雖然在客觀上承襲了秦朝的各種制度,但是鑒于秦二世而亡的深刻教訓,不得不在思想意識上打起十二分精神,對秦之典章制度予以猛烈抨擊,而對秦朝法治傳統更是尤為警惕,斥之以“暴政”,唯恐重蹈覆轍。
如陸賈在總結秦亡教訓之時就認為:“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1](P62)而賈誼也指出:“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3](P2244),認為秦王“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3](P14)激烈反對秦朝嚴刑重罰、以法為治的統治方式。于是,寬刑省禁的無為而治就成了漢代統治者的必然選擇。
然而,從國家治理和社會控制的角度來說,“法”的要素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徹底摒棄的,事實上,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漢律對秦法也有著一定程度的繼承,“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2](P1099)。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漸恢復,缺少法治約束的“無為”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日漸失序的社會狀況,以至于出現了“網漏于吞舟之魚”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法”的作用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其表現形式就是儒法思想的融合。
早在先秦時期,荀子在繼承儒家“禮治”思想的同時,也主張不能忽視“法治”的規范作用,在他看來,“法者,治之端也”[4](P272),認為“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4](P545),因此要禮法并用,“隆禮至法則國有常。”漢朝建立以后,儒生們承荀子之余緒,重新展開了對禮法關系的討論,在這一時期初步形成了禮法融合的趨勢。其中,以陸賈和賈誼的思想最為典型。
陸賈最早提出了要以“仁義”治國的禮治思想,他認為“禮義不行,綱紀不立”以致“后世衰廢”[1](P18),因而主張“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1](P17)。但陸賈也并不是絕對的排斥法治,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1](P16),統治者要“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1](P132),其強調“為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1](P124)的精神與法家是相通的。
賈誼作為荀子的再傳弟子,其禮法融合的思想主張要比陸賈更加明顯。在他看來,禮與法都是統治者借以維護統治的重要手段,“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3](P71)他將禮法的關系表述為“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并指出“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2](P2252),充分體現了他先禮后法,禮法并用的思想主張。
然而,在西漢初期,雖然禮法融合的意識已經出現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主張之中,但是由于秦亡之殷鑒不遠,人們對于法治精神的重新挖掘還是抱有非常警惕的態度。即便是賈誼自己,也還是再三強調“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2](P2253)只能說,禮法結合的統治模式想要真正得以實施,其時機尚未成熟。
二、德主刑輔與引禮入法的實施
經過漢初儒法合流的前期鋪墊,到了漢武帝時,雖然儒學獨尊,但“法”的精神也隨之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司馬遷在評價郅都、杜周等酷吏時以為:“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5](P3801)肯定了他們“方略教導,禁奸止邪”的重要作用。面對當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僣上亡限”[2](P1136)的局面,單純的禮樂教化并不足以挽救日益失控的社會秩序,在這種情況下,“法”作為一種具備強制性的社會控制手段,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禮治的有效補充。
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策問賢良文學,大儒董仲舒脫穎而出,在他為漢帝國所構建的禮治體系藍圖之中,禮和法成了社會控制得以實現的重要手段,“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刑罰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6](P353),兩者缺一不可。他利用陰陽五行的觀念,將之引申到禮法關系之上,提出:“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6](P341)“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2](P2501)這樣一來,禮與法、德與刑之間就天然具備了先后順序,“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6](P336),形成了“德主刑輔”的禮法關系。董仲舒這一思想最終為漢代統治者所接受,漢宣帝就曾因“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而遭到時為太子的元帝質疑,認為他“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于是“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2](277)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禮法并用的“霸王之道”已然成為漢朝政府治理國家時所秉承的重要方略,甚至上升到了“漢家制度”的高度。
既然德主刑輔、禮法并用的治國方略已然確立,那么對法律的制定與規范就成了重中之重。據《漢書·刑法志》記載,武帝時期由于“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之后“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以致出現了“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2](P1101)的局面。面對如此繁苛混亂的情況,如何實現以德為主,以刑為輔,保證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德政禮治順利實施?為此,漢代君臣采取了“引禮入法”的重要舉措。
所謂“引禮入法”,就是指將儒家的道德規范和是非原則注入到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來,用儒家思想引導國家的法制運行,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最早也是由董仲舒所提出的,在他看來,《春秋》一書蘊含著君臣、父子和夫妻之道的微言大義,因此對于維護國家禮治、維持社會秩序有著重要意義。這一提議很好地契合了統治者鞏固專制統治的需求,因而迅速得到了政府的提倡和推廣。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去位歸居”以后,“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2](P2525)《后漢書》里也說:“故膠西(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7](P1641)董仲舒用《春秋》所斷之案后來被編成一本《春秋決事比》,今已失傳,但從現存的幾個案例來看,每每以儒家思想來解釋甚至改造法律條文,實施以“父子相隱”“論心定罪”等原則,“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8],著重突出了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對法律的主導作用。
“引禮入法”的實施,并不限于對《春秋》這一部經典的重視,更不限于董仲舒一人,在當時,很多官員施政斷案之時都要引申經義,如公孫弘本是“獄吏”,后因“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5](P3550)才得到武帝的賞識;當時有名的“酷吏”張湯也“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5](P3785)漢昭帝時,大臣雋不疑也因能以經義決獄而得到昭帝和霍光的賞識,引發了他們“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大誼”[2](P3038)的感嘆。
此后,“引禮入法”的原則不斷延續下去,成了漢代法制建設的準繩。如東漢時期“掌天下獄訟”的陳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并提出了“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的說法,務求法律制定“應經合義”“與禮相應”。[7](P1554)這種用經義闡釋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當時之人的贊同,包括一些大儒如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也紛紛參與進來,史載“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余言。”[9]可以說,通過這些“引禮入法”的行為舉措,不僅使儒家思想深入滲透到法律的施行過程中,更使得儒家經典法典化了,從而大大提高了禮治的權威性與規范性。
三、禮法結合的深入與循吏政治的盛行
漢武帝以來,面對漢初數十年君臣“無為”而導致的“罔疏而民富”、社會失控的局面,漢朝統治者一方面大興禮治,實行禮樂教化,另一方面又重啟法治傳統,重用酷吏,到漢宣帝時,最終確立了德刑兼用、“霸王道雜之”的社會控制模式。宣帝幼時曾流落市井,因而早年間頗好刑名,甚至曾因時為太子的元帝“柔仁好儒”,而轉而偏愛“明察好法”的淮陽王,“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險些掀起一場更換繼嗣的風波。[2](P277)然而晚年時的漢宣帝思想有所轉變,面對吏治嚴苛的局面,終于不再堅持原來的強硬立場。
黃龍元年(前49年),即漢宣帝執政的最后一年,他下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2](P273)一改之前好用刑名的統治風格,要求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之后不久,宣帝去世,過去曾被他認為“亂我家者,太子也”[2](P277)的元帝繼位,漢帝國統治政策的重心逐漸向“德教”“周政”轉移,漢代禮治為主、法治為輔的社會控制體系得到進一步發展。在這其中,一個非常顯著的明證就是循吏政治的盛行。
“循吏”之稱始見于《史記》,《史記·循吏列傳》中給“循吏”所下定義是:“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5](P3741),《太史公自序》中也說,循吏為“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5](P3997)可見,司馬遷所謂的“循吏”,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奉法循理”。在此之后的《漢書》和《后漢書》也都專門列有《循吏傳》。《漢書》將董仲舒、公孫弘、倪寬三人列在《循吏傳》的開頭,認為他們:“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2](P3623),而《后漢書》也以既能“導德齊禮”又能“明發奸伏,吏端禁止”[7](P2458)作為循吏的標準。由此可見,循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漢代統治中禮與法相結合的表現。
從循吏政治的演變軌跡也可以看出漢代禮法結合逐漸深入的痕跡。《史記》中所記載的循吏均為漢代之前的人物,如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等,這表明在當時禮法結合的循吏之治不過是一種理想中的執政模式。到了宣帝以后,才出現了“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的局面,涌現出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一大批循吏[2](P3624)。到了東漢時期,被列入史書的循吏數量則更盛于前朝。
除了數量的增加之外,關于循吏事跡的記載更能夠體現出漢代禮法結合的演變與深入。“循吏政治的關鍵是擴大和強化條教的作用,使之成為國家律令與民間習俗即“公法”與“人情”之間的橋梁”[10]。這里所謂的“條教”,指的就是地方官員依據儒家禮樂教化的精神,所制定的不同于嚴苛的法律條文的施政方針,其教化意義不言而喻。
西漢宣帝時,著名的循吏黃霸“力行教化而后誅罰”而“治為天下第一”,他也因此聲名大噪。等他擔任丞相時,又“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后叩頭謝”。他正是想要用這種方式來鼓勵地方官員來通過“條教”實行教化,卻遭到了時為京兆尹的張敞強烈反對,張敞指出“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撿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最終張敞的堅持以法條律令為行政準則的意見得到了漢宣帝的支持,“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2](P3633)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雖然禮法結合的趨勢使得循吏政治得到追捧,但是禮和法之間還是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界限,對于執政者來說,“奉法”和“循理”都是非常重要的職責,二者不可偏廢。
宣帝以后,秉持“周政”、輕刑省法成了漢代統治政策的新取向。漢元帝在即位之初就下詔曰:“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2](P1103)在此之后,西漢的幾位皇帝均有蠲減律令的舉措。到了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帝同樣認為“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下令“議省刑法”[7](P29),面對大臣“法令既輕,下奸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7](P1166)的建議,則以“隆刑竣法,非明王急務”的理由予以拒絕。光武以后,章帝、和帝等也都采取了省刑約法的舉措。“法”理所當然的退居到次要地位,而禮治教化則成了施政治民的首要原則。
在這種崇儒重禮的政治氛圍影響之下,東漢循吏政治中注重教化的一面被著重突出了,而法律在很多時候反而成了用以襯托禮治精神的非必要手段。在《后漢書》中,利用“禮”的精神來息訟止爭就幾乎成了循吏的標配,如:
(秦彭)以禮訓人,不任刑罰。[7](P2467)
(許荊)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7](P2472)
(劉矩)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7](P2476)
與西漢時期“吏道以法令為師”[2](P3397)“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2](P3400)的觀念迥異,東漢循吏們以憑借個人意志而背離法律的行為非但沒有引來質疑,反而因為彰顯了儒家的禮教精神而受到褒獎與贊揚,成為了時人追捧學習的楷模。如童恢任不其令之時,“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其治下反而“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7](P2482)而立于熹平二年(173年)的《漢司隸校尉忠惠公魯君碑》碑文所載:“遷九江大守,□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載,穆若清風,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歌”[11],更是以能效仿黃霸、召信臣等循吏的事跡而自耀。
余英時先生曾指出:“研究漢代循吏決不應以兩漢書的《循吏傳》為限。”[12]這是因為在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隨著統治政策中禮治因素的不斷強化,法治傳統徹底退居于輔助地位,而循吏“以德化人”之原則影響則不斷擴大,逐漸成為更多官吏們所遵循的執政準則。如東漢時的劉寬,其人“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于是“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7](P887)而潁川陳寔義釋“梁上君子”的故事則更為著名:“時歲荒民,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7](P2067)面對不請自來的“梁上君子”,陳寔非但沒有追究其罪責,反而溫言勸慰,甚至慷慨贈絹,最終鄉閭之人都被他感化,“自是一縣無復盜竊”,成為漢代官員們以禮樂德化而非刑罰律令來治國安民的典型例子。
結語
漢朝建立之初,有鑒于暴秦之弊,統治者從中吸取了長足教訓,遂視秦法為洪水猛獸,采取了“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以休養生息。然而,在度過了王朝初期的恢復過渡階段之后,政府存在感相對薄弱的黃老學說已越來越難以適應大一統王朝的統治需要,日益壯大的漢王朝亟需一種新的學說來鞏固自身統治,在歷史上,正是完成了自我改造的儒家思想順應了這一需要,順理成章地被接納為新的統治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全面復興過程中,一直處于被打壓狀態的法家思想也隨之死灰復燃的,重新登上歷史舞臺。所謂漢承秦制,事實上無論是制度的構建還是具體的實施過程,漢對秦的法治精神都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繼承,而從國家治理和社會控制的角度來說,法治更是必不可少的統治手段之一,很多儒家學者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因而積極地推動儒法之間的合流,體現在統治思想與行政手段上,就是禮與法的結合。
在漢代,從一開始對法家思想的排斥,到儒與法在思想上開始合流,再到引禮入法的具體實踐,最終形成了外儒內法、德主刑輔、禮法結合的統治模式。然而,隨著禮法結合進一步深入,儒家禮樂教化思想日益受到尊崇,法的精神再次被壓制,逐漸淪為了禮的附庸,盛行于西漢中后期和整個東漢時期的循吏政治最能夠體現這一過程,在崇儒重禮的大環境中,原本應該是“奉法循理”、執兩用中的循吏標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能“以禮讓化之”才是被視為循吏的首要原則。在這種政治生態的影響之下,“陳寔遺盜”式的故事受到了極大推崇,止訟、息訟甚至無訟成為地方官員彰顯政績的重要追求,并由此對中國近兩千年的行政統治模式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