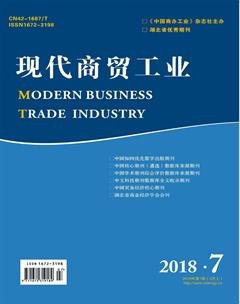古今政治思想的區別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基雅維利轉折處的思考
2018-04-03 05:39:36王睿
現代商貿工業
2018年7期
王睿
摘要:古今政治思想、觀念的發展變化,從圣經中對上帝的信仰與服從,到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提出政治體制該是如何,人們該如何一起共同生活、構建一個社會,再到現代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出現轉折。從古代政治走向現代政治,再到后來的洛克、盧梭等,古今政治思想觀念有很多相通之處,但也有很多差異。有鑒于此,開始思考一些亞里士多德與馬基雅維利這兩位先哲的不同之處,思考的外在工具便是兩位的著作《政治學》以及《君主論》。
關鍵詞:政治思想;政體;君主國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7.076
1對于政體的理解問題的差異
亞里士多德認為“政體(憲法)為城邦公民的組合一切政治組織的依據。”而人是一種政治動物,政體首先分為正宗政體與變態政體,正宗政體是“這一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的統治要是旨在照顧全邦共同的利益,”變態政體是“只照顧自己一人或少數人或平民群眾的私利,”也就是通過公務團體的目的,是為照顧全邦共同利益還是一人或少數人的私利,將政體分成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正宗政體又包括三種:王制(君主政體)、貴族(賢能政體)及共和政體。其中,政體(政府)以一人為統治者,能夠照顧全城邦人民利益的就是“君主政體”,若政體以少數人,雖然不止一人且不是多數人,便是統治者“(賢能政體)”,而群眾作為統治者并能照顧到全邦人民利益的則是“共和政體”。與正宗政體相對,他接著提出均不能照顧城邦全體人民的利益的三種變態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它們分別是上面提及的三種正宗政體相對應的變態,“僭主政體以一人為治,凡所設施也以他個人的利益為依歸;……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