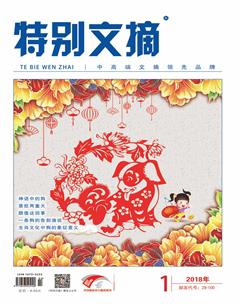民間藝術(shù)中的狗
對(duì)于務(wù)實(shí)而又心靈手巧的中國(guó)人來說,用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shù)形式,將忠誠(chéng)的朋友——狗留在記憶里,無疑是一種非常好的選擇。
在各種材料、各種方法創(chuàng)作的民間工藝美術(shù)作品中,許多都能見到狗的形象。例如木版年畫、剪紙、雕刻、泥塑、刺繡以及陶瓷器皿的裝飾紋樣、民居建筑的裝飾紋樣中,都曾出現(xiàn)過狗。
河南省淮陽(yáng)縣城以北有“伏羲太昊陵”。直到今天,太昊陵周圍的村莊仍然生產(chǎn)一種名為“陵狗”的泥玩具,又叫“泥泥狗”。它通體烏黑,彩繪紋飾,造型奇特,風(fēng)格古奧。其實(shí),這些泥玩具的造型并不都是狗,最多的倒是猴,民間卻一律稱之為“狗”。這種現(xiàn)象與伏羲就是盤瓠的傳說不無關(guān)系。這些傳說反映了上古時(shí)代可能存在著以狗為圖騰的部落。
武強(qiáng)木版年畫中有一幅《義犬救主》,畫中題字曰:“楊升醉臥在松陰,牧童燒荒火近身,黃犬濕草救主意,傳流萬代古至今。”畫中正有一條小狗自水邊奔向醉臥的楊升。這張年畫的內(nèi)容即源自“義犬冢”。原作中的主人叫楊生,木版年畫中改為楊升。
出土于河南新鄉(xiāng)百泉鎮(zhèn)的漢代陶狗,造型十分精準(zhǔn),甚至連狗身上的肌肉結(jié)構(gòu)都分明可見,說明當(dāng)時(shí)的作者對(duì)狗的形態(tài)已經(jīng)有了深入研究。唐代邛窯以出產(chǎn)小型陶瓷動(dòng)物著稱,也制作過狗。這種狗取坐勢(shì),前腿稍長(zhǎng),頸項(xiàng)也長(zhǎng),形似一個(gè)跪姿而昂首的人。把狗做成人形,作者一定對(duì)狗產(chǎn)生了獨(dú)特的認(rèn)識(shí)。
北京已故著名泥塑藝人韓增啟曾經(jīng)塑造過一對(duì)彩繪泥塑叭狗,黃綠彩繪,黑眼白框,神態(tài)憨拙質(zhì)樸,確是寵物風(fēng)范。甘肅環(huán)縣皮影造型中有一只“天狗”,跟隨二郎神楊戩左右,轉(zhuǎn)戰(zhàn)云天。其造型修長(zhǎng)勁秀,表現(xiàn)出敏捷機(jī)警的特質(zhì)。河北張家口蔚縣窗花中的狗無疑經(jīng)過了美化處理,色澤已完全脫離了現(xiàn)實(shí)局限,盡可能用鮮艷靚麗的顏色把狗表現(xiàn)得美好而生動(dòng)。
另有一位收藏家鄭作良,藏有一組黑陶狗,共5件,經(jīng)專家鑒定為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隨葬品。黑色陶器在中國(guó)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常有發(fā)現(xiàn),陶胎較薄,表面光亮漆黑,最薄的黑陶有“蛋殼陶”之稱。5件黑陶狗中,最為獨(dú)特的是仰犬,它仰首曲脖與前低后高的姿態(tài),猶如商周時(shí)期青銅器上的龍紋。從側(cè)面觀察,狗的造型與龍的造型非常相似,加上身上采用了圓形的鱗紋,更有了龍的意象。其他4件分別為臥犬、蹲犬、回頭犬、人形犬,每件風(fēng)采姿態(tài)各異,件件栩栩如生,造型古樸兇悍,沒有一件類同重復(fù),充分體現(xiàn)了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藝與豐富想象力,這些是研究民俗、陶藝、人文的珍貴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