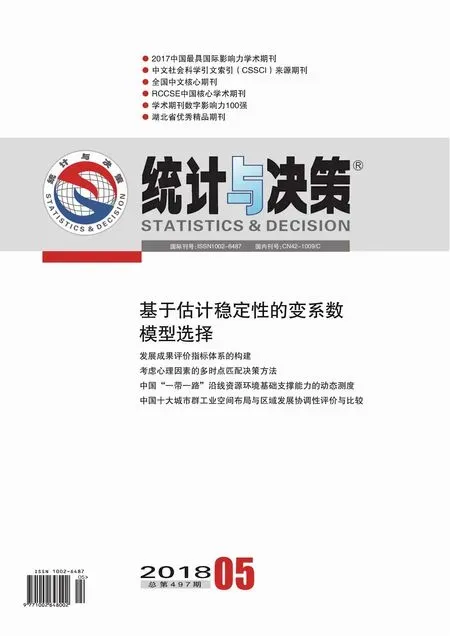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與生態效率的時空耦合特征分析
陳林心,何宜慶,周小剛
(1.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南昌330063;2.南昌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南昌330031;3.華東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南昌330013)
0 引言
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需要堅持和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注重綠色發展,建設生態文明,意味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改變,而金融業的發展能夠更快地促進經濟增長和區域發展,金融集聚和經濟發展也是促成生態文明和提高生態效率的必要途徑,如何合理而充分地發揮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對生態效率的提升作用,是亟待研究的科學問題。
國內外對于金融聚集、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的研究由來有之。有學者認為,金融聚集能夠較好地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引導要素資源流向高效率區域,使資源環境中生態要素的初始狀態發生改變[1,2]。Daly(1990)[3]認為能夠承擔環境保護責任的前提是經濟的持續增長,Sachs等(2001)[4]實證了資源稟賦反而成為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這一現象。另外,學者們也探討了金融集聚動因和影響因素、金融集聚效應,從金融集聚和經濟增長關系的角度,展開了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5-11]。對于區域生態效率的研究,國外學者著重理論和應用研究,國內學者大多感興趣于生態效率的評價[12-15]。綜合上述研究成果,雖然國內外關于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的研究都已相對成熟,但研究三者之間關系的成果較少。因此,本文基于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之間的協同關系,以我國內地省級行政單位(下稱省域)為對象,研究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探討三元系統協調發展的現狀與特征,并對我國省域金融、經濟和生態協調發展進行分析和評價。
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借鑒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從總體規模、銀行、主券、保險四個方面評價省域金融集聚;從民生改善、科技創新和社會發展三個角度評價省域經濟發展;從生態環境效益、資源能源效率、經濟效益和循環經濟四個角度評價省域生態效率,建立評價指標體系(見下頁表1)。省域面板數據分別來自2009—2016年的《中國統計年鑒》、31個省級行政單位各自統計信息網或iFinD數據庫。
金融集聚系統的12個二級評價指標包括:金融業增加值(億元)、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億元)、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億元)、金融業固定資產投資(億元)、金融業城鎮單位從業人員(萬人)、城鄉居民年末儲蓄存款余額(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股票發行規模(億元)、債券交易規模(億元)、保費收入(億元)、保險密度(元/人)和保險深度(%)。
經濟發展系統的6個二級評價指標包括: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居民消費水平指數、三產增加值指數、市場技術成交額(億元)和人均GDP(萬元/人)。
生態效率系統的13個二級評價指標包括:單位GDP廢水排放(噸/萬元)、單位GDPSO2排放(噸/億元)、單位GDP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噸/萬元)、單位GDP煙塵排放(噸/萬元)、單位GDP電耗(千瓦小時/元)、單位GDP水耗(立方米/元)、單位GDP城建用地(km2/億元)、總資產貢獻率(%)、本年應交增值稅(億元)、工業增加值(億元)、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億元)、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造林總面積(千公頃)。
2 研究設計
本文在選擇和確定了三元系統指標體系后,通過構建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函數,計算得出2005—2015年我國31個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并進行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相關性檢驗,從而根據省域耦合協調度所屬類型,刻畫出省域三元系統之間的時空耦合特征。
2.1 耦合度函數
本文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16],得到金融集聚系統F(x)、經濟發展系統G(y)和生態效率系統H(z)的三元耦合模型:

式(1)中,Cik為第i年第k個省域系統三元耦合度;F(x)ik、G(y)ik和H(z)ik分別為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第i年第k個省域的綜合評價指數。
顯然耦合度值C介于0到1之間。當C=1時,耦合度極大,子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之間達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統將走向新的有序結構;當C=0時,耦合度極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處于無序狀態,系統將向無序發展。將耦合度分為4個等級,分別表示耦合系統在時間序列上的4個不同的耦合過程(見表1)。

表1 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耦合程度分級標準
2.2 耦合協調度函數
耦合度雖然是反映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耦合程度的重要指標,然而,它在多個區域對比研究的情況下,卻很難反映系統的整體“功效”與“協同”效應,因為耦合度計算的上、下限一般取自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某一指標最大、最小值,所以單純依靠耦合度判別有可能產生誤導。為此,本文構造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三元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函數,用來評判它們交互耦合的協調程度,其公式可表示為:

式(2)中,D*為耦合協調度;T為三元子系統耦合協調指數,α、β、γ為三元子系統對總系統整體協同貢獻的權重,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金融集聚是手段,經濟發展是核心,生態效率是是歸宿,在此分別對它們賦值0.25、0.35和0.4。根據耦合協調度D*的大小和耦合階段,可以將耦合協調類分為:①0≤D*≤0.4時,為低協調耦合類Ⅰ;②0.4<D*≤0.5時,為中協調耦合類Ⅱ;③0.5<D*≤0.8時,為高協調耦合類Ⅲ;④0.8<D*≤1時,為極度協調耦合類Ⅳ。每一類包含四型:①F(x)-G(y)≥0;G(y)-H(z)≥0時,為生態效率滯后型A;②F(x)-G(y)≥0;G(y)-H(z)<0時,為經濟發展滯后型B;③F(x)-G(y)<0;G(y)-H(z)≥0時,為經濟發展超前型C;④F(x)-G(y)<0;G(y)-H(z)<0時,為金融集聚滯后型D。
2.3 空間相關性檢驗Moran’s I統計量
Moran’s I計算公式如下: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的分布特征
分析測算出2005—2015年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綜合值,各省域生態效率和經濟發展呈現非同步特征,生態效率綜合值兼顧了經濟效益和環境資源效益。整體上,省域生態效率存在波動向上的趨勢,但是各省域所屬等級變化比較大,如2005年,生態效率的前五強是北京、西藏、上海、天津和山東,排最后五位的是遼寧、吉林、廣西、湖北和安徽;而2015年,生態效率的前五強變為西藏、天津、北京、上海和青海,排最后五位的變為安徽、湖北、廣西、黑龍江和廣東。
東部省域的金融集聚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域。北京、廣東、上海、江蘇和浙江為金融集聚程度排名前五的省域;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和浙江為經濟發展水平排名前五的省域;貴州、寧夏、海南、青海和西藏為金融集聚排名最后五位的省域;西藏、廣西、云南、甘肅和貴州為經濟發展排名最后五位的省域。
3.2 三元系統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相關性檢驗
本文選用在給定空間單元最鄰近的4個單元的K值最鄰近空間矩陣,創建空間距離權值矩陣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由表2得知,2005—2015年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耦合度的空間自相關Moran's I統計量雖然大部分為正,但是并不顯著,表明三元系統耦合度在空間上并非具有明顯的正自相關關系;耦合協調度均通過5%或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存在較強的空間自相關性,空間溢出性明顯。

表2 三元系統耦合度和協調發展度的空間自相關檢驗Moran's I值
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證實了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溢出效應,接下來采用Moran’s I指數散點圖的局部空間自相關方法檢驗每個省域與周邊省域間的空間差異程度。為了便于對比分析,本文僅給出了2005年、2010年、2015年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耦合協調度(D)的局部空間散點圖,如圖1所示。

圖1 系統耦合協調度的Moran’s I散點圖
局部Moran’s I散點圖將耦合協調度劃分為4種不同象限的集聚模式:①象限中右上的點表示高耦合協調度集聚的省域(高高);②象限中左上的點表示耦合協調度低的省域,這些省域的周圍是耦合協調度高的省域(低高);③象限中左下的點表示低耦合協調度集聚的省域(低低);④象限中右下的點與第二象限的點的屬性剛好相反(高低),表3是2015年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相關模式:2015年我國有9個省域處在右上象限和11個省域處在左下象限,顯示耦合協調度的高度空間正相關性和空間集聚效應,對周邊省域的輻射能力較強;相比而言,只有11個省域處在左上象限和右下象限,表明這11個省域耦合協調度和鄰近省域存在空間負相關性。

表3 2015年省域耦合協調度空間相關模式
3.3 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耦合協調特征
根據系統間耦合協調度以及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識別出我國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耦合協調發展類型。表4列示了2005—2015年我國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耦合協調類型。從大類上看,有失調發展類(Ⅰ),輕度失調類(Ⅱ)和瀕臨失調類(Ⅲ),13個省域屬于失調發展類,12個省域屬于輕度失調類,嚴格意義上只有4個省域屬于瀕臨失調類;從所屬型上看,主要是金融集聚滯后型(D)和經濟發展滯后型(B),生態效率滯后型(A)和經濟發展超前型(C)只在很少省域或早些年份出現,說明多數省域在發展的后期注意到了經濟和生態的協調發展問題,這得益于各級政府的頂層設計和居民環保意識的不斷提高,但是對于多數省域來說,側重點都在于片面追求地方經濟的發展。

表4 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與生態效率耦合協調特征
表4中,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的耦合協調度主要表現為從類Ⅰ到類Ⅲ,只有北京在2005—2007年到達類Ⅳ。在樣本期間內,大部分省域的耦合協調類型都能夠保持相對穩定,如此,將省域耦合協調度的三個等級進行簡要分析。
(1)瀕臨失調發展類
北京、山東、江蘇和廣東屬于這一類。一方面說明全局上,我國內地各省域金融、經濟、生態協調發展狀況不容樂觀,值得重視;另一方面,這4個省市在金融集聚、經濟發展與生態效率協調發展方面表現出了不一樣的特征,北京的環境質量不高,生態效率滯后;江蘇和廣東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山東金融集聚相對滯后,協調發展呈現出金融集聚滯后→經濟發展滯后→金融集聚滯后的特點。
(2)輕度失調發展類
輕度失調發展類的省域有:作為區域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集聚度高,經濟生態發展存在生態效率滯后→經濟發展滯后的特點;經濟發展滯后型的河南、安徽、浙江、河北和四川;金融集聚滯后型的湖北、湖南、福建、遼寧、天津、陜西、內蒙古和重慶,總計14個省域。安徽省在輕度失調和失調發展之間逐年波動變化。
(3)失調發展類
黑龍江、吉林、山西、江西、海南以及其他8個西部省屬于失調發展類,并且無一例外的金融集聚相對滯后,山西在經濟發展滯后和金融集聚滯后兩者之間徘徊。因此從協調金融經濟生態發展的角度考慮,這13個省域要大力促進金融發展。
4 結論
本文利用2005—2015年省域面板數據,運用容量耦合模型和空間統計方法對我國31個省域的金融、經濟與生態三元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況進行實證分析,結論如下:
(1)省域金融、經濟與生態三元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存在趨強的趨勢和耦合協調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協調發展程度普遍不高,說明三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較弱和協調性較低,金融、經濟、生態協調發展任務十分艱巨。對于多數省域來說,當前金融、經濟、生態協調發展的要務是提高金融資源利用效率,可行的推進模式是:金融集聚→經濟發展→生態效率。
(2)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和生態效率系統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都存在明顯的地域性差異,耦合協調度呈現出東部省域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域的特征,并且與省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間對應關系;瀕臨失調發展和輕度失調發展的省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或長江經濟帶,東北部和中西部省域趨于失調發展。說明省域金融集聚、經濟發展與生態效率的協調發展程度和本身的經濟發達程度密切相關,所以對各省域來說,經濟發展是關鍵。
(3)省域金融、經濟和生態三元系統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基本趨同,大體上均表現為同步穩定上升,處于頡抗耦合和中高度耦合協調階段;協調發展度受經濟發展或制度設計中路徑依賴的牽制,短期多數省域維持現狀,金融、經濟和生態建設改革難度較大。
參考文獻:
[1]潘興俠,何宜慶,胡曉峰.區域生態效率評價及其空間計量分析[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3,(5).
[2]羅子嫄,何宜慶,毛華.華東地區金融集聚與經濟發展耦合關系研究[J].企業經濟,2013,(8).
[3]Daly H E.Toward Som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J].Ecological Economics,1990,(2).
[4]Sachs J D,Warner A M.Natural Resou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
[5]Camarero M,Castillo J,Picazo-Tadeo A J,et al.Eco-Efficiency and Convergence in OECD Countries[J].Resource Econ,2013,(55).
[6]劉軍,黃解宇,曹利軍.金融集聚影響實體經濟機制研究[J].管理世界,2007,(4).
[7]王恩旭,武春友.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國省際生態效率時空差異研究[J].管理學報,2011,8(3).
[8]Hellweg S,Doka G,Goran F.Assessing the Eco-efficiency Offend of Pipe Technologie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ost Eco-efficiency Indicator:A Case Study of Solid Waste Management[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05,9(4).
[9]茹樂峰,苗長虹,王海江.我國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與空間格局研究[J].經濟地理,2014,34(2).
[10]蓋文啟,蔣振威,丁珽.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性研究——1978—2008年我國人均GDP發展趨勢實證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0,(9).
[11]陳斐,孫向偉.中國城鄉收入兩極分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分析[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45(1).
[12]白彩全,黃芽保,宋偉軒,何宜慶.省域金融集聚與生態效率耦合協調發展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4,28(9).
[13]付麗娜,陳曉紅,冷智花.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城市群生態效率研究——以長株潭"3+5"城市群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4).
[14]鄧波,張學軍,郭軍華.基于三階段DEA模型的區域生態效率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1).
[15]吳小慶,王遠,劉寧等.基于物質流分析的江蘇省區域生態效率評價[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9,18(10).
[16]吳大進,曹力,陳立華.協同學原理和應用[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