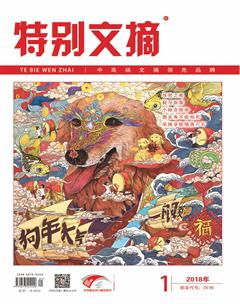別夸張讀書的作用
李妍
新京報:之所以現在關于閱讀的活動很多,“推廣閱讀”的口號很常見,是因為一方面大家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網絡上,讀書的人變少了;另一方面在意識上又認為讀書是一件好事。
陳丹青:當都在說讀書是件好事,已經不好了。19世紀是書的世紀,20世紀頭六七十年,也就是出現網絡之前,人不會說“讀書是件好事”,因為真的都在讀書。
據我所知,還是有很多人看書,我不覺得大幅度減少。愛讀紙質書的人口肯定會慢慢減少,讀報紙和雜志的人絕對大幅度減少,這是真事,所以紙媒比較困難。但書店照樣在開,不少書店倒閉了,可是我每次到書店做活動,瀏覽的人還是蠻多,情形有點像電影院,十年前也是一天到晚說電影院完蛋了,可是現在電影院成了娛樂場,特別火。
我相信這個過程會比較緩慢,再過50年、30年,90后們進入中老年,那時如果書店幾乎消失,我們有理由說:書,包括讀書人,真的退出歷史了。
新京報:現在很多還在堅持閱讀的人,他們自己就會把讀書描述成一件小眾的、有些孤單的事情,這好像是他們真實的情緒和感受。
陳丹青:讀書人早就是“小眾”,并不是網絡出現后。“小眾”指哪些書?要有個范圍。我相信你指的是人文書——文學、詩、哲學、歷史、古典、經典等等。成功書,永遠有人在讀,候機樓內堆滿了成功學的書。人文書從來沒有“大眾”過。
據我的觀察,俄羅斯、英國、意大利、法國、日本,地鐵上不會整個車廂的人都在看手機,至少百分之二三十,或者比例更高的人,拿本書在看。人家也有網絡啊。簡單地說,還是國民整體人文水準的問題。你很難用一個理由,譬如網絡,來推測判斷:啊呀,人不讀書了!
新京報:有什么方法能夠讓更多的人愿意讀書嗎?
陳丹青:我相信兩條:一、出好書,二、好書要設計得好看。人總會喜歡好東西:食物、衣裝、書……現在好看的書太少,好書更少。但我也是在胡說,因為永遠會有一群人——小眾里的小眾——不管世界怎么變化,他天生的樂趣就是讀書。
這樣的怪人未必是所謂的知識分子,也未必讀了“致用”,他就是喜歡。這種人隨便哪個時代都不會滅絕,但你不要指望大多數人都愛讀書。我相信,中國至少有80%的人一輩子不愛讀書,看見書就討厭,但其中有些人絕頂聰明,很會說話,能做大事,卻不太讀書。我就認識好幾個這樣的妙人。
總之,讀書跟智慧、教養、行動、人文水準,不一定是因果關系。魯迅說起民國葬禮上書生們斗挽聯,看誰寫得好,他就說:挽聯做得好,也就是挽聯做得好。同樣,博覽群書,也就是博覽群書。不要夸張讀書的作用,也不要夸張讀書的人群正在消失。
(摘自“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公眾號 圖/陳明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