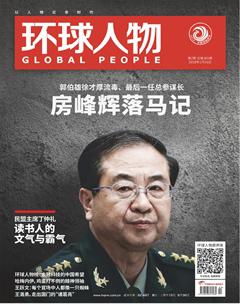陳村:網絡把文學變“瘦”了

2018年1月6日,作家陳村在上海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潘建東/攝)
1954年生于上海。1979年開始發表小說、散文等作品,1985年加入上海作家協會,曾任上海作協副主席。一直關注網絡文學,先后任“榕樹下”網站、 99書城網站藝術總監。2014年7月,擔任上海網絡作家協會會長。自2016年開始,主編電子雜志《網文新觀察》。
作家陳村的眼睛出了毛病,一年前剛剛動完手術,但這并不妨礙他仍然整天泡在網上。每天一醒來,他的習慣是先把電腦打開——若晚上下載東西,電腦則整夜不休。他在網上閑逛,發發微博,偶爾看看電影和直播,“也會寫一些雞零狗碎的東西,但很少寫所謂的作品了。”
更多的時候,陳村在為一份網絡文學批評類電子刊——《網文新觀察》忙碌。自2016年創刊起,這份雜志磕磕絆絆運行了兩年。作為主編,他事事過問,樣樣操心。
“那么多網絡文學,總要有人去觀察、去研究它的歷史、現在和未來。和傳統文學一樣,網絡文學也需要批評。”陳村拿出手機,給《環球人物》記者發過來一個《網文新觀察》電子刊的鏈接。最新一期是輕小說專輯,所謂“輕小說”,他解釋說:似乎跟現實題材較為疏遠,有幻想的意味,青睞異次元,有年輕文化的屬性。
關于中國的網絡文學,人們習慣以“榕樹下”網站的創立為起點。1997年12月25日,美籍華人朱威廉用自己在商海掙下的錢作為資本,創立“榕樹下”,開啟了網絡投稿的渠道,一代網絡文學青年的集體記憶由此展開。走到今天,網絡文學正好跨過20個年頭。
20年間,陳村是網絡文學的目擊者,也是幕后推手。從1999年加入“榕樹下”網站,任“躺著讀書”論壇版主,到“小眾菜園”的村長,再到上海網絡作家協會會長,網絡文學發展的每一個節點,他都密切注視著。

2001年12月,“榕樹下”成員一起聚會,那一次被認為是“最后的晚餐”。圖為“榕樹下”創始人朱威廉(左)和陳村。
“榕樹下”的網絡文學實驗
陳村觸網是在1997年,中國大陸互聯網對公眾開放一年后。有一次他從一家郵局經過,門口很熱鬧,原來正在推廣上海熱線。經不住工作人員勸說,他當場交了100塊錢,注冊了一個用戶名。
“上網得靠電話線,有一個‘貓嗚哇嗚哇地叫著,接通后才能上。”陳村回憶說。當時網速很慢,圖片只有指甲蓋大小,有時還打不開。因為按分鐘計費,他舍不得在線看,就打開網頁把文章一篇一篇存下來,然后斷網下線看。
第二年,“榕樹下”在朱威廉的經營下異常火爆,引起很多文學青年的關注。1999年8月,上海榕樹下計算機有限公司成立。一批作家被邀請來觀禮,其中就有陳村、趙長天(《萌芽》雜志主編)等。之后,“榕樹下”的工作人員找到陳村,問他要不要加入,經過幾番思索,他同意了。
“我當時就一個想法:想要知道網絡介入文學后,文學會變成什么樣子。”陳村說。他被委任為 “榕樹下”的藝術總監,用他的話說就是個“不管部部長”——不負責流程上的事務,主要是外聯。
朱威廉找陳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文壇有人緣,足可召喚、聚集起一批知名作家。在此之前,陳村已是中國文壇黃金時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上世紀80年代,他因在《上海文學》發表小說《兩代人》《我曾經在這里生活》而成名,和王朔、余華、馬原等都是好友。
陳村也果然不負眾望。1999年,“榕樹下”舉辦首屆網絡文學大賽,作家阿城、王朔、賈平凹、王安憶等都被他拉來當評委,一時之間轟動文壇。
“傳統文學作家平常都不看網絡文學,但評選時沒有人說看不起網絡作家。而且當時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的界限并不明顯,評判標準也差不多。”陳村說。那一次,獲得小說頭獎的是《性感時代的小飯館》,作者是蔣方舟的母親尚愛蘭。
“榕樹下”漸漸聚集了一批文學愛好者。寧財神、李尋歡、邢育森,號稱“榕樹下”的“三駕馬車”,安妮寶貝也在那里有一個工作室。陳村至今還記得辦公室里氣氛很好, “有的地方隔成幾個小房間,安妮寶貝他們三五個人就在一個小房間里辦公。寧財神坐在門邊,負責網頁設計。他是色盲,我有時嘲笑他‘色盲還做美工,他也不生氣,就笑笑。”
陳村還在“榕樹下”辦了一個“躺著讀書”的論壇,自任版主。初衷是在交流讀書中“求趣、求友、求情、求知”,但事與愿違,論壇上各色人等出沒,異端言論甚囂塵上,嚴肅讀書者卻未能受到關注。面對各種爭吵和喧鬧,他不得不貼出“陳村如何刪帖”的告示,又招來唾沫磚頭橫飛。
3年后,朱威廉的資金鏈無以維系,只能將網站賤賣。2002年2月5日,貝特斯曼集團宣布收購“榕樹下”。當天,陳村在網上貼出文章《告別榕樹》:“我相信,網文自有它的生命力,網站自有它的命運,網民的集體意志才是榕樹的根基。”
“榕樹下”的命運發生轉折,安妮寶貝、寧財神等各奔東西,之后紛紛出書,不再自稱“網絡寫手”。陳村也撤銷了個人主頁《看陳村看》,當時他的期望是:回歸一個傳統作家的本色——閱讀經典,勤奮寫作,我行我素。

當年“榕樹下”捧紅了許多網絡寫手,安妮寶貝是其中之一。
“小眾菜園”的美好時光
然而陳村并沒如他所愿回歸傳統,而是繼續混跡于網絡。先是以“陳村在上海”為網名,活躍在天涯社區“閑閑書話”上,發一些讀書隨想、文化評論等。2004年,他加入“99書城”,還是任藝術總監,在那里開辟了一個“小眾菜園”。
“開園的目的是勸誘潛水隱居的名士高人來此種菜、獻藝。”陳村說,這一次他吸取之前論壇的教訓,自己挑選 “種菜”人——凡是要加入論壇成為“菜農”,必須實名,且要經過陳村本人的許可。有人毛遂自薦,也有人通過朋友舉薦。
“小眾菜園”很快聚集了一批“菜農”, 最多的時候有300人,其中有作家、畫家、教師、記者、工程師,還有機關干部,當年“榕樹下”的“老人”趙波等也來這里“種菜”。
和天涯、“榕樹下”相比,“菜園”上活躍人數并不算多,但也熱熱鬧鬧,生機勃勃。作家葉兆言每天醒來都會看看“菜園”上發了什么,批評家吳亮是一個勤奮的“菜農”,一直在上面寫。還有一位奇特的“菜農”——自稱“除了要吃飯其他跟神仙一樣”的畫家朱新建,留下了許多精彩的文字和繪畫。
2006年,在網友的介紹下,李娟也成為“菜農”。當時她已出版《九篇雪》,陳村拿來讀,“她的文字很特別,這樣的文字是教不出來的。”陳村還引薦李娟在《文匯報》上開專欄,接下來她的書便一本一本地出,由此成名。
作家余華不泡論壇,偶爾會到“菜園”逛逛。他的小說《第七天》寫好后,先發了一章給陳村,后經授權被轉載到“菜園”上,“出現了大量批評性文字,大家在一起討論,但不罵人。”陳村說。
除線上的爭論和互動外,“菜農”們還常常在線下聚會。陳村記得連著好幾個春天,他和上海的幾個“菜農”約好到野外踏青。也有去外地的時候,2006年春,一幫人開著三輛車去南京,找朱新建;2007年,陳村又帶著幾個“菜農”開到烏鎮,拜訪木心先生,和木心吃飯,聊天。
“小眾菜園”維持了8年,2013年被關閉,曾有一段時間遷移到上海弄堂網,后來弄堂網也沒了,陳村的網絡文學實驗宣告失敗。
如今再回憶,陳村覺得那是“一個比較理想化的論壇”,“現在去看,至少有好的文字、好的圖片和好的畫留下來,這就夠了。”
網絡文學精神:匿名,愉快,不圖名利
當陳村帶著一批人在“小眾菜園”耕耘時,外面的網絡文學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榕樹下”幾經倒賣,漸趨沒落,新版“榕樹下”從2017年6月起,因網站維護停止更新。另一個新興網站起點中文網,先是在2003年開啟網絡付費閱讀新模式,后來被盛大文學收購。到了2017年,騰訊文學和盛大文學又聯合成立閱文集團,建成中國最大的網絡文學平臺。
《環球人物》:網絡文學走過的這20年,在您看來,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
陳村:如果粗略地分,可以將網絡文學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免費階段,像“榕樹下”初期那樣散漫、自發地寫作;收費階段,各種網絡文學類型快速生長,比如玄幻、奇幻、仙俠、穿越、宮斗等文本出現。與此同時,也會有像金宇澄的《繁花》、吳亮的《朝霞》等,這樣的嚴肅文學作為補充,還有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等上面的內容,一起構成今天的網絡文學。
《環球人物》:您一直對網絡文學寄予厚望,但最終好像還是失望了。
陳村:網絡文學最好的時代已過去。那是上世紀90年代,那時網絡的初心是不功利的,是老子所說的赤子之心,嬰兒的狀態。我還記得1998年,當時聽人說痞子蔡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很火,就跑到網上找來讀。它的確很吸引人,痞子蔡用一種網絡化的語言,以歡快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悲劇的故事。
更早的時候,還有一個北美留學生,網名叫圖雅,在網上寫在北京生活時的趣事,在華人圈廣泛流傳。后來出了書,編輯呼叫他領稿費,都始終沒有回音。這才是真正的網絡文學精神:匿名,愉快,不圖名利。
《環球人物》:那您如何看現在的網絡文學?
陳村:現在的網絡文學,在資本的推動下,把文學做大很好,但也“瘦”了——文學本來是海納百川的,有文學批評、散文、詩歌、雜文、小說,但如今卻是類型文學一枝獨秀。
另一方面,曾有一種趨勢,都把出版紙質書作為網絡文學的最高成就。如此一來,還有什么網絡文學呢?網絡文學的自由、隨意、不功利,已經被污染了。雖然我很理解這樣的變化,但是終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環球人物》:您會去看網上那些類型小說嗎?
陳村:我很少去看,只有在需要關注現象和趨勢時,才去翻上幾頁。我覺得死抱著類型小說“會死”。比如有一陣子盜墓小說很火,一下子就冒出很多,你可以寫上10年,但能寫20年嗎?一篇兩篇看下來都差不多,沒有人會一直愿意看下去。當然也會有新的類型出現。
《環球人物》:但網絡文學還有其存在的意義。
陳村:當然。網絡的存在,使得文學更加親近大眾——它可以隨時隨地和你發生關系,我覺得,以后的文學甚至可能都是網絡文學,因為文本的生產和消費都是在網上發生。
《環球人物》:那么在您看來,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有何不同?
陳村:我以前老覺得它們是一樣的東西,現在覺得不是。它可能真的是出現了轉折,就像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折。也許你曾經看不起的很多東西,包括不講究的文字、很水的敘事,慢慢變成了某種很自然的狀態,變成當然的了。不過,從根本上來說,文學是寫人的,它是用文學的手法研究人生,加深我們對人的認識,在這一點上,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沒有區別。
《環球人物》:您能預測一下網絡文學未來會是怎樣的嗎?
陳村:我不清楚,所有的預測都是不準的。網絡文學界雖風風火火,IP賣點大增,但近年流傳著一種恐懼:好時候會不會是壞時候的開始?人們會不會將興趣轉移到表演性的東西上去,比如視頻、直播等?文學永遠不滅,但它面對的大眾是否會背轉身去?這些,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