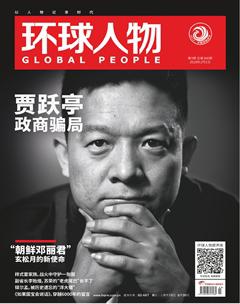《如果國寶會說話》,穿越6000年的留言
毛予菲
徐歡
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制片人,紀錄片導演。自2005年起制作了《故宮》《我從漢朝來》等紀錄片。2018年元旦,由她擔任總導演的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在央視紀錄頻道首播,廣受好評。

2018年1月19日,徐歡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侯欣穎/攝)
剛坐下,徐歡就主動打開了話匣。她沒有開門見山地聊自己的新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而是先提到了書寫“邊疆文學”的女作家遲子建。遲子建有本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以鄂溫克族女酋長柳芭的口吻,講這支弱小民族的百年滄桑。徐歡說,兩天前她在無意中得知,觸動遲子建寫這本小說的,原來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有著相似經歷的孟金福,中國鄂倫春族最后一位薩滿,他在深林中帶著對天地萬物最虔誠的敬畏,過著近乎原始的生活,而他的后人則在山腳下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與從小生長的土地產生了隔膜……
孟金福的堅守與執著,曾被徐歡的同事、央視導演孫增田拍成紀錄片《最后的山神》。這兩天,徐歡又翻出這部紀錄片。看完之后,她感慨于柳芭與孟金福的命運,更敬畏于這些“捍衛者”們內心強大的力量。
這些感觸,也正是徐歡在《如果國寶會說話》中,寄寓于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深意。《如果國寶會說話》由她擔任總導演,于2018年1月1日在央視紀錄頻道首播,分100集講述100件文物的傳奇。“從中華文明探源到大眾審美普及,從遠古陶器到明清字畫,那是我們認知歷史的物證,還有對祖先與文明的致敬。”
嚴肅恢弘的思考之外,徐歡很喜歡片中一句“文藝范兒”解說詞,分集導演寫給文物鸮(音同肖)尊的: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從高貴到不祥再到呆萌,貓頭鷹一直就是那個貓頭鷹,可人心變了好多回了。“我也想說,我拍或不拍,文物都在那里,但當你走近了看懂了,便會發現:時間是個有意思的事情。”徐歡說。
用文物打開歷史
《如果國寶會說話》每集僅5分鐘,“孵化”卻歷時整整兩年,讓主創團隊“掉了一層皮”。從搜集到篩選,團隊經過學習、研究、走訪、勘察后,380多萬件文物最終只留下100件。徐歡選文物的標準很明確:中國上下五千年文明中的坐標,展現大歷史的轉折與大文化的創造。
在這個標準下,商代后母戊大方鼎、古蜀國三星堆青銅人像、北宋《千里江山圖》,這些明星級別的國家寶藏入選,當然毫無爭議。但在第一集中,代表仰韶文化的“人頭壺”,入選時只是一件默默無聞的陶器。

第一集《人頭壺:最扔的凝望》截屏,一張來自5000多年前的“呆萌臉”。
汪喆負責人頭壺這一集的拍攝制作,她是個細膩敏感的女導演。“當時需要找一件新石器時代的文物,我們基本鎖定陶藝制品。徐導和我看了很多張陶像臉譜,它們有的猙獰,有的夸張,有的甚至有點丑陋。后來我們在一本文物雜志上看到這件人頭壺,第一眼就被這張嘴唇微微上翹的臉打動了。這件文物屬陜西半坡博物館,當時被借展到新疆烏魯木齊附近的一個縣級市。我們匆匆駕車趕到那座文化園區,人頭壺安靜地佇立在展廳,偶爾有三兩個觀眾稀稀拉拉路過展臺。從陜西一路追到新疆,終于見到那張微笑的臉,我覺得它特別孤獨。”
汪喆帶著團隊架好攝像機,拍這張45度仰望天空的臉,但從四平八穩的鏡頭里,只能看見它的下巴頦兒。她調整了角度,讓攝影機也歪著“腦袋”,與人頭壺的眼睛對視。在鏡頭里,汪喆呆呆地看著這雙眼睛,一瞬間感受到了6000多年前,人類在剛剛學會使用器具時所創造的文明。觸動之下,她立馬給遠在北京的徐歡發了一條微信,徐歡被她的文字打動了。“我們就拿它來做第一集吧,用這張平凡又呆萌的面孔開篇。”
于是,這件在公眾認知內知名度不高,留下的文字記錄也寥寥無幾的陶器,成了整套紀錄片的第一集。蔚藍而蒼茫的混沌中,一片星辰粲然升起,人頭壺仰望星空。“我們凝望著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顆心跨越時空,望見生命的力量之和……6000年,仿佛剎那間,村落成了國,符號成了詩,呼喚成了歌。”
而對于那些毫無疑問入選紀錄片的典藏級國寶,最難的是方向和立意。“可以寫的東西太多了。但片子只有5分鐘,到底該講什么?又能講什么?”這些問題,一度成為徐歡和團隊的最大難題。
分集導演馮雷給《環球人物》記者講述了第十一集《婦好玉鳳:鳳凰傳奇》的定稿過程:“最初我們想表達的是,鳳文化如何貫穿中華文明。但之前《紅山玉龍:尋龍玦》那集已經講述了龍的誕生和延續。組內幾個人一討論,這不行,龍與鳳這兩集的脈絡應該區分開來。輾轉之下,我們把視線聚焦到玉鳳的收藏者、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或許這位傳奇女性,就是鳳‘女性形象的最佳代言人。最終在前后換了6個方案,改了20個文案后,我們定了稿:以玉鳳引出婦好墓,再以墓中其他文物,講述她的一生。”正如解說詞:“玉鳳恰似她優美的風姿,定格在歷史的風景線上,為后人所景仰。”
負責統籌的總導演徐歡,將100件文物的解讀維度分為:考古、歷史、社會、科技、哲學等。“或許5分鐘的片子深度不夠,但它們各有立意。”她希望《如果國寶會說話》能成為索引和通道,為觀眾打開一扇窗,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讓他們隔著時間與空間,傾聽文物自己訴說傳奇。
有溫度地敘說
《如果國寶會說話》每集都有同樣一句開場白:“你有一條來自國寶的留言,請注意查收。”在年輕人聚集的嗶哩嗶哩視頻網站上播出時,彈幕“已查收”刷了屏。今年1月1日,《如果國寶會說話》在嗶哩嗶哩“央視綜藝官方”賬號播出,截至第一季25集完結,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累積了130萬的點擊量和3萬條彈幕。徐歡說:“過去在電視上播,我們只知道收視率,如今在網站上,觀眾有更具體的表達。他們喜歡什么,吐槽什么,都給了我們全新的體驗。這幾天,我們正在收集這些反饋,為后三季做準備。”
《如果國寶會說話》收獲了大批年輕粉絲,這在團隊的預料之中。紀錄片制作時,他們就很用心地注入了一些年輕元素。比如解說詞中會不時蹦出一兩個網絡用語。出自新石器時代的陶鷹鼎是一只健碩的雄鷹,它有個渾圓的大肚子,被形容為“肌肉萌”。考古學者楊兆凱是主創團隊的專家顧問,他第一次看片后,覺得有些出乎意料:“輕松的基調有點超過預期。不過這樣挺好,和陳列在博物館里、聚光燈下冷冰冰的文物相比,它們在鏡頭前變得活潑。這是年輕人喜歡的東西。”
紀錄片的海報文案也走“萌系”路線:“這款美瞳我要了”(太陽神鳥金箔)、“因為刻骨所以銘心”(甲骨文)、“說我像奧特曼的你別走”(三星堆青銅人像)。徐歡說:“文物背后能發散傳播的點,我們都提前規劃,做好二次傳播。”
但徐歡不希望人們因為形式的輕松,而將內容看得淺顯。“5分鐘短視頻符合人們碎片化的觀看習慣,但這并不意味著,紀錄片也是瑣碎的。《如果國寶會說話》以歷史紀年為脈絡,是一個有規劃、有立意的整體”。
徐歡覺得,文物的溫度不在于文案里是否有一兩句頗具萌感的句子,更和它的傳播形式沒有關系。“拍攝完成后,幾個分集導演跟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最初站在國寶前,懷抱著一顆無限敬畏之心。一年多下來不停看不停拍,琢磨透了,它們親切了起來。當你走近,當你了解,你會知道它們的故事,聽到它們的呼吸,讀到它們留下的跨越千年時光的留言。”
這些文物里有古人與今人的聯系,讓徐歡印象深刻的是第十四集《何尊:這里有中國》。這件青銅尊被安排在國寶最高展臺上,造型凝重又雄奇。尊內底部刻有銘文——剛剛繼位5年的周武王之子姬誦,與同宗的貴族何,討論父輩與新王的功績。在這122字銘文中,出現了“宅茲中國”四個大字,這是考古學家第一次在文本中發現了“中國”。“這些寫給祖先的文字,更像是寫給數千年后13億多中國人的信。” 何尊放到今天來解讀,依然能讓人感受到文化的認同與共鳴。
還有一些文物凝結了古人的智慧。第三集《陶鷹鼎:陶,醉了6000年》介紹陶器燒制技藝,其中蘊含著生活的哲理:陶,是時間的藝術,泥土太干則裂,太濕則塌,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們需要等,等土干、等火旺、等陶涼。徐歡感慨良多:“今天的我們總感嘆生活太快、時間不夠用,原來6000年前,古人就已經教給我們,如何與時間融合,如何與時間不較勁。假如陶鷹鼎會說話,它也許會告訴我們它在熔爐內外的那些日日夜夜吧。”
和文物對話需要好奇心
這兩年市場上出現了不少文化類節目,但徐歡自始至終都對自己團隊的作品信心滿滿,“我們不跟風,按自己的節奏來。這與市場無關,而是與愛好有關系”。
這些年,徐歡一直在熱鬧的電視圈里。她曾親歷中國電視新聞評論節目的黃金時代。1993年,她在“開風氣之先”的《東方時空》任編導,《實話實說》《世界》《面對面》這些央視老牌談話節目的背后,也都有她的身影。2003年,臺里的新聞中心成立特別節目組(后獨立為央視紀錄頻道),“希望有一些新嘗試”的徐歡加盟。在這里,她一路從文案撰寫做到總策劃、總導演,制做了不少文化類紀錄片,包括《故宮》《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等。在與這些博物館打交道的過程中,她體會到了文物的魅力。
工作之外,徐歡也常去博物館,無論多忙,都會抽空享受與文物的獨處時光。“文物是歷史的物證。”透過這些物證,她希望讓大家看到背后造物的人,理解器物與時代的關聯。而這些物與人扎根的沃土,就是中華文化的源頭。
《如果國寶會說話》開播前發生了一件小事,讓徐歡很有感觸。她帶著主創團隊來到宋慶齡兒童發展中心,為四、五年級的小學生辦了一場交流活動。“沒有一個孩子詢問這些文物值多少錢,而是都有自己的思考。有個小女生,指著胖嘟嘟的陶鷹鼎問我們的分集導演:為什么正經的古人,會做出這樣不正經的文物?她的思考是:古人一板一眼的,制作出來的也應該是像司母戊鼎、四羊方尊那樣嚴肅、沉重的大物件。”
徐歡覺得,這是對歷史的誤解。“古人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像‘我們自己。在創造某件物品的時候,他們的訴求和情趣與現在的我們沒有什么區別,只是因為眼界的差異,使用的方法不一樣而已。或許和文物對話,我們需要更多的好奇心,從詳實的考證出發,融入當代人的認知,甚至可以有一些帶主觀色彩的想象力。”正如網友在視頻下的留言:考古就像做一道閱讀理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