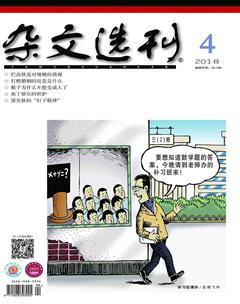我們不擅告別
2018-04-11 02:38:02黎弋
雜文選刊
2018年4期
黎弋
爸爸的癌癥,已經到了末期,每天抽胸水、輸營養液、止痛,周而復始。早晨,睡意朦朧中,冰冷的鋼針就插進爸爸體內抽血。床位前的記事板上,護士寫上爸爸這天要輸的液體,這是爸爸一天的生活主線。
爸爸有點煩躁,對我說:“我想回家。”他大概是想念他養在陽臺上的鳥,他想念那個連棉芯都露出來的破沙發,還有那臺落伍的舊電視。他想念自己可以任意起床、睡覺的空間,更準確地說,是那種自由的空氣。
去醫生那里試問,醫生說:“回家?他隨時都會猝死。”這是實話,脫落的癌組織已進入血管,形成癌栓,一周內,爸爸已經心梗過兩次。
我自己也不能適應任何一種紀律下的生活。我五歲的時候,爸爸給領導送禮,開后門把我送進了廠部幼兒園——那是全市試點的全托幼兒園,條件極好,當時甚是熱門。我去的第一晚,在小鐵床上輾轉難眠。隔壁傳來其他小朋友輕輕的呼吸聲,半夜我不敢去尿尿,直到憋得膀胱脹滿,才匆匆跑去。倉促中,襪子都被尿濕了,我就穿著濕襪子睡到天亮。爸爸來看我,我就一直哭,我說:“我想回家。”爸爸飛快地幫我辦了出園手續,用二八自行車載我回家了。我坐在車子的大杠上,如鳥出籠,快樂無比。
可是這次,我卻沒法帶爸爸回家了。
癌魔侵犯了爸爸的胸膜, 它像跋扈的蒙古大軍,沿著淋巴和血管,四處侵犯。爸爸的胸水,抽得越來越頻繁,化驗找出癌細胞之后,醫生說胸水不需要抽了。為了省下一次性水袋的錢,醫生讓我們直接用管子將胸水接到尿壺里,然后再倒進馬桶沖掉。……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