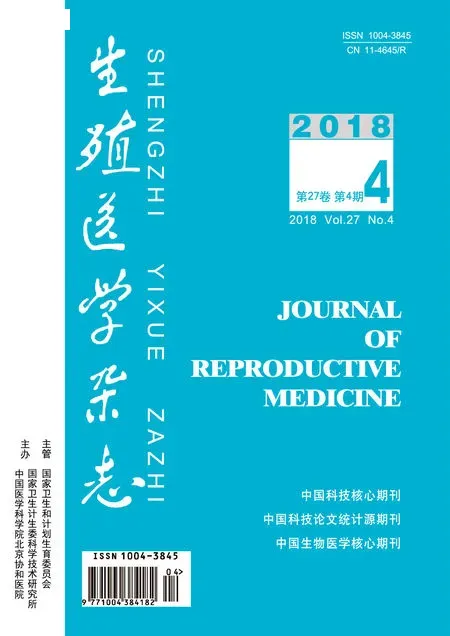個體化劑量長方案降調節在IVF-ET中的應用
龍惠東,鄧偉芬,王鳳
(深圳武警醫院生殖中心,深圳 518000)
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技術發展至今,促排卵方案已呈現多元化的局面,包括長效長方案、短效長方案、拮抗劑方案、微刺激方案、黃體期促排等,以期在不同的人群中應用達到最佳的促排效果及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經典的長效長方案因其應用方便、卵泡發育同步性好、周期取消率低等優點,目前仍是應用最為廣泛的方案。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有不同的藥物劑型、用藥途徑及用藥方案,使周期啟動更靈活。短效劑型(0.1 mg)需患者每天注射以維持有效的藥物濃度,治療麻煩且費用較高;長效制劑使用更方便有效。長效GnRH-a的標準計量為3.75 mg,這一設計主要用于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激素依賴型癌癥及子宮肌瘤[1],但在輔助生殖治療中使用全量甚至半量(1.85 mg)都會顯著增加促性腺激素(Gn)的用藥時間及劑量,影響臨床妊娠結局,增加患者的經濟及心理負擔。長效GnRH-a根據其使用劑量的不同,臨床應用方案多元化,各種不同劑量的降調節方案在不同人群是否都能達到理想的妊娠結局有待進一步評估。本文通過回顧性分析本中心2015年1~12月不同劑量降調節方案的周期參數,評估個體化劑量長方案降調節的有效性。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選擇2015年1~12月在本院生殖中心進行IVF-ET治療的不孕不育癥夫婦為研究對象,共3 639個周期。納入標準:女性患者年齡≤40歲,基礎竇卵泡數(AFC)>5個,抗苗勒管激素(AMH)>1.1 ng/ml。不育原因包括輸卵管因素、男方因素、盆腔粘連、子宮內膜異位癥、排卵障礙及不明原因不育等。排除標準:以博洛尼亞標準診斷為卵巢低反應患者。
二、促排方案
根據患者的年齡、卵巢儲備功能、體重指數(BMI)和既往促排歷史,按照臨床經驗選擇降調劑量。AFC≤10個者予低劑量(0.5~1.1 mg)降調節,結合患者AFC、AMH及BMI給予降調劑量:AFC 5~6個、AMH 1.1~1.5 ng/ml者予0.50~0.70 mg;AFC 7~8個、AMH 1.6~2.5 ng/ml者予0.75~0.80 mg;AFC 9~10個、AMH 2.5~3.5 ng/ml者予0.90~1.10 mg;正常反應者(AFC>10個,AMH>3.5 ng/ml)及高反應人群(AFC>30個,AMH>15 ng/ml)予常規劑量(1.25~1.40 mg)降調節;既往常規劑量降調不全(啟動日竇卵泡直徑>5 mm,FSH、LH、E2達不到降調標準)或輕度子宮內膜異位癥者予1.80~2.50 mg;或合并中重度子宮內膜異位癥者或腺肌癥者予3.75 mg降調節,以上分組根據BMI具體稍做調整。黃體中期使用長效GnRH-a(達菲林,Triptorelin,博福-益普生,法國)肌肉注射進行垂體降調節。根據GnRH-a劑量的不同分為:A組(41個周期)0.50~0.75 mg,B組(589個周期)0.75~0.80 mg,C組(64個周期)0.90~1.10 mg,D組(2 873個周期)1.25~1.40 mg,E組(41個周期)1.80~2.50 mg,F組(31個周期)3.75 mg。A~D組患者降調后14~16 d回診,E~F組降調后25~28 d回診,達到降調標準后開始使用FSH(果納芬,默克-雪蘭諾,德國)100~300 U/d誘導卵泡發育。理想的降調標準為FSH<5 U/L、LH<5 U/L、E2<183 pmol/L、竇卵泡直徑均≤5 mm、子宮內膜厚度≤5 mm、孕酮(P)<2.54 nmol/L。促排卵過程采用陰道超聲檢查和血清激素水平監測,當2~3個主導卵泡徑線≥18 mm,當晚20~21時予HCG 6 000~10 000 U肌肉注射扳機,36 h后取卵。
三、IVF-ET
取卵后進行體外培養和授精,男方嚴重少弱精癥者行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ICSI)受精,取卵后48~72 h進行ET。獲卵數≥20個或HCG日P>4.76 nmol/L或E2水平連續兩天>14 640 pmol/L時采取全胚冷凍,取消鮮胚移植。取卵后第2次月經第3天視卵巢恢復情況安排凍融胚胎移植(FET)。移植后采用HCG 2 000 U隔日肌肉注射或黃體酮40 mg每日肌肉注射或陰道栓劑行黃體支持。移植胚胎后第14天測定血清β-HCG,第30天進行陰道超聲檢查,B超顯示有孕囊和胎心搏動者確定為臨床妊娠。
四、觀察指標
降調節后啟動日及HCG日測定血清LH、E2、P水平,血清性激素水平檢測采用美國貝克曼全自動化學發光免疫分析儀。統計HCG注射日Gn總用量、獲卵數、MⅡ卵母細胞數(以ICSI周期為準)、正常受精率(2PN數/IVF獲卵數或ICSI的MⅡ數)、卵裂率、可利用胚胎率及優胚率。統計取卵后首次移植的臨床妊娠率、流產率、著床率及活產率,妊娠率=妊娠周期數/移植周期數×100%,流產率=流產數/妊娠周期數×100%,活產率=活產周期數/移植周期數×100%。
五、統計學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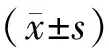
結 果
一、各方案組患者基本情況比較
A組患者年齡顯著高于其余各組(P<0.05),A組及B組的AMH值顯著低于其余各組(P<0.05),A組、B組及C組AFC數顯著低于其余各組(P<0.05),A組及B組基礎FSH水平顯著高于D組及F組(P<0.05),D組及E組LH水平顯著高于A、B、C組(P<0.05)。不育年限、BMI、基礎E2水平在各組間無顯著差異(P>0.05)(表1)。

表1 各組患者基本情況及血清激素水平比較(-±s)
注:與其余各組比較,aP<0.05;與D、F組比較,bP<0.005;與A、B、C組比較,cP<0.05
二、各組降調節程度及Gn用量比較
啟動日各組激素水平無顯著差異(P>0.05)。HCG日LH水平A組及B組顯著高于D組及E組,HCG日E2水平D組顯著高于A組、B組及C組,HCG日P水平D組顯著高于B組(P<0.05)。Gn總用量各組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表2)。
三、各組患者IVF-ET周期實驗室情況比較
A組、B組及C組獲卵數顯著少于其余3組(P<0.05);ICSI的MⅡ卵母細胞率各組間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IVF-2PN率E組顯著低于B組、C組及D組(P<0.05);可利用胚胎率F組顯著低于其余各組(P<0.05);ICSI-2PN率、卵裂率及優胚率在各組間無顯著差異(P>0.05)(表3)。
四、各組妊娠結局比較
全胚冷凍率D組顯著高于B組及C組(P<0.005);首次移植臨床妊娠率B組顯著低于D組(P<0.005);著床率D組及F組顯著高于A組及B組(P<0.05);活產率B組顯著低于C組及D組,E組顯著低于C組(P<0.05);平均移植胚胎數及流產率在各組間無顯著差異(P>0.05)(表4)。

表2 各組降調情況與Gn使用量比較(-±s)
注:與D、E組比較,aP<0.005;與D組比較,bP<0.005

表3 各方案組患者IVF-ET周期實驗室情況比較 [(-±s),%]
注:與D、E、F組比較,aP<0.05;與B、C、D組比較,bP<0.05;與其余各組比較,cP<0.05

表4 各方案組患者IVF-ET周期妊娠結局比較 [(-±s),%]
注:與B、C組比較,aP<0.005;與D組比較,bP<0.005;與A、B組比較,cP<0.05;與C、D組比較,dP<0.05;與C組比較,eP<0.05
討 論
GnRH-a是具有很強生物活性的九肽化合物,與垂體前葉腺體的GnRH受體有很高的親和力,具有較長的半衰期,結合后可刺激分泌FSH及LH“一過性升高”(“flare up”)效應,持續作用7~10 d后會引起GnRH受體減少,進而內源性的GnRH不能再刺激產生FSH及LH,隨著時間的延長,FSH、LH降至基礎值以下,呈藥物去垂體狀態,卵巢內卵泡停止生長和發育,體內的雌激素水平處于卵泡早期甚至達絕經期水平,實現降調節[2]。自1984年Porter等[3]首次引入GnRH-a用于IVF-ET以來,GnRH-a一直被廣泛應用于垂體降調節-卵巢促排卵中。早期曾提出半量的GnRH-a足以抑制早熟內源性LH峰,降低周期取消率,改善卵巢反應[4]。隨著現今IVF-ET技術的發展,發現降調節方案的應用可以多元化,在不同人群應用不同劑量的降調節,加上恰到好處的促排用藥,可實現良好的妊娠結局。理想的降調節是個體化應用GnRH-a制劑,使垂體脫敏,既可抑制LH峰的早發,但又不過度抑制卵巢對Gn的反應,以獲得優質的卵母細胞、胚胎和良好的妊娠結局。本文通過綜合評估患者的年齡、BMI、AFC、基礎FSH水平及既往促排歷史,給予不同人群不同劑量的降調方案,結果顯示均能獲得理想的降調節狀態,結果與張學紅等[5]報導的結論相似。
由于降調節有劑量依賴性和時間依賴性,大劑量的GnRH-a對下丘腦和垂體產生過度抑制,導致卵巢低反應及增加Gn用量,過低劑量的GnRH-a又會出現降調不全導致早發LH峰出現,影響妊娠結局[6]。早在1996年Broekmans等[7]探討了GnRH-a降調節的劑量效應,發現降調的劑量依賴性主要以LH表現明顯,FSH無劑量依賴性。本文發現,基礎LH在高反應人群(D、E組)中更高,而HCG日的LH水平在A、B組反而更高,提示跟降調劑量有關。促排期間LH的水平過低會影響卵泡發育、卵母細胞質量及受精率[8];LH還可直接作用于子宮內膜LH受體,支持內膜的發育[9],LH過低會降低子宮內膜的容受性,所以LH對于促排期間卵泡正常發育和內膜容受性都至關重要[10],卵泡期稍高的LH水平對高齡或低卵巢儲備患者可能更有利。因此,尋找合適劑量的個體化的降調劑量對提高IVF-ET的妊娠率至關重要。
李潔等[11]曾報導0.375 mg低劑量的降調會出現降調不全而出現早發LH峰案例。因此本中心最低劑量降調是0.5 mg(A組),用于高齡或竇卵泡數較少的患者,未發現有早發LH峰現象。A、B、C組的獲卵數顯著減少,通過年齡、AMH、AFC及基礎FSH的數據反映出是由于自身卵巢儲備下降所致。A、B組的臨床妊娠結局稍差于其他組特別是D組,分析原因與該組患者年齡增大及卵母細胞質量下降有關。大劑量降調可使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的盆腔內環境得以改善,有利于改善卵母細胞質量及子宮內膜容受性,但F組的獲卵數及著床率與D組相當而可利用胚胎率卻低于D組,E組的活產率也低于C組,其原因可能是因子宮內膜異位癥所致。張雯碧等[12]報導子宮內膜異位癥主要通過影響卵母細胞質量間接影響胚胎質量,與卵母細胞的線粒體結構異常及線粒體數量減少、DNA復制減少、卵母細胞質量下降有關,可能與卵母細胞發育的微環境(卵泡液)氧化應激反應相關;郭藝紅等[13]報導應根據不同類型內膜異位癥特點制定不同方案,提示子宮內膜異位癥人群可能需要更加細化的降調方案或連續多次降調節,而本文納入對象僅為一次降調的患者。常規劑量1.25~1.40 mg方案適用人群最廣,常用于卵巢儲備正常或者儲備高的多囊卵巢綜合征(PCOS)患者,D組的實驗室結果及臨床結局都較理想,但全胚冷凍率偏高,主要由于獲卵數較多,HCG日的E2及P水平更高,特別是PCOS患者。Chen等[14]報導PCOS患者凍胚移植的妊娠結局比鮮胚移植更佳,提示全胚冷凍及后期凍胚移植可能是高反應人群獲得理想妊娠的更佳治療方案。促排期間的Gn用量與卵母細胞的發育潛能及子宮內膜容受性的關系最近也開始受到關注。有文獻報道過高的Gn量會導致活產率下降[15-16]。本文統計發現,通過使用不同劑量的降調節方案可避免垂體性腺抑制過深,減少促排時Gn的用量,各組間Gn的總量并無顯著性差異,從而有利于改善臨床結局。本研究中各組間的MⅡ率、卵裂率、優胚率、流產率均無統計學差異,說明根據患者的卵巢反應給予不同的降調劑量,可達到垂體降調節,又無過度抑制卵巢功能,是值得選擇的一種降調節方式。而結果中活產率有所不同,一方面可能與納入人群的偏移有關,另一方面卵巢功能稍差的患者其臨床結局可能受到一定的影響。
綜上所述,不同的患者個體情況各異,對GnRH-a的反應性也不盡一致。靈活應用個體化劑量的長方案降調節既可以有效抑制早發LH峰,又能在不同反應人群達到理想的降調水平,獲得較好的妊娠結局。
【參考文獻】
[1]張翔,鄭偉. GnRHa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研究進展[J].國際婦產科學雜志,2005,32:243-246.
[2]周燦權,鐘依平.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的臨床應用[J].中國實用婦科與產科雜志,1999,15:754-756.
[3]Porter RN,Smith W,Craft IL,et al. Induction of ovulation for in-vitro fertilization using buserelin and gonadotropins[J].Lancet,1984,2:1284-1285.
[4]Dal Prato L,Borini A,Coticchio G,et al. Half-dose depot triporelin in pituitary suppression for multiple ovarian stimulation in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ology:a randomized study[J].Hum Reprod,2004,19:2200-2205.
[5]張學紅,李麗斐,趙麗輝,等. 應用不同劑量長效GnRH-a(達菲林)降調節的臨床效果分析[J].生殖與避孕,2005,25:435-437.
[6]Balasch J,Gómez F,Casamitjana R,et al. Pituitary-ovarian suppression by the standard and half-doses of D-Trp-6-luteinizing hormone-releasing hormone depot[J].Hum Reprod, 1992,7:1230-1234.
[7]Broekmans FJ,Hompes PG,Lambalk CB,et al. Short term pituitary desensitization:effect of different doses of the gonad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 triptorelin[J].Hum Reprod,1996,11:55-60.
[8]Fleming R,Lloyd F,Herbert M,et al. Effects of profound suppression of luteinizing hormone during ovarian stimulation on follicular activity,oocyte and embryo function in cycles stimulated with purified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J].Hum Reprod,1998,13:1788-1792.
[9]楊婷,李麗斐. 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對子宮內膜容受性的調控[J].國際生殖健康/計劃生育雜志,2012,31:479-483.
[10]Wiesak T. Role of LH in controlled ovarian stimulation[J].Reprod Biol,2002,2:215-227.
[11]李潔,詹雪君,高軍,等. 在IVF-ET中低劑量長效GnRH-a與短效GnRH-a長方案降調節的評價[J].生殖醫學雜志,2015,24:828-833.
[12]張雯碧,徐叢劍. 子宮內膜異位癥對胚胎和子宮內膜的影響[J].中國計劃生育和婦產科,2017,9:1-3.
[13]郭藝紅,孫瑩璞. 不同類型子宮內膜異位癥降調節方案及、Gn啟動時間、劑量[J].生殖醫學雜志,2015,24:820-824.
[14]Chen ZJ,Shi Y,Sun Y,et al. Fresh versus frozen embryos for infertility in the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N Engl J Med,2016,11:523-533.
[15]Munch EM,Sparks AE,Zimmerman MB,et al. High FSH dosing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live birth rate in fresh but not subsequent frozen embryo transfers[J].Hum Reprod,2017,32:1402-1409.
[16]Baker VL,Brown MB,Luke B,et al. Gonadotrophin dos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ve birth rate:analysis of more than 650,000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cycles[J].Fertil Steril,2015,104:1145-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