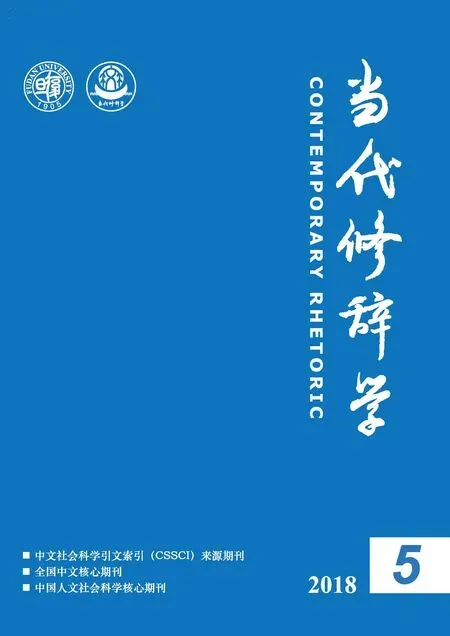佩雷爾曼新修辭學視域下論證評估研究*
蔡廣超
(延安大學政法學院,陜西延安 716000)
提 要 在新修辭學中,佩雷爾曼的普遍聽眾在本質上充當了評估論證好壞的標準或規范。借鑒約翰遜、布萊爾提出的RSA標準以及黑斯廷斯提出的“批判性問題評估法”,普遍聽眾作為評估論證的標準可以具體化為聽眾對前提以及前提對結論支持關系的遵從,這種遵從體現為與每一論證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一個合情理的論證就是與其論證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獲得普遍聽眾的遵從;一個不合情理的論證就是與其論證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至少有一個沒有獲得普遍聽眾的遵從。
一個完整的論證理論除了包括論證概念及其相關要素分析,還應包括論證評估部分,這是任何一個論證理論都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實際上,論證評估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評估的目的是區分好的和壞的論證(蔡廣超2009:20)。也有學者認為,論證評估是非形式邏輯的落腳點,也是核心(武宏志、周建武、唐堅2009:563)。但是,在新修辭學中,佩雷爾曼沒有直接涉及論證的評估問題,而是著重從修辭學視角來論述聽眾和各種各樣的論證技術(techniques of argumentation)或論證型式(argument scheme)。有鑒于其對聽眾之重視、對論證目的和論證理論目的之闡述,依本文之見,普遍聽眾(the universal audience)在本質上充當了評判論證好壞的標準或規范。為了完善佩雷爾曼所倡導論證理論,本文試圖重構其論證理論評估部分,在闡述論證評估標準嬗變基礎上,詳細論述了普遍聽眾何以成為佩雷爾曼評估論證的標準或規范;在借鑒約翰遜、布萊爾提出的RSA標準及黑絲廷斯所倡導“批判性問題評估方法”基礎上,將普遍聽眾作為評估論證的標準具體化為與每一論證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并通過對具體論證案例之分析來彰顯上述評估方法的可行性。
一、 論證評估標準的嬗變:從形式邏輯到非形式邏輯
論證評估是論證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何謂“論證評估”?依據《邏輯學大辭典》的解釋,論證評估是根據充足理由原則的邏輯要求,對論證理由的真實性、理由對推斷的支持關系及論證語言的可理解性等所作出的判定(彭漪漣、馬欽榮2004:704)。依戈維爾(Trudy Govier)之見,論證評估就是評估論證的前提以及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方式。在其看來,如果一個論證的前提合理可接受(rationally acceptable),前提為結論提供合理的支持,則這個論證令人信服(cogent)(2010:87)。在約翰遜(R.H Johnson)看來,論證評估理論需要回答是什么品質或特性使得一個論證成為一個好的論證?(2000:180)依本文之見,雖然以上論述闡述“論證評估”的側重點不同,但是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論證評估都是由論證評估標準和論證評估方法兩個方面構成。具體來說,論證評估標準是判斷論證的品質進而區分其好壞的依據,論證評估方法是說明如何運用評估標準來評估論證。鑒于論證理論有形式邏輯論證理論與非形式邏輯論證理論,相應地,人們對論證評估標準的探尋也經歷由可靠性標準到RSA標準的變化過程。
首先,基于形式邏輯的論證理論,把有效性以及以其為核心的可靠性作為論證評估的標準,在論證實踐中引發了一系列問題。由于邏輯是研究好推理(好論證)和壞推理(壞論證)之區分的規范性學科,它必須基于一定標準對論證進行評估。①在形式邏輯中,論證評估的方法被深深嵌入形式化的烙印,首先將論證翻譯為形式語言,然后借助可靠性標準加以評估。人們通常認為,一個好的(good)論證就是一個可靠的(sound)的論證,而論證達到可靠性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前提真實且推理形式在演繹上有效(晉榮東2015:22)。在形式邏輯中,“前提真實”或者說“論據應當是真實命題”(《普通邏輯》編寫組2010:362)涉及各門具體學科,邏輯學通常無法判定具體命題的真假。也就是說,形式邏輯評估論證就是判斷論證形式有效與否。但是,有效性作為論證評估的標準存在很大局限性,一是有效性作為論證評估標準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一方面,有效的論證不一定是好的論證,如乞題或循環論證。另一方面,無效的論證不一定就是錯誤的論證,如歸納論證或假定論證;二是有效的論證在實踐中很容易達到;三是有效性很難解釋,在實際論證中,針對某一觀點往往既有支持也有反對它的好論證。②
其次,非形式邏輯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于不滿局限于用邏輯形式來理解論證結構、用有效性及以其為核心的可靠性來評估論證,為此,學者開啟了對于論證評估的多元方法的探求。1970年,漢布林(C.L Hamblin)提出了論證評估的真值的(alethic)、認識的(epistemic)和辯證的(dialectical)標準(1970:224-252)。1977年,約翰遜和布萊爾(J. A Blair)在分析謬誤時提出了RSA標準——相關性(relevance)、充分性(sufficien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1992年,戈維爾在接受RSA標準基礎上提出了ARG標準——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相關性(relevance)和好的根據(good grounds)(1992:68-69)。2000年,約翰遜在《展示理性》(ManifestRationality)一書中,重新將真(truth)作為論證評估標準之一,進而將RSA標準變更為RSAT四個標準。可以看出,用于評估實際論證的評估標準在不斷發展中得到逐步完善。武宏志(2009:563)認為,非形式邏輯在論證評估標準上的轉變,就是從去語境的、理想化的標準即正確性(有效+真前提)標準,轉到語境的、現實的日常論辯的標準。
二、 新修辭學論證的評估標準:普遍聽眾
作為非形式邏輯理論先驅之一,佩雷爾曼在新修辭學中沒有明確論及論證評估問題,但在闡明論證(argumentation)③的目的和聽眾的意義時,已對判斷一個論證能否實現促成或強化聽眾遵從(adherence)④論題應該滿足的條件有所涉及,因而,在一定程度也論及論證評估問題。
在新修辭學中,佩雷爾曼從修辭學角度來論述論證問題,所以論辯技術的實效性是核心,這是修辭學的本質所決定的。依其之見,論證理論的目的是研究促成或強化心靈對于那些尋求同意之論題遵從的推論技術(discursive techniques),論證的目的是為了促成或強化聽眾對論題的遵從(1969)。在這里,對論證、論證理論目的之描述包含三個關鍵詞:論證、聽眾和遵從。其中,“聽眾”作為論證主體之一居于核心,包括普遍聽眾和特殊聽眾(the particular audience);遵從是聽眾對論題置信程度的體現,論證的說服力(persuading)和確信力(convincing)彰顯了不同類型聽眾對論題的遵從。對特殊聽眾有效力的論證具有說服力,獲得普遍聽眾遵從的論證具有確信力。對于那些有意激勵人們行動的人來說,說服力比確信力更重要,這是因為論證具有確信力僅僅是行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果一個個體更為關心遵從論證涉及的理性特征,則論證具有確信力更重要(Perelman 1969:27)。在《展示理性》中,約翰遜表達了相同觀點,“一個好論證是達到其目標的論證,其目標……是理性說服(rational persuasion)。相應地,一個好論證就是理性地說服他者(the other)接受其結論的論證”(2000:190)。
在新修辭學視域下,論證和聽眾交織在一起,不可分割,論證的目的為了聽眾,論證的品質取決于聽眾,聽眾的特性也會影響論證者的行為和所采取的論證技術或型式(Perelman1969:23-26)。聽眾如何影響到論證者對前提的選擇、表述以及論證技術的使用,其實已經涉及論證的評估問題。例如,論證的前提由關于實在和偏好的共識構成,它們不是總在論證之初就被明確地陳述出來。在很多時候,它們是在論證過程中才被提出來,或者是在事后對論證過程進行仔細檢查時才會被發現。無論這些前提是否在事前被明確陳述出來,如果聽眾沒有對它們達成共識或者不遵從這些前提,論證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根據愛默倫(F.H.van Eemeren)、加里森(B. Garssen)等人的分析概括,對論證的前提缺乏共識有三種情況:一是對前提的地位缺乏共識,說的是論證者提出一個事實但聽眾希望看到它是如何被證明的,或者論證者假定了一個價值位階但聽眾認為它不存在;二是對前提的選擇缺乏共識,指的是論證者提出了一個事實但聽眾認為與論證不相關或者更愿意看到該事實沒有被提及;三是對前提的語言表述缺乏共識,則是說論證者帶有偏見地或用其內涵不為聽眾所接受的語詞來表述某些事實——被承認是事實或對其與論證的相關性有共識(2014:269-270)。質言之,對論證前提以及三種對論證前提缺乏共識的情況就從反面說明一個好論證、一個想達致其目的的論證,其前提應該為聽眾所認可;或者說,其論證者與聽眾應該就前提達成共識。這其實就涉及對論證前提的評估問題。那么,佩雷爾曼是否討論了論證技術/型式的選擇與聽眾共識之間的關系,即論證技術/型式的評估呢?他是否論及一個實現其目的的論證,其論證技術/型式應該為聽眾所認可?
依赫里克(Herrick)之見,佩雷爾曼的聽眾非常重要,能可靠地檢驗論證的理性品質(1997:197)。佩雷爾曼自己也意識到,論證的價值不可能取決于任何一個偶然遇到論證之人。為此,他不僅給出了“聽眾”定義,也區分了聽眾的不同類型,希望克服沒有獨立標準來衡量論證價值的缺點。在他看來,聽眾不僅是由那些明確針對的對象或閱讀論證的人組成,也包括論證者希望通過論證影響的人(1969:19)。可以看出,聽眾是佩雷爾曼新修辭學論證理論的基礎與核心,聽眾對于論題的遵從強度是判斷論證成功與否的標準,從而與基于形式邏輯的論證理論對論證所進行的那種非此即彼的評估——要么是有效的好論證,要么是無效的、壞論證——區別開來。在佩雷爾曼觀念中,評估一個論證的好壞的判斷標準是普遍聽眾的遵從強度,或者說新修辭學最為重要的論證評估標準是普遍聽眾(蔡廣超2014:14-18)。福斯(S.K.Foss)、特拉普(R.Trapp)等曾經直言不諱地指出,普遍聽眾是區分論證好壞的標準或規范(2002:89)。在這里,普遍聽眾是由全人類或者至少是所有正常的成人組成(Perelman 1969:30)。在《修辭王國》中,佩雷爾曼對這一概念作了進一步闡述,認為其是由全體人類或者至少是所有有能力和理性的人組成(1982:14)。普遍聽眾的思想來源可追溯到古典西方修辭傳統,亞里士多德的《論題篇》是其建立的基礎(Golden 1986:288)。作為演說者內心構建的理想概念,普遍聽眾具有歷史的偶然性,隨演說者和文化不同而發生變化。依米歇爾·梅耶(Michel Meyer)之見,普遍聽眾是理想聽眾,原則上為每一個人所共享,但不在任何特定個人之中,它是傳統哲學所稱之為理性的對應物(2010:405)。⑤⑥
在新修辭學視域下,一個為普遍聽眾遵從的論證是成功實現了目的的論證,因而是合情理的(reasonable)論證;反之,則是未能實現目的的論證,因而是不合情理的(unreasonable)論證。⑦很明顯,佩雷爾曼以聽眾為核心的論證理論的評估標準與傳統論證理論評估標準相去甚遠。它不僅恢復了為傳統論證理論忽略的聽眾要素,而且把聽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將普遍聽眾作為評估論證好壞的標準與規范。盡管如此,在如何運用這個標準來評估論證方面,佩雷爾曼沒有給出可行的操作方法,而且普遍聽眾作為評估論證的標準和規范非常抽象,具有相對性,過于籠統且在實踐中難于操作。但這并不意味著聽眾概念不能作為背景因素在提出論證評估標準時發揮作用,為了規避聽眾因素作為評估論證標準具有的相對性與堅持邏輯標準普遍性之間的內在沖突,約翰遜、布萊爾(1987:41-56)提出“模范對話者”(model interlocutor)概念來重新解釋RSA 標準。在這里,“模范對話者”概念與彰顯佩雷爾曼將理性、合理標準引入修辭學的“普遍聽眾”概念具有同樣作用,與邏輯更為接近,因此,可將論證評估的RSA標準視為普遍聽眾作為評估論證標準的具體化。由于論證評估主要是論證技術/型式的評估,這種評估進一步展開為對前提的評估和對前提與結論之間支持關系的評估,可將普遍聽眾的遵從具體化為對前提的遵從以及對前提與結論支持關系的遵從兩個方面——A用于評估前提,R和S用于評估前提和結論之間的支持關系。依本文之見,由于論證技術/型式具有不同類型,加之聽眾在論證評估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將RSA標準作為普遍聽眾標準的具體化來重構新修辭學論證評估理論,還需要借助批判性問題(critical questions)的策略將RSA標準以及聽眾的意義進一步具體化,也就是說,為每一種論證型式匹配相應的批判性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來判斷相應的論證型式或者說使用這些型式的具體論證的好壞。
三、 論證型式評估方法:批判性問題評估法
在《從公理到對話》(FromAxiomtoDialogue)一書中,巴斯(E. Barth)和克雷伯(E. Krabbe)(1982:14-19)區分了“形式”一詞的三種含義:形式1來源于柏拉圖所說的form(相/型相/理念);形式2指現代邏輯系統中所理解的句子或命題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邏輯形式;形式3最初指那些依據某些規則被調整或系統化了的程序,尤其是那些有助于區分一個討論之勝負的言語論辯術的形式。由于論證型式是從形式3的角度對論證技術之結構的刻畫,它不同于形式2意義上的邏輯形式,因而不能按照形式邏輯對推理形式之有效性的判定來加以評估。在新修辭學視域下,論證不同于演證,它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和目的性,即論證是論證者促成或強化聽眾對論題之遵從的活動及其產品。另一方面,聽眾的遵從既是論證的目的,也具有評估論證成功與否、能否達到其目的的功能。鑒于此,黑斯廷斯(Arthur Hastings)(1962)在論證研究領域第一次實踐了被后人稱作“批判性問題評估法”的方法來評估論證型式,他在博士論文中討論了9種論證型式、相應的實例以及與每一種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迄今為止,批判性問題評估法已成為非形式邏輯學家評估論證型式的標準方法。
在分析非形式邏輯的核心概念“論證型式”時,武宏志、張志敏(2008:6)具體說明了如何運用批判性問題評估法來評估論證型式。簡單來說,就是給出每一論證型式及其批判性問題集,將論證型式用于對話語境中的具體論證,運用與論證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來評估雙方證據分量。實際上,適合論證型式的論證評估方法就是一旦支持者提出一個論證,如果回應者提出一個恰當的批判性問題而支持者未能回答,論證型式則不合理(Walton et al.2008:3)。為判定新修辭學描述論證型式合理與否,可以將RSA標準作為普遍聽眾遵從的具體化,它們分別對應于不同的批判性問題,而不同的批判性問題承擔不同的評估功能。其中,R是評估前提與結論是否具有相關性,S是評估前提與結論支持關系是否充分,A是評估前提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由于佩雷爾曼提出論證的目的是為了獲得聽眾對論題之遵從,作為RSA標準具體化的批判性問題提出者就是普遍聽眾,回應者就是論證者。在特定對話語境中,為了使聽眾對前提的遵從轉移到結論,或者增強聽眾對論題的遵從強度,論證者會使用一定的論證技巧或論證型式,與論證型式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或制約條件能否得到滿足是衡量論證合理與否的依據。就此而言,如果論證者對與論證型式相匹配批判性問題給出肯定回答,論證就會獲得普遍聽眾的遵從,其論證就會因為對普遍聽眾具有確信力而得以成功。如果論證者對與論證型式相匹配批判性問題之一或多個給出否定回答,論證就無法獲得普遍聽眾的遵從,其論證就會因對普遍聽眾不具有確信力而難以成功。
與形式邏輯對演證的評估相比,批判性問題評估法在評估論證方面具有以下特點:在形式邏輯中,對演證的評估結果具有普遍性和非此即彼的性質,就前者來說,它是超時空的,一個推理有效與否與這個推理所處的時空沒有關系;就后者來說,它要么有效要么無效,沒有程度的區分。在非形式邏輯中,運用批判性問題評估法評估論證的結果具有情境性且存在程度區分。就前者來說,它與論證所處的時空條件、與論證的主體均有關系,同一種論證在不同的條件下其評估結果很可能不同。就后者來說,聽眾對結論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遵從—不遵從兩種情況,而是存在遵從強度的變化。
四、 新修辭學論證評估案例分析:分離論證
基于以上論述,借助黑絲廷斯的“批判性問題評估法”,新修辭學的論證型式可以運用與其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進行評估。在這里,我們對具體論證型式的分析、評估無意窮盡新修辭學所描述全部論證型式,而是以分離論證為例,在概述新修辭學所描述分離論證的基礎上,抽象出分離論證的形式結構,并輔之以與其相匹配的批判性問題,然后給出實例,最后依據論證評估的標準,運用批判性問題對具體案例進行分析,進而評估論證的合理與否。
分離論證是新修辭學考察論證技術的一項重要內容,盡管“分離論證技術在古代修辭理論中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Perelman1982:52)但是,這種論證技術在實踐中的價值不容忽視。何為分離?一般來說,“分離”一詞意味著分開(separation)。《柯林斯英文詞典》中說到,如果你想使自己與某事或某人分離,你應表明與他們沒有聯系;如果你要把某事與其他事情分離,開始時就應將兩者視為彼此分開。在論述新修辭學的論證型式時,沃尼克(Barbara Warnick)和克萊恩(Susan L.Kline)(1992:10)對“分離”作了闡述,不同于類比把兩個不同領域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分離是將原來的不相容概念予以分解進而修改概念的結構。在佩雷爾曼看來,分離就是把聽眾本來認為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分成兩個新的概念,每一個概念僅僅包含原始概念的一部分。其中,一個概念包含原始概念中屬于表象的部分,另一概念包含原始概念中屬于實在的部分。在實踐層面,概念的分離意味著妥協;在理論層面,概念的分離可以帶來一種對未來而言仍將有效的解決辦法,因為通過重塑我們關于實在的概念,它將相同的不相容情形再次出現(1969:413)。麗絲(van Rees)在深入分析佩雷爾曼關于分離的論述后,給出了一個綜合性定義,即“分離是一種論證技巧,它的目的是為了化解矛盾或不一致,把由一個語詞表達的統一概念分成兩個新的、價值不等的概念。一個從屬于一個新的語詞,另一個或者從屬于原有的語詞——它經過重新定義被用來指稱一個內容減少了的概念,或者根據自己的定義從屬于另一個新的語詞,同時放棄原有的語詞”⑧(2009:9)。
基于上述分析,分離論證的結構可以重建為如下論證型式:
1. 論證型式
前提1:在語境C中,概念S與事實矛盾或不相容,
結論:S1(S概念中表象部分)、S2(S概念中實在部分)
2. 批判性問題
CQ1:在語境C中,概念S真的與事實矛盾或不相容嗎?
CQ2:如果S與事實矛盾或不相容,是否有理由表明S1是S的表象部分、S2是S的實在部分?
3. 案例
依據佩雷爾曼的觀察,法律是最喜歡妥協的領域。在法律解釋中,分離技巧在“強奸”一詞定義的爭論中發揮著至關重要作用。最初,“強奸”一詞的法律意義是指婚姻關系以外非自愿的異性性行為。在婚姻中,強奸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一個妻子同意嫁給她的丈夫時,就會認為她是無條件的同意。夏帕(Schiappa)指出,婦女權力運動成功地挑戰了男性性特權的理論基礎定義,目前,“強奸”的法律定義不再包含婚姻關系之外的必要限定條件。現在,“強奸”一詞是指通過威脅、使用武力或受害人不同意的所有性行為(Rees 2009:23)。
4. 論證評估
分離論證的確信力可以用相應的兩個批判性問題進行評估。在上面案例中,夏帕使用分離技巧來說明“強奸”一詞含義的變化,原來婚姻關系以外非自愿的異性性行為屬于強奸,現在強奸的法律定義不再包含婚姻關系之外的必要限定條件,只要是通過威脅、使用武力或受害人不同意的所有性行為都屬于強奸。聽眾可以對夏帕就“強奸”一詞含義的變化給出的分離論證提出如下質疑:CQ1:在語境C中,“強奸”一詞真的與事實矛盾或不相容嗎?CQ2:如果“強奸”一詞與事實矛盾或不相容,是否有理由表明原來的強奸概念是表象部分、現在的強奸概念是實在部分?如果論證者能提供有力的證據,對CQ1、CQ2給出肯定回答,那么,夏帕提出的分離論證就能夠使普遍聽眾確信,為其所接受,從而使這個論證成為具有確信力的論證。反之,如果不能對這兩個批判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給出肯定回答,其論證就會因對普遍聽眾不具有確信力而難以成功。
五、 結 語
在佩雷爾曼的論證理論中,普遍聽眾構成了論證評估的核心,盡管約翰遜、布萊爾提出的RSA標準以及黑絲廷斯倡導的批判性問題評估方法使得抽象的普遍聽眾作為論證評估的標準更為具體,對具體分離論證的分析、評估則彰顯了上述評估方法的可行性。然而,在理論實踐中,普遍聽眾概念不僅受到責難,也受到眾多學者的曲解和誤解。但不管怎樣,佩雷爾曼導入的普遍聽眾給修辭學注入了相對客觀的理性標準,既拒斥了笛卡爾的唯理性主義,也排斥了后現代放棄合理性的偏激立場(蔡廣超2014:14-18)。有鑒于此,重構新修辭學論證的評估理論,完善佩雷爾曼的論證理論,不僅是使普遍聽眾理解、遵從“普遍聽眾”概念的過程,也是使普遍聽眾確信“普遍聽眾”作為論證的評估標準在理論上是必要的,在實踐中具有可行性。
注釋
① 論證評估的標準有三種生成方法。一是先驗方法。比如漢布林弱化或降低由FDL生成的標準,但該方法似乎不太可能生成可行的評估理論。二是經驗方法。從辨識許多好論證的標本開始,然后通過反思這些例子,形成評估理論,可能是由于對心理主義的畏懼,形式邏輯家從未嘗試過這個方法。三是語用方法。從按照論證的目標條件對論證的反思開始(武宏志、周建武、唐堅2009:563)。
② 本文在引用時作了修改(孫巖2006:9)。
③ 在國內,“argumentation”一詞有三種譯法:辯論(沈宗靈1992:387-402)、論辯(愛默倫、荷羅頓道斯特1991;愛默倫、漢克曼斯2006)和論證(廖義銘1993:32;武宏志、周建武、唐堅2009:98、99、101、102、136、148)。其中,“辯論”的譯法較少使用,且易與普通的口語辯論(debate)相混淆;在愛默倫、赫羅敦道斯特等看來,“argumentation”一定是在現實的兩個主體之間展開(Eemeren et al1996:1-15),故譯為“論辯”;依佩雷爾曼之見,“argumentation”不僅包括在現實兩個主體之間或論證者與想象聽眾之間展開的“argumentation”,也包括書寫的“argumentation”(佩雷爾曼1969:6-7)。有鑒于新修辭學中“argumentation”的含義包含但不限于愛默倫等人的理解,本文采取“論證”的譯法。
④ 在學術界,“adherence”一詞有三種譯法:遵從(廖義銘1993:35-36)、確信(佩雷爾曼2004)和認同(羅伯特·阿列克西2002:200)。對于該詞的翻譯,阿諾德(Carroll Arnold)在《修辭王國》序言中已給出清晰說明,他說在討論每一個論證者修辭情況方面,佩雷爾曼給出了很好的術語選擇,相對于“接受”或“拒絕”主張,論證者致力于“引發和增加聽眾的adherence”,“adherence” 提醒我們它要好于諸如“同意—不同意”、“接受—拒絕”或者“贊同—不贊同”之類的術語,有鑒于此,本文主張“adherence”應譯為“遵從”。
⑤ 本文在引用時參考中文翻譯(米歇爾·梅耶、史忠義譯,趙國軍校2013:31),并做了修改。
⑥ 在這里,我們對作為本文的核心概念“普遍聽眾”作了清晰界定和論證,并闡述其來龍去脈,得益于審稿專家建議。謹致謝忱!
⑦ 新修辭學試圖描述人們在實踐中使用的論證技巧,以贏得他人對論點的贊同。用于評估論證的合情理性標準是聽眾,如果論證能成功影響它針對的聽眾,論證是可靠的(或是argumentatively valid)。新修辭學提供了對不同類型聽眾的描述,區分了“特殊”聽眾和“普遍”聽眾,其中特殊聽眾由實際人組成,他們是論證者或作者在特殊事例中言說對象;普遍聽眾是合情理性的代表(Eemeren et al.2004:47)。
⑧ 這個定義包含的各種要素,可以在其他作者給出的定義中發現,他們給出的定義以佩雷爾曼的工作為基礎。愛默倫、何羅敦道斯特等(1978:284)把分離定義為“論證者在舊的概念之外引入一個新的概念,舊的概念不能包括所有差別,用這種方法完成分離以服務于論證目標”。舍倫斯(1985:59)視分離為“在一個概念中引入分化,類似于概念結構的活動”。愛默倫、何羅敦道斯特和漢克曼斯(1996:144)說分離包含“在先前聽眾視為統一體的要素中引入分離,在實踐中,一個概念與先前作為其組成部分的概念相區分”。格賴斯(1997:72)把分離描述為“通過聲稱,聽眾認為屬于某個概念的某些因素不再屬于那個概念,表述那個概念語詞的意義減少:分離引起對一個術語的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