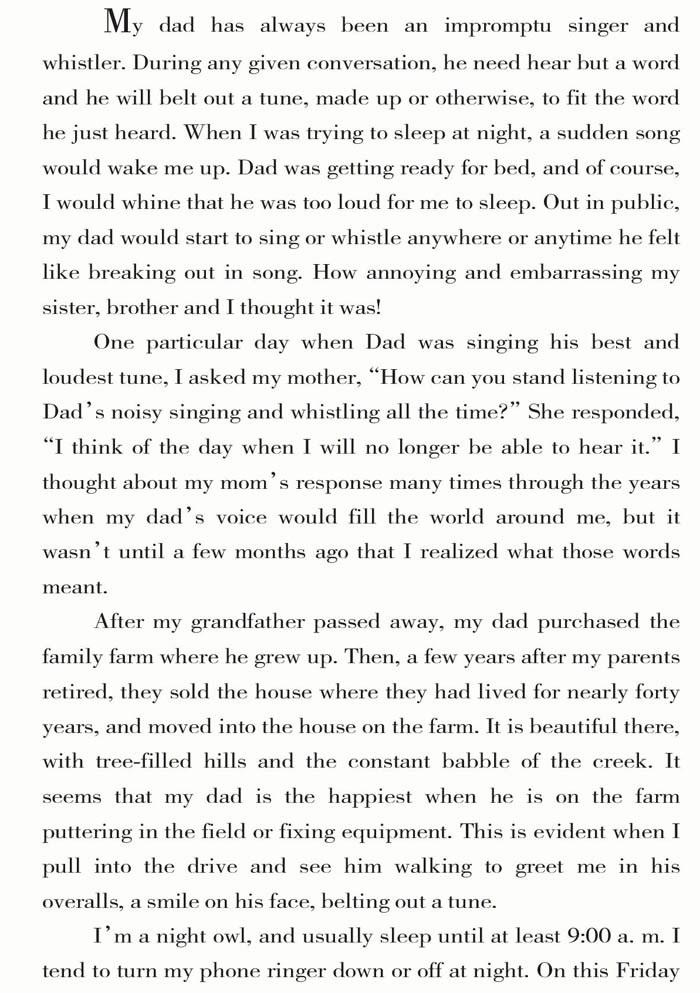爸爸的歌聲
王穎
我的爸爸總是即興唱歌、吹口哨。和人聊天時,只要聽到一個詞,他就能引吭高歌,把聽到的詞編上曲子,曲子也許是他自己編的,也許不是。有時,晚上我正要睡著時,突然歌聲傳來,把我吵醒。爸爸準備睡覺了,當然,每當這時我都會抱怨他吵得我睡不著覺。在公共場合,爸爸也是隨時隨地,想唱就唱,想吹口哨就吹口哨。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覺得那非常令人厭煩和尷尬!
記得有一天,爸爸在唱他拿手的曲目,聲音特別大,于是,我問媽媽:“爸爸唱歌吹口哨這么吵,您怎么能忍受得下來?”她回答說:“我會想我再也聽不到他唱歌的那一天。”從這以后,我無數次思考媽媽說的話,在此期間爸爸的歌聲一直陪伴著我,但直到幾個月前,我才明白了那句話的含義。
我的祖父去世后,爸爸買下了他從小住到大的家庭農場。然后,我的父母退休幾年之后,就賣了他們住了將近40年的房子,搬到農場的房子里去住了。農場環境優美,小山上樹林密布,還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在農場里做農活、修設備的時候,爸爸好像是最幸福的。每當我開車到達農場,看到他穿著工作服走出來迎接我,臉上帶著微笑,嘴里哼著小曲時,我就知道他是幸福的。
我是個夜貓子,通常至少要睡到上午九點才起床。晚上,我總是把手機鈴聲的音量調低或者調成靜音。這個星期五早上醒來時,我發現手機上的信息燈跟往常一樣閃爍不停,但反常的是,我收到了媽媽發來的信息。爸爸在冰上滑倒,摔傷了頭部,正在接受緊急腦外科手術。
穿衣服時我失聲痛哭,匆忙穿上最厚的冬外套,戴上手套后,便沖向醫院。趕到醫院時,家人、朋友都和我媽坐在一起。不到一個小時,醫生出來告訴我們手術進行得很順利,他已經清除了對爸爸的大腦產生壓力的血塊。
進入病房,我們很高興地看到爸爸雖然頭裹著紗布,頸部固定在支架上,但他的精神很好,話也很多。在他最初問醫生的幾個事情中,其中一個是:“這會影響我的歌聲嗎?”這是件好事,醫生的態度非常樂觀,他甚至還提到父親下周一也許就能出院回家了。
然而到了周六,事情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發展,星期天早上,爸爸進行了第二次手術。我再次淚眼模糊地開車趕到醫院。又經過幾個小時漫長的等待,手術終于完成,我們可以見到爸爸了。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嚇了一跳,眼前的父親面部腫脹,不能說話……
隨著時間的流逝,爸爸的病情有些許好轉。看著爸爸費勁地走路吃飯,我的眼中充滿了淚水。經過了我生命中似乎最漫長的一周后,爸爸終于轉到了康復中心。第二天,我沿著走廊走向爸爸的病房時,他熟悉的歌聲從遠處傳來。爸爸在唱歌!簡直難以置信,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剛走進房間,就看到爸爸除了頭上那許多亮藍色的縫線外,已經和摔倒前沒有什么不同了。
爸爸摔傷三個星期后,媽媽終于可以帶他回家了。當然,爸爸還需要后續的康復治療,但有一點他已經完全恢復了,那就是他的歌聲和口哨聲。如今,再聽到他在公共場合唱歌,在睡前吹口哨,或者即興高歌時,我不再覺得厭煩了,我會感到欣慰,因為我現在意識到,將來有一天我會再也聽不到爸爸的歌聲。但是,我希望那一天短時間內不要到來。
(責任編校/周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