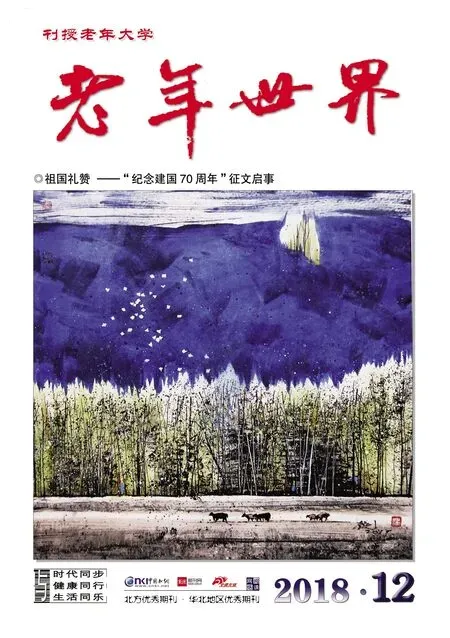那年蓋涼房
九 月
涼房,是咱呼和浩特人的習慣叫法,其實應為倉房。
回憶起小院里有涼房的那段日子,很有嚼頭。為此我寫過一首叫《呼市人》的詩,其中有這樣兩句:“……呼市人早先圪蹴在小院里拉風箱/圪蹴著吸溜一碗黃昏……”
那是上世紀70年代,老丈人病故,丈母娘就我愛人這么一個女兒,作為上門女婿,我退出結婚時住的職工宿舍,跟隨媳婦到她娘家住,加一起不過是三口之家。那是一個單位的家屬院,那時候院內沒有樓房,一排排一順兒平房。我們的家居于一排平房的中間,除了我們家以外,左右鄰居們都圈著小院,小院里都有涼房。我一個大男人住了這里,豈能不蓋涼房?否則這樣下去會被人說成“懶貨”的。于是,我為未來的涼房開始從方方面面著手準備。那時候的這個家屬院寬綽,南面是一大片空地,坑坑洼洼,看樣子人們在這里挖坑取土,脫過不少土坯。
正值炎熱的夏天,我只穿一條短褲,打水、和泥,用借來的特大模子脫坯。之前,因為我脫過坯,干起來沒問題。半天下來,全身就被曬得紅紅的,擦一把汗水或彈掉一塊濺在身上的泥塊,皮膚沙疼。
兩三天工夫,一塊塊中間留著縫隙碼起來的幾百塊土坯就晾干了。愛人幫助我把一塊塊坯搬到借來的排子車上時,我說“你別干了,穿個裙子不協調。”她說“那有啥的,臟了就洗唄。”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我倆歪歪扭扭地推車,車上的土坯一陣擁擠,一陣相撞,有的“笑掉大牙”,有的邊角被蹭禿,有的“樂彎了腰”,打中間裂開。還好,宅院空間窄小,蓋不了多大涼房,何況,一側可利用鄰居家涼房墻面,這些坯綽綽有余。

頭兩天約好幾個朋友,星期日(當時為單休日)這天早晨動工。大梁、一堆椽子,是早已準備好的。那時候,哥們兒喝點茶、吃個焙子就滿足了,沒有更高要求。這邊和泥,那邊砌墻,正干著活兒的時候,扭頭之間我突然發現鄰居家的小伙子不知什么時候也參與進來了,我讓他先喝上一點兒,吃上一點兒,他說吃喝過了。一伙人都是年輕力壯的后生,都是蓋過涼房的好把式,只干了個把鐘頭,三面墻就壘起來了,效率之高,令我始料不及。
我唯一沒有準備好的,就是涼房的門。此時,留多大門框呢?我犯難了。我們中間有個愛開玩笑的,他說“高,以夫人身高為準。寬,以丈母娘身寬為準。”逗得大家一陣大笑。這個時侯,鄰居家的小伙子對我說:“我家涼房里有扇多余的門,你如果不嫌棄,就拿來試試。”我說:“這有啥嫌棄不嫌棄的,一個破涼房用的門唄!”我們幾個人從他家涼房里抬出那扇門,看了看,還真不錯。我說“價錢,完了再說。”小伙子學著剛才我的腔調:“這有啥價錢不價錢的,一個破涼房用的門唄!”把眾人逗樂了。大家把門窗安裝,把房頂抹得光溜溜的。在門角一側還砌了一臺土灶。我看了看,心里很滿意,說“大家洗洗手,吃飯。休息一會兒再把墻抹一遍,完事。”那幾個就說“別價,一溜兒抹完墻算了,一會兒的工夫。”說罷,真是一會兒工夫,墻抹完,“戰場”打掃干凈。
自此,這個從來沒有過壯勞力、一直沒有涼房的家,有了涼房。從此,這一排因沒有涼房一直處于豁口的地方,立起涼房,補上空白。夏天可以在涼房燒火做飯,冬天可以在涼房里冷凍一些白條雞、白條羊什么的,家里暫時不用的破爛東西,可以堆放在涼房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這個大院動工蓋家屬樓,平房、涼房全部推倒。我家從此告別涼房,過上了住樓房的日子。而那些幫我蓋涼房的同事和鄰家朋友,那些情景,成了永遠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