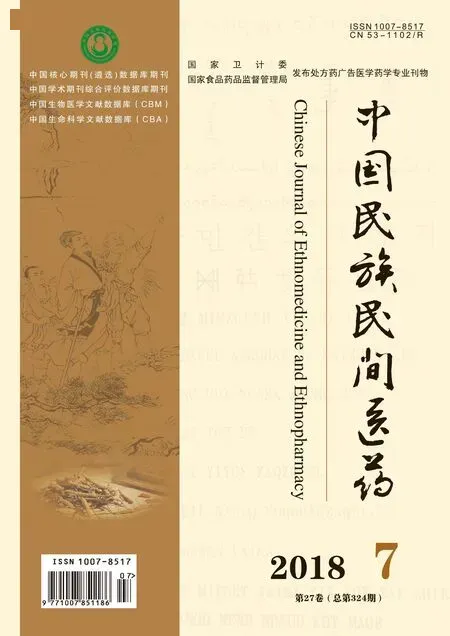痙攣肌起止點浮針松解對腦卒中后肘關節屈曲痙攣的療效觀察
廣東省第二中醫院針灸康復科,廣東 廣州 510095
腦卒中目前已成為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全球性疾病之一,約有20%~40%的中風患者在后期罹患有肢體偏癱痙攣[1]。肢體痙攣可導致肌肉僵硬、關節活動度下降、關節攣縮,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后期肢體功能的恢復[2]。目前,緩解中風后肢體痙攣的方法主要包括藥物治療、矯形器、康復運動以及物理因子治療等[3-4],然而,經過上述治療,仍有半數以上的患者未得到滿意的療效。因此,尋找一種更為安全、有效的方法顯得尤為迫切。浮針療法是一種新興療法,主要在病灶周圍淺筋膜層(相當于傳統經絡理論的皮部)針刺,可以迅速改善局部循環,解除肌肉的痙攣。浮針的應用目前已涉及到臨床各個領域[5-7],中風后肘關節痙攣多表現為肘關節的過度屈曲和內收,涉及的痙攣肌主要是肱二頭肌及胸大肌,筆者采用浮針松解肱二頭肌及胸大肌起止點治療腦卒中后肘關節屈曲痙攣,療效較滿意,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5年4月至2016年8月于廣東省第二中醫院針灸康復科住院患者54例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按照1∶1的比例隨機分為對照組(傳統針刺)和治療組(起止點浮針松解),每組各27例。對照組,男性18例,女性9例,年齡47~73歲,平均年齡(60.56±3.98)歲;病程1~4.3月,平均病程(3.1±0.1)月;其中缺血性卒中14例,出血性卒中13例;治療組,男性16例,女性11例,年齡45~71歲,平均年齡(58.78±4.71)歲;病程1.2~4月,平均病程(2.8±0.2)月;其中缺血性卒中15例,出血性卒中12例。兩組年齡、性別、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納入標準①西醫診斷標準參照《實用康復治療學》[9]腦卒中疾病診斷標準;②中醫診斷標準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1996年頒布的《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試行)》[10];③經頭顱CT或MRI確診為腦血管病,且病程≥1月;④有上肢或者下肢肌張力增高,且改良Ashworth評分≥Ⅰ+級,MMSE評分≥21分;⑤近2周內未服用肌肉松弛藥,且病情穩定,表達能力正常;⑥年齡在18~70歲之間;⑦簽署知情同意書。
1.3排除標準①嚴重的意識障礙患者;②其他原因引起的肌肉痙攣;③有嚴重的心、腦、腎等其他臟器并發癥;④半年內參加過其他的臨床試驗研究。
1.4治療方法兩組均進行基礎治療:包括控制血壓、控制血糖、調節血脂、防止血小板聚集、神經營養藥、對癥治療、防治并發癥,輔以必要的營養支持,根據患者自身情況進行關節松動康復鍛煉。
1.4.1對照組在基礎治療上,采用傳統針刺治療。患者仰臥位,頭針取對側頂顳前斜線中2/5,選取肩髃、曲池、手三里、外關、合谷。常規消毒后,用華佗牌0.30mm×40mm毫針針刺,頭針沿頭皮平刺30~35mm,刺入帽狀腱膜以下;體針直刺20~30mm。以上諸穴進針得氣后以平補平瀉法捻轉2min,留針30min。每日治療1次,連續治療4周。
1.4.2治療組在基礎治療上,采用浮針療法。選取肱二頭肌起止點、胸大肌止點作為松解靶點,以距靶點3寸處為進針點,常規消毒后,用南京浮針研究所研制的6號一次性浮針工具,針尖朝向靶點處,迅速刺入皮下,沿皮下疏松結締組織平刺,進針過程中力求無疼痛、得氣感,否則退回重新進針。進針完成后,以進針點為支點,手持針柄對準靶點進行扇形掃散。每針掃散約2min,同時囑患者進行關節的主動運動,若無疼痛、酸脹等感覺,則抽出針芯,以膠帶固定針柄,留針24h,隔日治療1次,連續治療4周。
1.5觀察指標
1.5.1改良Ashworth評分(MAS)[11]評定各關節痙攣程度共分為6個級別,即0級、Ⅰ級、Ⅰ+級、Ⅱ級、Ⅲ級、Ⅳ級。為便于統計,相應級別分別計數,即0級=0分、Ⅰ級=1分、Ⅰ+級=2分、Ⅱ級=3分、Ⅲ級=4分、Ⅳ級=5分。
1.5.2Fugl-Meyer評分[12]評定各關節運動功能該表條目主要評定關節的運動、協調能力和反射3個方面,每個條目分為3個等級,即不能完成為0分,部分完成為1分,全部完成為2分。上肢最高評分為66分,下肢最高評分為34分。
1.5.3Barthel指數[13]評分評價日常活動能力(ADL)該表共包括10個項目,每個項目分10分、5分、0分3個等級,最高分100分。

2 結果
2.1兩組MAS評分比較兩組治療前后MAS評分顯示,與治療前相比,兩組在治療28d及隨訪時的評分均有統計學差異(P<0.05或P<0.01);且治療組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治療前后MAS評分比較 (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P<0.01;與對照組同時間點相比,#P<0.05。
2.2兩組Fugl-Meyer評分比較與治療前相比,兩組在治療28d及隨訪時的評分有統計學差異(P<0.05),治療后兩組之間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診時治療組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Fugl-Meyer評分比較 (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與對照組相比,#P<0.05。
2.3兩組Barthel指數評分比較與治療前相比,兩組在治療28d及隨訪時的評分均有統計學差異(P<0.05),治療后兩組之間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診時治療組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Barthel指數比較 (分,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與對照組相比,#P<0.05。
3 討論
肌肉痙攣是腦卒中患者后期常見的并發癥,臨床主要表現為肌張力增高、腱反射活躍及亢進,嚴重影響患肢運動功能的恢復。其原因可能與大腦對下運動神經元的抑制功能減弱,導致前角α運動神經元的過度興奮有關[14]。該病在中醫屬于“筋病”、“痙證”的范疇,《素問·痿論》載:“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素問·痹論》載“痹在于筋,則屈不伸”;《素問·調經論》:“病在筋,調之筋”。由此可見該病病位在筋,治療當以調筋理筋為法。
目前,大量研究已證實針灸在緩解中風后肢體痙攣方面有獨特的優勢,針灸治療中風后偏癱痙攣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針灸可顯著降低患肢MAS評分,促進肢體功能的恢復[15]。浮針作為一種新興的針灸療法,與《內經》中浮刺、毛刺、恢刺等有類似之處,其主要特點是將針具刺入激痛點周圍的皮下淺筋膜,進行扇形掃散,并留針較長時間,以達到松解痙攣、減輕疼痛的目的[16]。浮針對中風后肘關節偏癱痙攣的療效,尚未見相關研究。
本研究采用起止點浮針療法,進一步觀察其與傳統針刺間的療效差異,結果顯示,兩種方法均能明顯改善肌肉的痙攣程度與運動功能,提高患者的日常活動能力,而在改善痙攣及遠期療效方面,浮針優于傳統針刺。關于浮針的作用機理尚未完全明確,目前有研究認為,浮針的作用主要與調節局部組織的空間構型有關,浮針對皮下淺筋膜的刺激可使局部組織產生一定程度的電效應,這種電效應可沿著有半導體特點的蛋白質及多糖所構成的通道迅速移動到患病部位,進而促進其發生壓電效應,引發液晶體的空間組織結構改變至正常狀態[17]。也有研究認為,浮針的作用機理可能與低級中樞的調節有關,也可能與脊髓節段分布有關[18]。但上述機制仍停留在科學假說階段,急需臨床和基礎實驗的進一步驗證。除此之外,目前國內關于浮針的應用仍欠規范,如浮針療法進針點的選擇,文獻中一概無準確定位,套管的留置時間亦無統一標準。而這些因素對評價浮針療法治痛作用的客觀性與準確性有重要影響,故而有待進一步探索、規范。
綜上所述,痙攣肌起止點浮針松解療法可顯著改善肘關節痙攣患者的痙攣程度及生活質量,在臨床上治療中風后肢體痙攣時值得推廣應用,但其起效機制仍需進一步探討,其治療方案的實施也需進一步的規范化。
[1]Zorowitz R D,Gillard P J,Brainin M.Poststroke spasticity Sequelae and burdenonstroke survivors and caregivers[J].Neurology,2013,80(3 Supplement 2):S45-S52.
[2]Graham L A.Management of spasticity revisited[J].Age and ageing,2013,42(4):435-441.
[3]Francisco GE,McGuire JR.Poststroke spasticity management[J].Stroke,2012,43(11):3132-3136.
[4]Kheder A,Nair KPS.Spasticity: Pathophysiology,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J].Pract Neurol,2012,12(5):289-298.
[5]黃素貞.浮針療法聯合康復訓練對腦卒中偏癱患者的臨床應用價值分析[J].針灸臨床雜志,2016,32(5):22-24.
[6]周昭輝,莊禮興,陳振虎,等.浮針療法結合康復訓練治療中風后肩手綜合征:隨機對照研究[J].中國針灸,2016,36(7):636-640.
[7]李婷,張小娟,葉美杏,等.浮針加埋管療法對強直性脊柱炎患者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6的影響[J].新中醫,2016,48(8):155-157.
[8]Mu JP,Liu L,Zhou LZ,et al.Clinical Observation on Fu’s Subcutaneous Needling plus Electroacupuncture for Post-stroke Spastic Hemiplegia[J].Journal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Science,2012,10(6):372-376.
[9]馮曉東,馬高峰.實用康復治療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3:344.
[10]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腦病急癥協作組.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試行)[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6,19 (1):55-56.
[11]魏鵬緒. 關于改良 Ashworth 量表的探討[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14, 29(1): 67-68.
[12]盧寨瑤. Fugl-Meyer量表在腦卒中康復評定中的應用分析[J]. 臨床醫藥文獻電子雜志, 2016, 3(11):2032-2032.
[13]張雅靜, 張小蘭, 馬延愛,等. Barthel指數量表應用于急性腦卒中患者生活能力測量的信度研究[J]. 中國護理管理, 2007, 7(5):30-32.
[14]楊慎峭,金榮疆,朱天民,等.康復訓練結合電針對腦卒中肢體痙攣大鼠γ-氨基丁酸能中間神經元表達的影響[J].中國康復醫學雜志,2013,28(3):202-203.
[15]Lim S M,Yoo J,Lee E,et al.Acupuncture for spasticity after strok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2015:2015.
[16]楊江霞, 符仲華. 淺析浮針的理論與臨床研究[J]. 西部中醫藥, 2015, 28(6):156-158.
[17]張超,候群.中醫手法聯合康復治療對腦卒中康復患者臨床觀察[J].中華中醫藥學刊,2015,33(2):461-463.
[18]苗廣宇,周立秋.浮針療法治療腦卒中后偏癱痙攣狀態150例[J].中國針灸,2009(S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