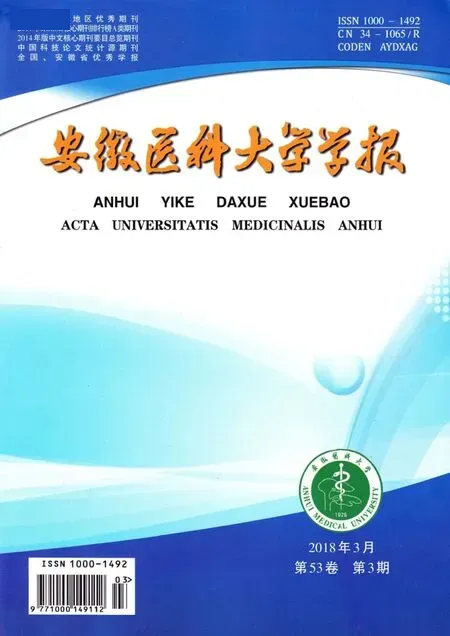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憐憫水平與病恥感之間的相關(guān)性分析
何孔亮,耿 峰,郜見亮,郝 蕊,靳勝春,王 璐,汪 凱
自我憐憫指個人遭遇挫折和不幸時,能直面自己的不足之處,以非批判的態(tài)度對待自己的短處,同情自己的遭遇,始終保持對自我痛苦的理解和接納的態(tài)度,反映了一種寬容并有潛力的適應(yīng)性行為[1]。既往研究[2]證實(shí),自我憐憫水平和情緒、認(rèn)知相關(guān)聯(lián),可以預(yù)測個體對負(fù)性生活事件的情感反應(yīng)和認(rèn)知反應(yīng)[3]。一般來說個體自我憐憫水平越高,其生活態(tài)度越容易樂觀,不良認(rèn)識越少,負(fù)性情緒越低,其抗應(yīng)激能力較強(qiáng),自我認(rèn)識相對完善[4]。
精神分裂癥是一組伴有認(rèn)知功能損害的精神疾病,由于社會刻板印象及文化等影響,公眾往往對精神疾病患者存在消極認(rèn)知[5]。其實(shí)不止是對精神分裂癥,在其他種類精神疾病上也是如此。當(dāng)公眾貶低或歧視精神疾病患者時,患者會將此類負(fù)性認(rèn)知內(nèi)化,并采用隱瞞病情、與外界隔離等自我保護(hù)機(jī)制。而這些不良認(rèn)知混合其產(chǎn)生的負(fù)性情緒即為病恥感[6]。病恥感會受患者的個性和社會支持狀況等因素影響,程度嚴(yán)重的病恥感在患者精神病性癥狀緩解后也可能持續(xù)存在,從而對患者的心理認(rèn)知活動和社會功能產(chǎn)生較大的負(fù)面影響[7]。
國外已有研究[8]初步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我憐憫水平與其認(rèn)知功能損害程度存在一定的相關(guān)性,但患者病恥感嚴(yán)重程度與自我憐憫水平之間是否存在相關(guān)性,國內(nèi)外尚無此類研究。故該研究著重調(diào)查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我憐憫及病恥感水平,并對二者的相關(guān)性展開分析。
1 材料與方法
1.1病例資料采用便利抽樣法抽取2017年3~6月在合肥市第四人民醫(yī)院接受門診治療或住院治療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作為患者組。入組標(biāo)準(zhǔn):① 符合ICD-10精神分裂癥診斷標(biāo)準(zhǔn);② 年齡18~50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③ 經(jīng)過藥物治療有效,能夠配合參與測試。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 伴有嚴(yán)重軀體疾病;② 酒精、藥物、毒品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質(zhì)濫用者。共選取完成100例病患入組,其中男39例,女61例;年齡 18~49(27.34±7.40)歲;受教育年限9~20(12.79±2.81)年;病程4~240(65.97±59.52)個月;疾病類型:偏執(zhí)型60 例,未分化型 40 例;用藥情況:僅使用一種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的35例,同時使用兩種或以上用藥的65例,所有藥物口服劑量均折算成等效氯氮平劑量,見表1。
選取合肥市第四人民醫(yī)院周圍社區(qū)正常健康者作為正常組,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 被試對象直系親屬有明確精神疾病史或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② 有毒品、藥品、酒精等精神活性物質(zhì)濫用。共 151 例,男76例,女75 例, 年齡 18~50(26.68±9.63)歲; 受教育年限 9~18(12.56±1.83)年,見表1。
患者組與正常組間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和Beck抑郁量表評分差異均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所有測試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并簽署了知情同意書。本研究已經(jīng)通過合肥市第四人民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
1.2工具
1.2.1中文修訂版自我憐憫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revised self-compassion scale,SCS-C) SCS-C為自評量表[9],共26個項(xiàng)目,包括3個分量表: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正念。所謂自我友善是指個體遇到困難挫折時明白這是一種人生經(jīng)歷,能夠安慰自己,以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看待困難挫折,繼續(xù)前行。所謂普諞人性是指能認(rèn)識到每個人都有短處,每個個體的經(jīng)歷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所謂正念是指對痛苦不壓抑,不回避,個體直接面對痛苦的正性情感和思想。量表由“幾乎沒有”到“幾乎總是”采用5級評分,合計(jì)得分越高表明個體進(jìn)行自我憐憫的能力越強(qiáng)。
1.2.2中文修訂版Link 量表 該表為自評量表[10],共46個條目,包括3個分量表:貶低-歧視感知量表,此部分共有12個條目,其中6條反向計(jì)分;病恥感應(yīng)對量表,包含內(nèi)容有:對病情保密、隱瞞,不參與社交、退縮,試圖教育他人以及針對他人的歧視行為進(jìn)行反駁及挑戰(zhàn),把自己分離在精神疾病群體之外,此部分共27個條目,有1條反向計(jì)分;病恥感情感體驗(yàn)量表,包含了2個維度,直接反映患者對疾病的主觀感受。整個量表采用4級評分法,其中有7條反向計(jì)分,合計(jì)得分越高表示病恥感越強(qiáng)烈。
1.2.3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 PANSS常規(guī)有30項(xiàng),加上3個評定危險(xiǎn)性的補(bǔ)充條目,共33項(xiàng)。每一項(xiàng)都有1~7級嚴(yán)格的評分標(biāo)準(zhǔn)。該量表計(jì)分值與精神癥狀嚴(yán)重性呈正相關(guān)性。
1.2.4Beck 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該量表較側(cè)重評定情感和心境,所設(shè)計(jì)的條目偏向于臨床“抑郁癥狀”的一些描述,共13個條目,經(jīng)過國內(nèi)修訂,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最終通過合計(jì)得分的高低來判斷是否有抑郁癥狀,0~4分說明無抑郁,5~7分說明有輕度抑郁,8~15分說明中度抑郁,16分以上則為重度抑郁。

2 結(jié)果
2.1一般資料比較精神分裂癥患者組與正常組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Beck抑郁評分等臨床基礎(chǔ)資料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見表1。
2.2兩組間SCS-C總分以及各個因子得分比較與正常組比較,患者組 SCS-C 總分及其各個因子分均低于正常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總分及其各個因子評分值見表2。
2.3患者組SCS-C評分與病恥感、PANSS評分間的相關(guān)分析Pearson相關(guān)分析顯示,患者組SCS-C評分及其各個因子分別與病恥感總分評分間均呈負(fù)相關(guān)性,其中SCS-C中的自我友善因子得分與病恥感中的情感體驗(yàn)因子得分呈負(fù)相關(guān)性(P<0.05)。患者組PANSS評分中陽性癥狀得分與BDI得分呈正相關(guān)性(r=0.253,P=0.011),等劑量氯氮平用量與病恥感的情感體驗(yàn)呈正相關(guān)性(r=0.314,P=0.015),與病恥感總分亦呈正相關(guān)性(r=0.294,P=0.023)。見表3。

表1 兩組間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資料與癥狀得分比較±s)
*劑量折算成氯氮平等效劑量

表2 兩組間SCS-C總分以及各個因子得分比較±s)

表3 患者組自我憐憫得分與病恥感得分的相關(guān)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結(jié)果初步顯示,患者組SCS-C總分低于正常組,反映了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憐憫能力受到損害,此結(jié)果與以往相關(guān)研究[12]結(jié)果一致。患者在SCS-C 3個分因子(包括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正念)上的得分也均低于正常組,說明即使在疾病穩(wěn)定期間,精神分裂癥患者遇到不幸以及挫折時,個體對自身缺點(diǎn)、不足的接納以及對于自我能力的理解能力存在缺陷,依然對自己感到失望,常常感到孤立、無助,無法和諧的生活;同時,患者較難直面自己身處的環(huán)境,自我痛苦的情緒以及思想一直持續(xù),不能客觀理智地看待自身所面臨的問題,從而產(chǎn)生過度的不良認(rèn)知,出現(xiàn)負(fù)面情緒[13]。精神分裂癥患者在康復(fù)期的上述心理特征,可能會使患者產(chǎn)生更多的諸如悲傷、恥辱、罪惡感等負(fù)性情緒,對日常生活的滿意度降低,因而對生活中的壓力采取消極的方式去應(yīng)對,社會功能進(jìn)一步降低。既往國外研究[14]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憐憫水平與PANSS量表的陽性癥狀量表得分呈相關(guān)性,在本研究并未得到證實(shí)。本研究顯示SCS-C中的普遍人性因子得分與PANSS量表的陰性癥狀量表得分及總分存在顯著負(fù)相關(guān)性,與此前研究[12]結(jié)果一致,表明分裂癥患者低水平的普遍人性感可能與陰性癥狀中的被動、孤僻等表現(xiàn)有關(guān),普遍人性感水平降低則患者的陰性癥狀明顯。
病恥感是造成精神分裂癥患者疾病穩(wěn)定期負(fù)面情緒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既往有調(diào)查[15]顯示近一半的精神分裂癥病患承認(rèn)曾在與周圍人來往中受到歧視,產(chǎn)生了病恥感的感受。這種感受妨礙了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人際交往,擔(dān)心被拒絕而退縮、回避正常的社交。同時在臨床工作中,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藥物維持治療特別容易受到病恥感的影響,因?yàn)榛颊邠?dān)心藥物副反應(yīng)及服藥行為暴露自身疾病,為了避免因病導(dǎo)致的羞恥感從而減藥甚至停藥,所以幾乎有一半患者對長期藥物治療配合程度較差[16]。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憐憫與病恥感程度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性,這表明患者在低水平的自我憐憫狀態(tài)下,容易產(chǎn)生不良認(rèn)知,對自我認(rèn)識不足,不能完全接納自身的疾病,同時不能客觀理智地認(rèn)識到自身的疾病狀態(tài),也會出現(xiàn)負(fù)性情緒,這些不良認(rèn)知及負(fù)性情緒,會讓患者體驗(yàn)到更強(qiáng)烈的病恥感,更容易感受到外界的歧視,并且出現(xiàn)更多的隱瞞自身病情、與外界隔離等行為,這對疾病的長期治療、服藥的依從性均具有很大的阻礙。以后在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用藥的長期管理上,不僅要針對其總體精神癥狀進(jìn)行藥物以及心理干預(yù),同時要通過提供關(guān)于自我憐憫的心理支持及提高自我憐憫水平的系統(tǒng)訓(xùn)練,減輕患者的病恥感體驗(yàn),更好地促進(jìn)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fù)。
本研究首次針對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憐憫與病恥感水平做相關(guān)研究,初步結(jié)果表明患者自我憐憫水平越低,病恥感越為強(qiáng)烈。但研究仍存在不足,例如對于精神分裂癥未具體分型、藥物的使用不統(tǒng)一,以及病程長短等未進(jìn)一步控制變量。以后的研究中需進(jìn)一步擴(kuò)大樣本,同時根據(jù)患者疾病發(fā)展的過程以及患者服藥的依從性,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預(yù)措施,從而幫助恢復(fù)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
[1] Brenner R E,Heath P J,Vogel D L,et al. Two is more valid than one: examining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self-compassion scale (SCS)[J].J Couns Psychol,2017:[Epub ahead of print].
[2] Bluth K,Blanton P W. Mindfulness and self- compassion: exploring pathways to adolescent emotional well-being [J]. J Child Fam Stud,2014, 23(7): 1298-309.
[3] Bluth K,Blanton P W. The influence of self-compassion on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early and older adolescent males and females [J]. J Posit Psychol,2015,10(3): 219-30.
[4] Heffernan M,Quinn Griffin M T, McNulty S R,et al. Self-compassio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nurses [J]. Int J Nurs Pract,2010,16(4): 366-73.
[5] Silke C,Swords L,Heary C.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empathy and social norms on adolescents’ implicit and explicit stigma responses[J]. Psychiatry Res,2017,17(257):118-25.
[7] Vrbova K, Prasko J, Holubova M, et al. Self-stigma and schizophrenia: a cross-sectional study[J].Neuropsychiatr Dis Treat, 2016, 12: 3011-20.
[8] Arimitsu K,Hofmann S G. Cognitions as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affect[J]. Pers Individ Dif,2015,74: 41-8.
[9] 陳 健,燕良軾,周麗華.中文版自憫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中國臨床心理學(xué)雜志,2011,19(6):734-6.
[10] Horsselenberg E M,van Busschbach J T,Aleman A,et al. Self-stigm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victimization, psychotic symptoms and self-esteem among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J]. PLoS One,2016, 11(10):e0149763.
[11] 鄭洪波,鄭延平. 抑郁自評問卷(BDI)在抑郁患者中的應(yīng)用[J]. 中國神經(jīng)精神疾病雜志,1987,4(6):236-7.
[12] 高艷平,董 毅,耿 峰,等.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憐憫水平及其與快感缺失間的關(guān)系[J].中國臨床心理學(xué)雜志,2016,24(5):819-22.
[13] 岳君思,耿 峰,董 毅,等.抑郁癥患者自我憐憫水平及其與快感缺失的關(guān)系[J]. 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51(7):1058-61.
[14] Eicher A C, Davis L W, Lysaker P H.Self-compassion: a novel link with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J].J Nerv Ment Dis, 2013, 201(5):389-93.
[15] Krupchanka D,Katliar M. The role of insight in moder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and stigma among their nearest relatives: A pilot study[J]. Schizophr Bull,2016,42(3):600-7.
[16] Hofer A,Mizuno Y,F(xiàn)rajo-Apor B,et al. Resilience, internalized stigma, self-esteem, and hopelessness among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Cultural comparison in Austria and Japan[J]. Schizophr Res,2016,171(1-3):8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