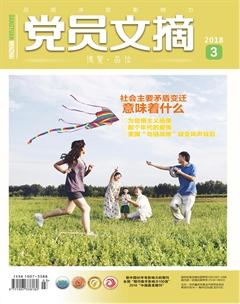禪城:打開大數據“瓶子”
鄭嘉璐
2017年被稱為中國的“新零售元年”,新零售背后的關鍵是商界以大數據為核心賦能實體經濟,相較而言,政府對大數據的使用則顯得有些冷清。
在實際工作中,基層政府也的確需要大數據的幫助,這種需求還很強烈。但偏偏就是在政策支持與實際需求的雙重動力之下,大多數地方政府的大數據工作雷聲大、雨點小,遲遲不見長足的進步,其痛點究竟何在?
為了探究基層政府對大數據的利用情況,記者選擇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作為樣本開展調查。
打破信息壁壘的困難在哪里
與阿里的消費大數據、騰訊的社交大數據不同,政府手中的大數據并不集中,而是分散在各個部門,缺少連接的渠道,形成人們常說的“信息孤島”。
一座孤島上的信息對本島的“島民”而言利用價值非常有限,但在其他“島嶼”看來就不一樣了。
例如,民政部門在審查貧困戶資格的時候非常需要申報人的資產信息,這些信息在車管所、房管局和稅務局都有,但民政部門就是拿不到,結果少數有房有車的家庭也成了貧困戶。
政府要想把大數據用起來,首先要打破信息壁壘,讓碎片化的大數據“活過來”。
禪城區數據統籌局數據資源科科長盧向國的主要工作就是對接各個職能部門,收集大數據,在實際工作中,他向各個部門直接索要數據是非常難的。
不少部門總會用這樣那樣的理由拒絕數據共享,總的來說無非是不敢、不愿和不能三種原因。
不敢是指害怕有風險、擔責任。一些領導擔心一旦出現信息泄密就是自己的責任,所以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對數據共享敬而遠之。
不愿就是有的部門把自己掌握的數據作為自身利益和權利的一部分,甚至看成是私有財產,不愿意拱手相讓。
還有一種情況是不能開放,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由國家一級或省一級垂直領導的單位,如工商、國稅、質檢等部門。它們的數據源代碼多掌握在上級部門手里,區一級政府沒有獲取權限。大量數據上傳到市、省一級,基層要使用時還得申請數據回流,不僅手續繁瑣,成功率也極低。
種種原因使得信息壁壘高筑,信息孤島難以打通,是數據賦能政府治理的痛點所在。
另辟蹊徑
直接向部門索要數據會面臨種種阻礙,禪城區2014年啟動的“一門式”政務服務改革卻無意中探索出一條新路,將大數據工作中的“我求人”轉變成了“人求我”。
“一門式”政務服務是指將原來多個辦事大廳的服務事項集中到一個服務中心,簡化到一個窗口辦結。
“一門式”服務的初衷是簡化辦事流程,解決市民辦事難的問題。在提供高效服務的同時,禪城區卻有意外收獲——作為副產品的大數據。
由于“一門式”平臺將十幾個部門的24個審批系統匯聚在一處,原本分散在各部門的數據也在這里集中。
這種集中有兩種方式。
禪城區行政服務中心副主任何樹營說,愿意主動分享數據的單位提供數據端口,數統局可以將它們的數據批量導入;而不愿或不能提供數據的單位,平臺可以用“跳轉”的方式截流數據。
所謂跳轉,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復制。比如政務服務平臺雖然沒能獲取民政系統的數據,但是在行政審批過程中,平臺擁有查閱這些數據的權限。
于是,每完成一次與民政相關的審批,服務平臺就把一個個體的民政信息收集起來,時間久了,這些信息匯成大數據,此前不能直接獲取的民政數據便掌握在區一級手中了。
在禪城區行政服務中心,每個窗口的業務員面前都有兩臺顯示屏。一臺顯示的是“一門式”政務服務的操作系統,另一臺則顯示其他部門的數據,專門用來跳轉截流。
這種做法其實是一種妥協,地方政府需要數據又不能直接獲取,只好選擇這種稍顯麻煩的方法自己收集。
三年多來,“一門式”平臺沉淀的數據量已經超過了三億條,這些數據與個人、企業緊密相關,有很高的利用價值。
不過這種方式也存在局限性,盧向國說,“一門式”平臺的數據都是行政審批類的“塊狀數據”,一些由部門掌握的“條狀數據”在行政審批中用不到,也就無法通過跳轉的方式截流。
為了獲取更多的條狀數據,禪城區接連出臺了《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辦法》和《大數據共享共建共用工作指引》,明確了“誰使用,誰負責”的原則,從制度上打消了部門提供數據時的顧慮。
更有效的做法則是將各單位的大數據工作納入年終績效考核,以此給部門施加壓力。盧向國坦言,自從有了績效考核,部門推諉、不愿提供數據的情況有了明顯改善。
“一門式”平臺積累的大量塊狀數據則是數統局的“本錢”,有了本錢,才能吸引其他部門來做數據交換。
禪城區數據統籌局副局長張軍說,目前各個單位的大數據意識已經越來越強,部門領導感受到大數據對他們工作實實在在的幫助,就愿意主動參與進來,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目前,數統局面臨的最大困難不再是區內部門的阻力,而是垂直領導單位的數據回流難。
大數據的能量迸發出來
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副教授鄭磊講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政府的數據就像封在瓶子里的蘇打水,關著瓶蓋的時候看上去悄無聲息,但只要把瓶子一打開,“嘭”的一聲,大數據的能量就迸發出來了。
禪城區的實踐印證了這個比喻。“大數據池”成型之后,禪城區開始探索對大數據的使用,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入學無紙化”。
過去,適齡兒童尤其是非本地戶籍的適齡兒童入學需要監護人現場提交戶口、住房、社保、工作證明等一系列資料,過程繁瑣。
現在,這些信息已經打通,教育部門只要調閱相關數據,就能在后臺用大數據完成審核,不僅免去了家長開證明、交材料的麻煩,還杜絕了材料造假的可能性——因為這些材料是由政府部門直接提供的。
這樣的應用還有很多。例如根據大數據形成的信用分級,政務服務平臺能夠提供信任審批服務,材料不全也可以先辦事;社會綜合治理云平臺則可以將多種渠道發現的社會問題通過標準化流程推送到對應責任部門,并指定具體負責人,避免部門之間推諉扯皮的情況。
大數據在禪城區的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上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在幫助政府科學決策方面,大數據的能量還沒有完全釋放。
禪城區數據統籌局副局長鄭小廣說,傳統的政府決策是模糊的,靠著經驗和感覺作決定,容易犯錯,只有大數據能幫助政府了解宏觀面上的情況,在數據支撐下作科學的決策。
目前的問題是,用大數據高效服務、精準治理相對容易,但政府決策是非常復雜的事情,牽扯到很多方面,大數據該以何種方式介入,禪城區還在探索當中。
(摘自《南風窗》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