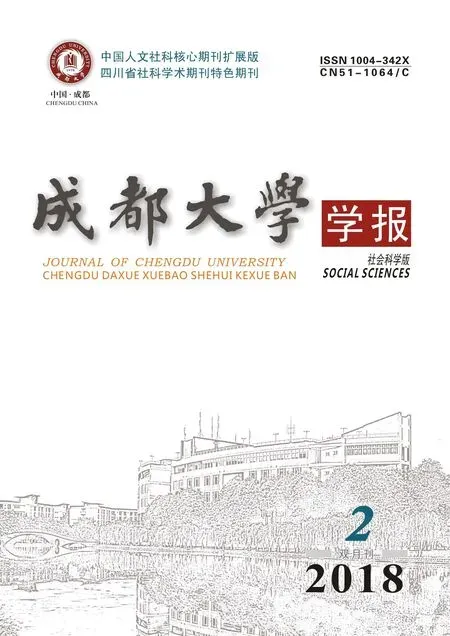《三國志補義》的內容與特色*
劉治立
(隴東學院 歷史與地理學院, 甘肅 慶陽 745000)

一、《三國志補義》的內容
《三國志補義》的內容涉及多個方面,在字詞釋義、時間、地點辨正、典章制度索隱、諸家說法比較等方面均有闡發。
(一)注釋音義,勘正字句
(二)闡釋地理,辨析時間

(三)解析典故,闡發制度
典故指關于歷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傳說,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具體出處的詞語。而制度指歷代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所指定和推行的政策、法規及具有法律效力的習俗等。康發祥在《三國志補義》中注意揭示典故,如《劉二牧傳》“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于事也。’”康發祥引用了裴松之的注解,進一步認為,“今人謂人死曰‘物故’,本此”[1]750。《魏延傳》記載,魏延與楊儀不和,“有如水火”,康發祥說:“按時人以不相能為水火,語本此”[1]758。
各個時代的貨幣單位變化比較大,康發祥以豐富的知識對其進行梳理。《呂蒙傳》記載,孫權給呂蒙“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一億到底有多少,康發祥做了詳細的解釋:“按億有大數,有小數。十萬曰億,乃小數也;萬萬為億,乃大數也。孫權于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余年鑄當千大錢。荊州之定在建安二十四年,未有當五百、當千大錢。所賜之錢,乃泛用之錢耳,以黃金五百斤準之,則非小數之十萬,必為大數之萬萬可知。”[1]826三國時期,蜀漢的許多官職只是遙領,法正之子邈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當時漢陽郡(治今甘肅甘谷縣)并不在蜀漢的轄區,康發祥注解:“按漢陽時已入魏,此蓋遙領之耳。張翼領扶風太守,亦猶是。”[1]755
(四)比較諸說,說明原委


基于對三國正統的判定,《三國志補義》在編次上不按陳壽原書的次序,采取先蜀漢而后曹魏的編排順序。卷一首篇是《先主傳》,其次是《后主傳》和《二主妃子傳》,其后才是《劉二牧傳》。對于這樣的安排,康發祥解釋說:“按陳《志》以二牧列昭烈、安樂之前,殊覺不合夫《蜀志》,以焉、璋列二主之前,何不以董卓、袁紹諸人列曹氏父子之前乎?今從《前漢書》陳勝、項籍、張耳、陳余,《后漢書》劉元、劉盆子、隗囂、公孫述俱列帝紀后之例,移置于此。”[1]749康發祥以兩《漢書》的史例為根據,做出這樣的順序調整。這種觀點劉知幾已經提出,“陳壽《蜀書》首標二牧,謂益州牧,即焉、璋也。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劉知幾提出了問題,而康發祥將之付諸實施。由于帝蜀而抑魏,對三國志的原有標題也做了改寫,如《先主傳》和《后主傳》下分別注以“陳書曰先主、曰傳,今當改正曰《漢昭烈帝紀》”,“陳書曰傳,今當改為紀”[8]35。而曹魏四卷帝紀,也做了改正,《武帝紀》下注明“陳志曰紀,今當易曰傳”,在《文帝紀》《明帝紀》和《三少帝紀》下則注“陳志曰紀,今易同前”。

二、《三國志補義》的特色
康發祥的“補義”,最突出的成就不在字詞的解釋,時間、地名的考證等,這是清代考據學者注釋《三國志》的共同目標。對三國志的解讀、對裴松之注的研判,以及對《三國志》體例的討論,是其書的不同于其他注本的特色。
(一)對《三國志》及裴注的獨到見解
以“義”為名的注述,漢以前多是說明經學典籍的義理,其體式和古代傳注相近。六朝以后,則專以解注者為義,與義疏同意。作注而說其義,是義的內涵,何宴《論語集解序》:“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疏曰:“謂作注而說其義。”這種注釋在作文字訓詁的同時闡發原作之義理,在經學一統學術的地位動搖的背景下,為許多經史注釋者所采用。以闡釋所解書籍的要義的義體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盛行起來,出現了許多義體注本,如南朝梁時崔靈恩有“《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9]677。康發祥將其著述命名為“補義”,表明其書主要是要闡發自己的見解,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三國歷史的看法,二是對《三國志》的見解,三是對裴松之注的認識。
1.對三國歷史的看法


2.對《三國志》的見解


康發祥深受正統儒家思想的浸潤,對春秋筆法非常贊同,對于《三國志》中的“書法之妙”也很注意發掘。陳壽在《吳書·濮陽興傳》中揭露丞相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勾結寵臣張布,“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裹,邦內失望”。康發祥評價說:“按堂堂之相,與寵臣比周,宜其死也。曰丞相曰寵臣,此書法牽連之妙。”[1]836陳壽有意溢美曹操,但有些地方還是體現了直筆,曹操率軍進攻陶謙,“所過多所殘戮”,康發祥說:“按承祚作魏志,每多曲筆回護。茲言多所殘戮,此直筆也”[1]768。司馬昭指使成濟襲殺曹髦,《三國志》僅言“高貴鄉公卒”,對死因只字不提,歷來為史家詬病,劉知幾在《直書》中對“發仗云臺,取傷成濟”,陳壽“杜口而無言”[8]69予以譴責。梁章鉅也發出了質疑:“前此幸太學、幸辟雍皆稱帝,至此忽改從舊號。且明系刺死,而但書卒,不可解”[12]277。康發祥憤怒地指斥:“按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云龍門之變,昭假手于成濟,抽戈犯蹕,遂成惱惡。史不能大書特書,暴其罪惡,乃假以皇太后之令,多方掩飾,以欺萬世,可謂悖矣。且于帝髦之死,祗書曰卒。夫即以髦帝制不終,仍從舊爵,亦當以薨書,不應以卒書。何物鬼魅,操此史筆。亮哉,黃東發之言歟!按《晉書·天文志》于彗星見角下,大書曰高貴鄉公為成濟所害;于客星見太微下,大書曰高貴鄉公被害;于日有蝕之下,亦大書曰有成濟之變。《晉志》不諱言,承祚之史何悖謬如此。”[1]773康發祥痛斥這種回避真相的歷史記述為“悖謬”。
3.對裴松之注的認識


裴松之征引材料是很審慎的,對于一些記述還表達自己的看法,如《諸葛亮傳》摘引了有關空城計的記述后表示,“舉引皆虛”。《文聘傳》記載,“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裴松之引用《魏略》的材料做補充,“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雖然裴松之也表示“《魏略》此語,與本傳反”,但對這一則“空城計”沒有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論斷,“按《魏略》實屬不經,豈有大兵臨城而可以臥而卻之乎!況孫權雄才大略,豈肯不攻而去,竟如小兒之可欺乎?吾觀魏臣諸傳,每多虛譽,而《魏略》尤甚,識者鑒諸。”[1]794《魏略》所記述的文聘臥舍卻敵,顯然是低估了雄才大略的孫權的智商,這種虛譽可謂荒誕不經,不可輕信。
三、對《三國志》的體例的卓見

由于特殊的身世和經歷,歷史人物往往有多個名字,如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后乃復姓,改名忠”[2]1048,陸遜“本名議”[2]1343。在敘述中應該前后一致,不要諸名雜用,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李嚴于建興八年改名為平,《李嚴傳》中前半部分稱“嚴”,后半部分則呼為“平”。康發祥認為,“李嚴既于建興八年改名‘平’,傳中不應前后異名,宜始終以‘平’名之,以從馬忠、陸遜諸傳之例。否則《馬忠傳》何以不前曰‘狐篤’,后曰‘馬忠’;《陸遜傳》何以不先曰‘陸議’,后曰‘陸遜’也。”[1]758
在《呂布傳》中,突然插進一大段張邈的事跡,雖然與下文有一些聯系,但還是顯得很突兀,康發祥說:“按《呂布傳》中夾張邈一傳,既非合傳,又非附傳,其體例特奇”[1]780。雖然沒有明確否定,但還是將其點出,暗示這種離奇的做法很不合規范。《閻溫傳》文字又少,而作為其附傳的《張恭傳》卻相對詳細,稱張恭父子“著稱于西州”。從敘述的內容看,張恭的影響似乎要大于閻溫。康發祥指出:“按溫傳附張恭及子,就傳甚詳,而溫傳頗簡,何如作張恭父子傳,而以溫傳附之邪。即以歲時考之,恭事亦在溫前也。”[1]794按照康發祥的意見,與其稱《閻溫傳》,還不如稱為《張恭傳》,這樣更符合實際。

四、《三國志補義》的不足
康發祥生活的時代,與陳壽相隔一千六百多年,形勢完全不同。在分析《三國志》的許多問題時,康發祥沒有充分考慮特定的時代局限,而是囿于清代的思想局限,以自己所處時代的觀念(如正統觀)來苛求古人,不能像錢大昕所提出的護惜古人之用心,因此,在一些具體論斷中也存在不恰當之處。
(一)政治倫理化準則壓倒了事實依據
龐德本為馬超的部將,曾跟隨馬超投奔張魯,后來又隨張魯歸順了曹操。在與關羽作戰中,龐德對督將成何說:“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茍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2]546最后兵敗被殺。對于龐德的豪言壯語,康發祥站在蜀漢正統的立場上,提出激烈的批評:“按龐德身為降將,不死于馬超、張魯,而死于曹操,猶五代時周臣韓通不死于漢而死于周也。雖時作壯語以死,君子無取焉。”[1]794以龐德不死于馬超、張魯,而死于曹操,特別是與康發祥所仰慕的關羽對抗而死,就否定其死節,表示“君子不取”,缺乏歷史公允。
(二)偏重發義而忽略了知人論世


(三)時間考辨帶有臆斷

關于劉放和孫資任光祿大夫的時間,康發祥說:“《齊王紀》,正始元年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正始元年始加光祿大夫,則前此未為光祿大夫也。青龍初年恐是但加侍中耳,光祿大夫四字疑衍。”[1]791對于這一論斷,盧弼提出駁議:“本傳明言正始元年更加放、資左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曰‘更加’者,明前已加也(《齊王紀》并未言‘始加’,‘始’字康氏所增)。且漢制,光祿大夫屬光祿勛。此則變更官制,位次三公,與特進同為加官,故再加任命,特書《本紀》。傳文不誤,康說非是。”[11]1343
(四)注解詞語偏離本義
康發祥憑其管窺,對字詞做出解釋,也出現偏離詞義的地方。《和洽傳》:“太祖令曰昔蕭、曹與高祖并起微賤,致功立勛,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2]656句中“屈笮”的含義是困苦危難。康發祥根據《說文解字》做出解釋,“按《說文》,笮,迫也,篇海急也,屈笮,或是褊急之義”[1]805。“褊急”意謂氣量狹小,性情急躁。雖然加上“或是”,表明只是一種推斷,但確實還是背離了詞義。漢高祖在創建基業的過程中多次陷入困苦危難,但蕭何、曹參等人卻恭敬順從,始終追隨不舍,周守昌征引經籍注例,解釋更加達意,“屈笮是委屈急迫之意,《史記·大宛傳》徐廣注,屈,抑退也;《荀子·榮辱》篇:屈,竭也,笮,《說文》,迫也;《漢書·王莽傳》:迫笮青徐盜賊,即此意。”[15]855
盡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三國志補義》的成就還是很重要的,其認識上的局限和個別論斷的瑕疵并不能掩蓋其在《三國志》注釋中的貢獻。發掘《三國志補義》的成就,對于全面認識清代學者的史注活動,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康發祥.三國志補義[M]//二十四史訂補·第五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2]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4.
[3]潘眉.三國志考證[M]//二十四史訂補·第五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4]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5]汪文臺.七家后漢書[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6]何焯.義門讀書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7.
[8]劉知幾.史通[M].長沙:岳麓書社,1993.
[9]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0]趙翼.廿二史札記[M].北京:中國書店,1987.
[11]盧弼.三國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2]梁章鉅.三國志旁證[M]//二十四史訂補·第五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13]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2.
[15]周壽昌.三國志證遺[M]//二十四史訂補·第五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