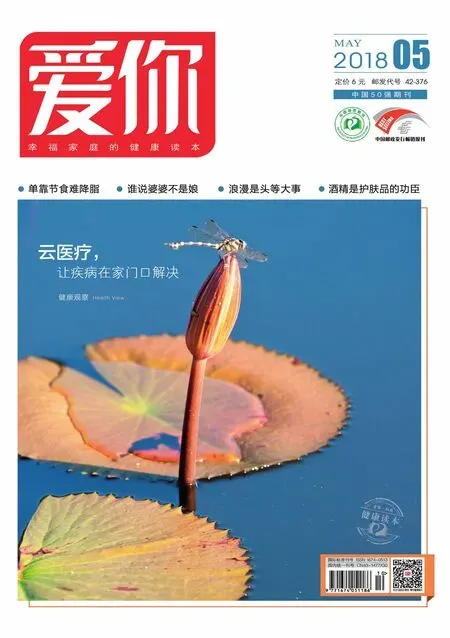沒有勝利者的戰爭
2018-05-11 09:51:46◎佘濤
愛你 2018年14期
關鍵詞:情感
◎ 佘 濤

1918年底,阿道夫·希特勒在一戰中因毒氣負傷在普魯士小鎮養傷,當他恢復意識的時候,驚聞同盟國已經戰敗投降。他撲倒在自己的床上,把腦袋埋進枕頭和被子里。“我從站在母親墓前的那一天起就沒有哭過,現在我無法自已了。”
這種以民族主義為導向的情感,在一戰后社會危機和激進化思潮的刺激下,釀成了20世紀最濃郁的一杯毒酒。
恥辱感是任何一個戰敗國都會有的正常情感,但是一戰所帶來的這種情緒有其特殊性——它容易轉化為極具攻擊性的背叛感。
對戰敗國德國而言,戰后最要緊的事是彌合被戰爭極大撕裂的德國社會。新成立的魏瑪共和國政府試圖彌合這裂痕,埃伯特總統在勃蘭登堡門迎接從前線返回的軍隊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們沒有被擊敗。”可惜這樣的努力在戰后德國的困境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右翼思潮的左右夾擊下敗下陣來。
許多昔日的士兵都覺得自己被后方出賣了。他們經常被蘇維埃的支持者解除武裝、撕去肩章和羞辱人格。有些人還覺得家人并不歡迎自己,因為他們的長期離家使得家庭收入減少,還不能以打了勝仗來辯解。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讓人們看到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可以實現的。
赤色革命激起了德國右翼分子的反彈,本來“相對平靜和以濃濃的資產階級化引以為傲”的慕尼黑反而成為魏瑪共和國中最堅定的反布爾什維克的城市。激進復仇的情緒四處蔓延。
猜你喜歡
今日教育·作文大本營(2025年3期)2025-03-24 00:00:00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5期)2021-01-18 02:59:48
家庭醫學(下半月)(2020年4期)2020-05-30 12:42:50
現代裝飾(2020年4期)2020-05-20 08:55:06
北極光(2019年12期)2020-01-18 06:22:10
小太陽畫報(2019年10期)2019-11-04 02:57:59
海峽姐妹(2019年9期)2019-10-08 07:49:00
青年歌聲(2019年7期)2019-07-26 08:35:00
中國生殖健康(2018年5期)2018-11-06 07:15:40
發明與創新(2016年6期)2016-08-21 13:49:38